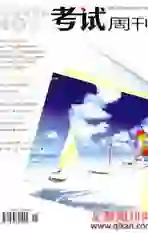马远、夏珪绘画构图研究
2009-06-08韩飞燕
韩飞燕
摘 要: 对马远、夏珪的绘画作品前人一直有“残山剩水”的说法,本文试图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及理学思想的影响三个方面去探讨他们作品的构图问题。
关键词: 马远、夏珪 山水画 残山剩水 画风 影响
马远、夏珪是南宋时代的两位重要画家,在山水画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
山水画至宋代,其兴旺之景象前所未有。它向多方面发展,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也更加多样。五代荆浩所提出的“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创作方法,宋代画家已能充分掌握并运用。沈括提到的“以大观小”,更道出了中国山水画在观察自然与表现自然上所具有的一种特殊方法。
两宋山水画的题材内容也逐渐扩大,不止探索山川自然的奥秘,很多作品与当时的社会生活联系甚密,与游乐、山居等活动结合起来,虽然着重于山川自然的描绘,但也能反映当时社会的某种面貌。此外在技法上也有很大的突破。
在绘画方面,南宋承继了画院的制度,规模和人才的罗致都不减北宋;北宋时代因为大局比较稳定,在画院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的画家,而在南宋,杰出的大师差不多都包罗在画院里面,影响范围较北宋更大。山水画由于新环境的刺激和影响,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号称“南宋四家”。他们在山水画坛上创造出“水墨苍劲”的新风格。他们画山石喜用斧劈皴,方棱峻峭,骨格峥嵘;画树多瘦劲挺拔,风致潇洒;用墨不作层层积染,而是从浓淡中求层次变化,一气呵成。故他们的画给人以苍劲挺健而又清新俊秀的美感。在四家中,李画较为雄健苍古,刘画则偏于峻峭工细,马画坚实浑朴,夏画清妙秀远,各具特色。尤其在章法布局上,他们能别开生面,打破荆、关以来“全景山水”的格局,而创造出边角取景法,使山水画产生新的意境。其中又以马远、夏珪最为出众,他们的山水画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远及日本,促进了日本绘画的发展。
马远,字钦山,光宗、宁宗时画院待诏。出身绘画世家,曾祖马贲、祖马兴祖、伯马公显、父马世荣、兄马逵等皆为宋代知名画家。
明曹昭《格古要论》云:“马远师李唐,下笔严整,用焦墨作树石,树叶夹笔。石皆方硬,以大劈斧带水墨皴。其作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树参天,而远山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此边角之景也。”马远学李唐而又有创新,用焦墨作树石,大斧劈画山,发展了水墨苍劲一派技法;构图别具格法,常常是很简洁,或是利用远景和近景相对比、相烘托,而得到鲜明、强烈的效果。这一表现方法固然李唐是先驱,但到了马远,运用的更成功,更有新发展,成为南宋山水画的一大特色。
夏珪,字禹玉,钱塘人,宁宗朝画院待诏,赐金带。人物苍老,“雪景全学范宽,院人中画山水,自李唐以下,无出其右者”(《图绘宝鉴》)。
明曹昭《格古要论》云:“夏珪山水,布置皴法与马远同,但其意尚苍古而简淡,喜用秃笔。树叶间夹笔。楼阁不用尺,界画信手画成,突兀奇怪气韵尤高。”夏珪山水师李唐,而又有所发展,喜作带水斧劈皴,简劲苍老而墨气明润。与马远画风相近,同属水墨苍劲一派。传世画迹有《溪山清远图》卷、《江山佳胜图》卷、《灞桥风雪图》轴、《遥岑烟霭图》纨扇等。
夏珪的创作题材主要是山水画,也兼画人物。夏珪爱好描绘风、雪、烟、雨中的江湖景色,从其现存的一部分作品来看,他确实擅长表现这种江南水乡的气候特征。同时夏珪还擅长长卷这一创作形式。
纵观马远和夏珪的绘画作品,可以说马远和夏珪最不同于前人的地方是在画面的构图和笔墨运用方面,一直以来都有“马一角”、“夏半边”的说法。这种构图简洁、主体鲜明的山水画有一种全新的境界。但是由于这种创新不同于传统绘画的全景构图,因而引起了许多评论,有人附会说马远画的是“残山剩水”,刚好象征着南宋的山河破碎,如“评画者谓远画多剩水残山,不过南渡偏安风景耳”(《珊瑚网》)。这种说法是不太妥当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皇权下的绘画
虽然说南宋偏安一隅,政治上十分黑暗,军事上也相对较弱,但是经济及科技高度发达,文学艺术也有很大的成就。作为服务于宫廷画院的画家,可以说统治者的喜好对他们的创作十分重要,他们表现的大多是当时社会生活好的一面,不论是悠闲的宫廷生活还是美丽的自然山川都是他们描绘的对象。画家们以得到帝王的肯定为荣耀,而马远、夏珪就都曾是画院的待诏。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除了极少数像梁楷那样随性自如、弃金带而去的画家以外,绝大多数的画院画家都是以统治者的爱好为准绳的,马远、夏珪也不例外。因此他们不太可能为了讽喻统治者偏安一隅而去创造“边角之景”的山水画,因为这关乎他们的生存。另外,马远、夏珪二人都是继承了画家李唐晚期画风并加以发展才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的。
李唐,字晞古,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生卒年不详。宋徽宗时已入画院,北宋灭亡后,与弟子萧照南渡,建炎间(宋高宗的第一个年号,1127—1130年)仍入画院为待诏,阶成忠郎(正九品)。李成在宋代绘画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上接北宋画院之余绪,下开南宋院画之风气。宋高宗对他的画艺极为赞赏,认为“李唐可比李思训”,并多次在他的作品上书题。
正是由于李唐得到了朝廷高层的欣赏,他的风格才会在画院风尚。李唐晚年画风已经类似于“边角之景”了。如他的《清溪渔隐图》:此图大约描绘的是江南雨后渔村恬淡而宁静的生活场景。画面彻底颠覆了北宋全景山水的构图法则,已然是南宋山水画所特有的类似于“特写”的“边角之景”了。画面上大石突兀,上不见山峰,下没有坡脚;而树木则看不到树梢,只有劲挺的树根牢牢地“抓”在大石上。其后的马远、夏珪之构图法就脱胎于此,并有所发展。
二、艺术发展需要创新
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艺术也不例外。任何的艺术风格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都需要变革,否则就会僵化,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北宋时期习惯以立轴画大山,山水画的主要特征是雄壮浑厚。宋室南渡,绘画中心转向南方,许多北方的画家南下,中国山水画“山”的主题变为“水”。画家们更致力于塑造秀丽的江南山水形象,画风也由北宋的雄壮浑厚转为空灵雅秀。另外,南宋特別发展长卷,相对于北宋以“立轴”画大山的习惯,长卷是更适于“水”的流动与视觉移动的效果。
对于这一点,顾平先生在《偏安情结:南宋四家绘画》中说:“浙江杭州景色是典型的江南特色,南宋都城临安,画院因此也便置于这美景之中。南宋画院又设在宫廷之外的望江门内,因此画家们便有了陶乎自然的便利条件。我们从‘南宋四家以西湖、钱塘为题所作山水可看出画家游历的记录,这些景致自然要被他们摄入作品之中。比如‘四家的许多作品的近景,就画了杭州一带的阔叶木,也有表现汀渚蒲苇之类;画中并多有烟雨感。这些对象的表现必然要用与之相适合的笔墨,所以北宋的笔墨产生了变异。在山石形态表现上,同样也如此,因为笔墨是从北方山水语汇中变化而来,虽然有简约化倾向,但由于特写表现的关系,局部之景放大石质结构,因此有了大斧劈皴,这种大斧劈皴也非常适合江南石质山景。如马远《踏歌图》、夏珪的《溪山清远图》等。而稍远之景则以线勾后,全以淡墨染之,仍有南方土质山坡之感,只不过不能近视之。如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夏珪《山水十二景》等。正所谓‘远山取其势,近山取其质。”[1]
宋室南迁以后,自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艺术要想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必须改变,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因此边角山水也就应运而生了。
三、理学思想的影响
北宋后期,正是理学发展的高峰期,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程均活动于此时,他们的思想倾动朝野,影响甚巨,对宋画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应当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理学在宋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理学强调一沤就是茫茫大海,一尘就是无量大千,万物各有其理,其理通而为一,自一物即可关照万物,自一理即可关照万理,在一个微小的物象之中,“周人情物理之变”。所以受此影响,画家们关心细微之处的妙韵,渺小处的真实,至简而天下之理在焉。因为在他们看来,空间再小、物象再微,都是一个自在圆足的世界,都是一个“全”。他们期望以一片树林、一块石头、一角溪水、几只禽鸟去创造一个大境界,无边的世界就在这一草一木中。所以,南宋的大多数画家都醉心于微小的世界中,留连于小山小水之上,徘徊于汀渚之间,吟味小景的意味。
北宋后期,小景画颇为流行。这种绘画风格,无论是构图还是审美意趣都与南宋边角山水有共通之处。这一时期,正值理学发展的高潮期。当时盛行的理学思想对画院画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当时的审美思潮下,全景山水所体现的那种境界与审美主体所产生的距离,使画家与观者的自我性灵受到压迫,使得以后很多画家不再去千里江山中寻找表现对象,而往往着眼于微小的物象。赵令穰、王诜都善画小景画,苏轼也对小景画非常感兴趣。北宋末年更加多了起来。可见李唐笔下的画风之变也是在画风转型之下的一种必然。而作为他的后继者的马远夏珪的画风也当然是在这种形势发展下的必然结果。
可见,马远、夏珪的画风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并不是对南宋统治者偏安一隅的暗讽,它只是艺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艺术形式。而其后师从他们的后代画家也有很多,如明代前期的浙派,故有“院体浙派”的称谓。可见马、夏画风的影响之大。
参考文献:
[1]顾平.偏安情结:南宋四家绘画[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