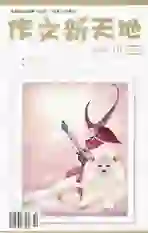乡愁三叠
2009-06-07卢李霞
卢李霞
在路上: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彼时还是踩着15岁尾巴的青涩少年,于飒飒秋风之中看故乡林中落尽的红叶,田地间整饬的麦茬;而今,我却已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异乡的路,成为了天地间游吟无边山水的诗人,尘世中跋涉广袤大地的行者。
我并非是不知故乡之美。因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福祉,我得以融入故乡的每一次日夜更替,四季轮换,我得以在日益成长的过程中触及她的血脉,她的根系,和着她呼吸的节律欢畅跳动。我知晓她的生命力所在并对此坚信不移,因那是我能够切肤感知的温存。在路上,每当独枕夜色清凉如水,脑中便有故乡的帧帧画面流转而过。
我看到夏日里,故乡的山坡绿得浓稠。树与竹交错而植,枝叶蓊郁,远望如海。白至晃眼的日光由枝枝丫丫的缝隙打下,隐约可见数条光柱。林中水汽温凉,弥散成雾,蝉鸣似浪。烈日下尚在劳作的农民肤色古铜,暴露在阳光下的脊背上爬满了细密的汗珠,似在诉说对天空与土地的虔诚信仰。我看到秋天里,故乡被温暖人心的金红色包裹,空气中弥漫着粮食的馨香,触动心底那方来自生命原始的感动。乡农们的欢声笑语犹如一支甜醉心曲,汇成秋走过的跫音,散发着的微醺气息,悠悠然使人铭刻于心。我看到冬季里,绒毛般的白色精灵悄然而至,银装素裹后的大地刹时变得静穆,房屋,远山,石桥,草木,皆在素净一致的色调中和谐相拥。白雪皑皑的天地间时有农人长久驻足,极目远眺,姿态虔敬,默祷来年的风调雨顺。我看到故乡的春,那是我离开的季节。初春三月,冰雪消融,泥土温润,草木绿得单薄却也有了无可抗拒的生长欲念。林间走过一遭,便浸染了一身植物的辛香。当我走在与家相反的方向,踏上通向未知的蜿蜒路径,有老人向我道别。他们以枯瘦黝黑的手掌颤悠悠地抚过我的脸庞,其时我看到如刻刀般游走的时光在他们脸上所留下的深浅沟壑,顿觉动容。
我并非是薄情寡义,只是我知道,我必须离开。我与故乡皆须成长,这是身心拔节的必然呼唤。选择上路,我的成长便在路上。而对故土,我希冀能尽我所能,为其安一双深邃的眼眸,注一池奔涌的血液;我希冀能以我一路走过的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成其生长的养分,使之得以感受别处的故事,聆听别处的歌声,使之拥有更丰润的胴体及更丰厚的土地。
与故乡暌别经年,我曾路过城市路过村庄,路过沙丘路过森林,路过河川路过山岭,路过了无尽的荒漠,路过了丰美的草原,也路过了神话中的湖泊与城堡。日渐沧桑的脸庞成为在年岁与路途中自我磨砺的清晰见证。历经百千个或嘈杂或静默的日夜,于此一番由羞赧少年蜕变为洗练歌者之过程中,沿路一切辛酸苦楚早已了然于心,冷暖自知。在此之间,一路孤苦寂寥却总抵不过乡愁的蚀骨忧伤。若说物质上的暂缺是掌上一段粘滞的蛛丝,那源自精神深处的乡愁便若烙于心房的伤疤,倔强深刻与我同行。它是一段镌刻在体内的曼妙音符,游离在深远的夜幕之下,于月的清辉之中,夜夜笙歌。
异乡梦: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惆怅,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开的时候,我以为我已不再爱她。
那一日,晨曦微露,我与同行的伙伴一同踏上了不归的旅途。走在新开的崎岖山路,我未回头望一眼雾中的村。我是那么急于摆脱她,就像要摆脱一个可怖的梦魇。我甚至未曾记得来路如何。
较之他人,我还算幸运,凭借一身气力,时常能在车队装卸货物或在工地上搬石运沙。所得微薄,但也能对付平日生活。每日奔波劳累使我无暇忆起故乡及关于她的任何,无论是我所尽知的不堪还是尚未意识到的好。
一日,同住的工友收拾了行囊欲回故地小住。面对我的疑惑眼神,他笑言:“漂泊在外,沉浮无尽,总觉得是浮萍野蓬,孤苦无依。故乡是我的归宿地,对她的情爱是牵着我的线,离得再远也总是要回去的。你我背离桑梓之地的缘由虽不相同,但与故乡的爱恋终究是相类的。”我虽没搭话,心中却陡生对他的诸多歆羡。他尚有家可归,而我却早已割断了线,忘却了路,所谓故乡,不复寻踪。
那一晚,如豆灯火之下,我第一次试图忆起故乡的样貌。记忆封存过久,早已泛黄落尘,回忆如隔了毛玻璃般不甚清晰。只能依稀记起幼时的故乡,其时她尚且美丽。清晨,村庄被雾气所包裹,安眠中的她笑容甜美如幼童。正午时分,田塍上便走过三三两两送饭的妇人,有壮汉盖着草帽在树荫底下小憩。傍晚收工,农人们便在袅袅炊烟的呼唤下,顶着夕阳结伴回家。但凡不落雨的夜,总能见到数点星光,光辉闪耀,照亮回家的路,指引归家的人。回忆至此,始觉思念如野草般疯长,像藤蔓植物那般紧紧攫住了心脏。离开时,我以为我已不再爱她,于是存心与她相忘于世,今日才明白过来,那片生长过的温柔土地是无法被轻易忘却的。可悲可叹,因当年自绝后路式的决绝彻底,如今我终是回去不得。
行年渐晚,时间冲刷之下,故乡的面貌或许会变得愈发模糊,空留一抔怀念及遗憾于我。我惊异对故乡的痴恋竟可在心底蛰伏如此之久,而一旦唤醒,却又奔流不息。当年离开时的不道别不回望想来也并不是急于甩脱的迫切,而是一旦驻足,留恋便会牵绊住双脚的自知。长久以来情感中的沉疴不过源于对乡土之爱的逃避与错解,由此嬗变而来的乡愁却平添了更多的悲叹与怀想。
如今我只能于异乡的梦中回归故里,梦醒便是别离。那解不了的乡愁,已然成为我生命中一枚悲情的勋章,使我夜夜怅惘。
子规啼: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
初春的一日,与友人上山踏青,于半山休息时,有活泼的鸟儿自身旁掠过,友人告知:那便是子规了。想起中学老师常讲,古人借“子规”表露思归之情,如今再闻此名,心内感伤,算来离家在外已是三月有余。杨耕先生曾写过:现代是一个流动的时代,每个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游子,不约而同地,我们都在流动,或神游八极,或远走天涯,但心安处,即是故乡。初次读之,便有感喟油然而生。
我并不知自己的原乡在何方,祖先代代都是游子,迁徙已成习惯。幼时便跟随父亲辗转,每次别离都是一次伤害。没有原乡,因而处处都是异乡。本以为要若无根之萍般漂游一生,无处驻足,直至寻得那句“心安处,即是故乡”,方使我如醍醐灌顶。原来故乡并不只是肉体的归宿地,更是灵魂的栖居之所,一片流过血流过汗的土地,即是故乡。
数年前于异国他乡求学的日子里,目睹繁华三千,但那终是陌生的风景。夜幕下的华灯初上,以异乡人的眼望去灯火阑珊不过是粉饰太平。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下的迎来送往皆与我无关,只是徒然荡起无所归依的虚无气息。心闲下来的时候常隔着大洋眺望祖国的方向。那片热土,不管肥沃或是贫瘠,在故乡这一称谓前,都是象征家的图腾。
简桢写道:走惯贫沙,啃过粗粮,吞噎之时竟也有蜜汁之感,或许,这是我的迦南地。的确,纵然故乡并不富足繁华,但在其中所经历的,也足够漂染整个年华,足够填充三月、三年甚至三世的空缺。
时光在树上写史,写不下的,是沉沉的乡愁。一月之后回归故里,我必掬一捧故乡的土,嗅嗅那落菊的清馨。
(指导教师:章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