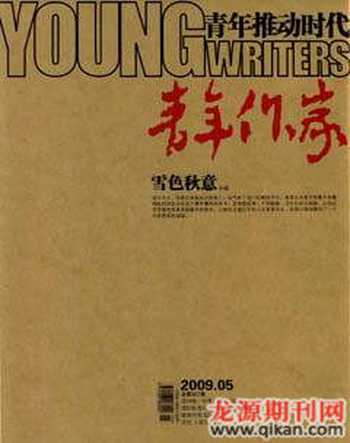植物学
2009-04-29胡桑
胡 桑
你捎给我大地的消息
——何羲和《假期》
我最初学会走路的地方不是在木楼板上,也不是在宽大的厢房或者家家户户门前露天的稻地(用来晒稻子的水泥地)上,而是在某一片番薯地里。如今,东升自然村的地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除去村子西南一角高出水田许多的房屋宅基依然保持旧貌,其余的桑树地和水田优美而苍老的轮廓在三四年前的平整土地期间荡然无存,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总是在想尽办法“建设”新的东西。我惦念着的故乡的那片高低起伏、错落有致、死角颇多的土地终于被平整为整齐得毫无特点的水田和同样整齐得毫无特点的桑树地。虽然并不能确定我家番薯地的具体位置,但是,我“想”起来,总会浮现出村东“大畈里”一带的一片桑树地。那片桑树地其实是隔壁阿芳爷爷的番薯地,只因常去剪番薯梗子,记忆十分清晰。它隐藏在一大片桑树地中间,西边矗立着一株硕大阴森的柏树,树下是一个大坟。每次父母在灯火微暗的餐桌上说起我的婴儿时期,总要强调家里的贫穷、我的无人看管,于是小小的瘦弱身躯只能跟随父母去地里劳动。就在番薯地里,我扶着一只竹箩筐(方言里有两种:方者曰簸、圆者曰箩,体积都很大),竟叫着母亲的名字,走向另一只箩筐。这是我走路的开始。就在一片番薯地里。为什么我总是走不惯大都市的街道,走在上面总是心情阴郁、抵触。原来,我一开始只会走坑坑洼洼的番薯地,那时父母在挖番薯。
番薯是我生命里的第一种植物。后来读书,总是见别人叫它红薯,待到在大学里学习现代汉语课才得知,“番”在外来词里十分普遍。比如番茄、番石榴,是国外或外族来的东西。就像方言里还有一种以“洋”开头的词,什么洋火(火柴)、洋机(缝纫机)、洋钉、洋铅丝、洋肥皂。同样和外国有关。吴语这些最初的声音是我最初的世界。
故乡最多的植物自然是水稻和桑树。桑树地总是围绕在村子的周围,犹如绿色的御林军,常年厮守。关于桑树和桑树地我在几年前的《桑树地:记忆的滩涂》一文中已经详细写过。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在西安上学。后来到上海,终于多出很多时间回家。尤其是清明时节,在纷纷细雨里,我发现,初春的桑树抽出嫩芽是嫩嫩的鹅黄的,鲜活欲滴,十分可人。到夏天,桑葚挂满枝头,无人理睬,怡然自得。而桑葚在上海已经被当做商品上市,卖到好几块一斤,城里人大概想象不出桑葚是一种野果,除了顽皮的小孩,基本上无人问津。
乡村对我而言不是一种地域,也不仅仅是故乡,而象征了一种生存方式。我用桑树做了自己的笔名。于是,桑树在内心便越长越高大。曾与何羲和描述过桑树:一种浩瀚绵延的绿色植物。桑树地之于我,就像大海之于海边渔民,桑树对我而言的确是一种象征。
桑树地外面就是大片的水稻。西起新开河东到南塘(含山塘),中间被一块叫做“牛舌头”的桑树地隔开。这些水田不全是东升的,还有邱家浜的。所以,每到农忙时间,田耕上来往着许多熟悉的面孔。水田里就热闹起来,问候、打趣、闲聊,吴语在水田上空飞翔。这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场景。我常常感叹不能在农忙时节回家,不能再倾听这种声音、观看这种场面。每次回家,农忙尚未开始或早已结束,去田野里乱走,只能见到一两老人,在拔草或者锄地,很凄清。
我这一代的孩子不像现在的孩子娇惯。我们六七岁就开始下地。所谓的下地,一般是下水田——种田,或者叫做插秧。我说过,故乡最多的植物是桑树和水稻,而一般的所谓劳动,就是种田和养蚕。这两种植物一旱一水,一木本一草本,一高一低,犹如巨大的绿色城墙,共同拱卫着故乡的村庄。大面积的灌满浊水的水田,对我来说,就像是庞大的湖泊。我是漂浮之上的一只小船,永远不能抵达岸边。我小小的身躯陷在被水泡软的泥里,一边插秧,一边缓慢地行动。我感到腰疼。母亲却说,只有大人才会腰疼。可是我在插秧时却真的在腰疼。我充满了对水田的恐惧,主要源于吸血的极丑的蚂蝗以及会咬人的狰狞的蛇。青蛙很可爱。夏天早些时候还有蝌蚪。黑色的蝌蚪其实是蛤蟆的幼虫,而泥土色的个头较大的才是青蛙的雏形。不过,这个常识一直被我们的小学课本所忽略。《小蝌蚪找妈妈》里的插图是黑色的蝌蚪。以至于我后来和其他人说这是蟾蜍的孩子,没人信。但青蛙在水田里其实是很弱势的,它经常是水蛇的猎物。
水田里有一种饭粒虫。它长得就像一颗饭粒,白白的,长长的,瘦瘦的。会咬人。在我尚未被它咬到之前,比我稍大几岁的永妹早就经验过这种疼痛,她描述得异常吓人,据说咬后不能走路。这增加了我的恐惧。可是,当我被咬后,发现疼痛并不那么剧烈,而是一直隐隐的,我依然能坚持插秧。它咬的时候,只是像针扎的一瞬,随后疼痛会逐渐增加。这种饭粒虫并不大,常出其不意地突袭。
“双抢”(抢收、抢种,在早稻和双季稻之间)时正值仲夏,水烫。烫得我稚嫩的皮肤难以忍受。父母却没有感觉,硬逼我下水。
所以,我对水田一直没有好感。在我童年的内心深处,水田是一片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我对它的热爱是后来追加的。当进入中学、不需要下地劳动时,我常去野外散步,带着青春期无名的“愁苦”——我当时有个笔记本,琴红姐送我的。我在上面模仿李商隐《登乐游原》写了首自由体小诗,姐姐看后,只说了一个词“愁苦”。散步的时候,这些宁静的绿色水田竟开始进入我内心了。大地才开始向我敞开。现在的记忆里,恐惧逐渐消散,温暖与日俱增:我赤着脚深陷在一大片水汪汪的田地里,周围是父亲抛下的扎好的秧苗。眼前和左边是业已插好的秧苗,每条六株,一人种一条,中间有秧绳隔开。我的插秧速度是很快的,常被乡亲称道。却快不过母亲,且需很费力气才能赶上父亲。所以,我的左边(我们从左往右插)经常是母亲插好的秧苗——嫩嫩的、在微风里摇曳。这种体验很切身。这是我对大地最初的情感。
我上中学后,尤其是高中后,就开始喜欢读书。经常拿一册书,去京杭运河边读。在运河上飘来的带着水汽、鱼腥、机油味的风里。印象很深的一次是一个阴云轻遮的黄昏,我在运河边的土堆上读《燕知草》。德清籍作家俞平伯的散文集。村民扛着锄头走过,和我打招呼。不过,我一直不知道“燕知草”是什么东西。但那样一种阅读的感觉如同一株巨大的植物根植在我内心深处——一切事物温顺地伏在身边:运河、运河里挖上来的泥堆、风、桑树、草丛、水田和黄昏。
杭嘉湖地区的清明节传统气氛浓郁。祭祖、走亲戚。祭祖俗名“拜阿太”。一年很多次。拜阿太的规矩很多。必须是八仙桌,三面放长凳。南面空着,桌上点香烛。其余三面的桌上置酒筷——杭嘉湖的祖先都是喝酒的,这一点很神奇。酒筷每列十三对,酒盅和筷子须间隔放置。菜一般是七盘或者九盘。俗曰“七上八下九出头”,象征家里的时运。如果是祭神,就不需要这么多菜。只需猪头、活全鱼、炖好的全鸡,以及水果三盘、豆腐干三块。祭拜时,大门须关闭,留缝。旁边的人不可高声说话。不可触碰桌上的酒菜。更不可坐在那三条长登上,打扰神灵。期间添酒三次。家里人站立弯腰合掌拜两次,每次三下。开始和结束各一次。收筷子的时候,直接收起放入篮子,不可在桌上撞击以求整齐。小孩不可喝祭过祖的酒,但对大人很有益处。
清明节走亲戚是春节之后最大的一次。但和祭祖一起与植物都没什么关系。这多半是大人的事,孩子们只有遵守。而放风筝和吃麦芽圆子才是真正的孩子们的清明节。清明节的风大,而且顺着同一方向,最适合放风筝。方言里的风筝叫做“鸢子”。我们放的风筝都是手工制作的。材料是竹篾和桃花纸,以及用糯米煮的浆糊。清明节过后就是养蚕季节,所以家家户户开始请篾匠来修蚕匾。家里买一根十米左右长的毛竹。然后篾匠就把毛竹削成薄薄的竹篾,嵌进蚕匾破损的地方。所以,此时要做风筝可以就地取材。桃花纸同样是养蚕用的材料。是蚕蚁和小蚕阶段铺在蚕匾里的白色薄纸,形似宣纸,薄如蝉翼。
我们的风筝一般不求好看,只求飞得高远。往往做成方形,很大。放飞时需用秧绳。秧绳就是插秧时用来划定界限的绳子,绿色,十分结实。我从小是形式主义者。我的风筝总要做成电视里看来的动物模样,最常做的是燕子。我做的燕子风筝在新联中学的风筝节上获过一等奖。
清明时节雨稀疏地下着,田野里微微地发绿,各种草开始生长。水田里尚未积水。只是潮湿、柔软。放风筝的场地就是如此这般的水田。我们踩在嫩草上,欢快地跑着。风筝在微暗的空中啪啪地响——风拍打桃花纸的声音。
清明节的时候,田里长出来一种特别的植物,它贴地而生,莲花般往四处展开。叶子是小小的卵形。最重要的是颜色,是泛着嫩绿的银白色,上面有白色绒毛。这种植物的名字是我一直琢磨不出来的,方言里叫做“棉絮头”,因为它长得像棉絮。如果是老年的“棉絮头”,中间会长出一条几厘米高的花茎,花是黄色的,就像黄色棉花团。这种植物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长相,更在于用途。杭嘉湖一带用它来做一种糕点,叫做麦芽圆子,按照方言的发音应是“芽麦圆子”。用发芽的麦粒碾成的面粉和上煮熟的“棉絮头”做成的一种圆子。甜甜的,颜色暗黑而带绿。吃起来滑而不腻,是南方糕点中的上品。而且仅产于湖州东部和嘉兴。德清县内除仙潭之外便是稀罕之物。大人们的任务是发麦芽、做圆子和烙圆子。发麦芽就是把一蛇皮袋麦子扎好,放入河埠水中的石阶。温暖的春水很快就会催生出麦芽,然后去碾成粉(方言曰“轧粉”)。做圆子就是将面粉和“棉絮头”和在一起,掺上糖,做成圆子,然后压扁。烙圆子方言叫做“焊圆子”,犹如北方烙饼,只不过要多放些油,油里放上糖。麦芽圆子就贴在锅壁上“煎”。屋里顿时香甜四溢。
孩子们的任务就是去田野里挖“棉絮头”——方言叫做“挑棉絮头”。“棉絮头”长得隐蔽,须从乱草中挑剪出来。这又是孩子们清明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学回家,我们就三五成群地提着篮子去挑棉絮头。我们和大人们不一样,他们一般是用镰刀整棵挖走,然后回家洗干净,坐在走廊下慢慢地将嫩叶剪下。孩子们的手续更加简单、精致。我们只用剪刀,直接在地里的植株上剪下又嫩又肥的叶子,“棉絮头”的根和茎杆都在,可继续生长,况且可以省去在家里挑剪的功夫。
棉絮头身体弱小,而做麦芽圆子则需大量的棉絮头。有时候,我们为了贪图速度,就用另一种“白胡子草”来替代。这种“白胡子草”体积是“棉絮头”的好几倍。叶子粗大,深绿色,边缘长有白色绒毛,故名。它的味道和“棉絮头”差不多,可是不够细腻。
如今,我熟悉家乡田野里的每一个角落和挑棉絮头不无关系。我们(建伟、奥莉、红男、丽萍、芳芳和我)沿着机耕路、田埂、水渠、河滩以及桑树地和水田的交界处,到处寻找棉絮头的身影。我喜欢和女孩子结队。一般总要找别人少去的地方。比如东港或者梅家里。那边的“棉絮头”经常要比其他地方的要大出一倍。这些地方对我们而言就好像是世界的边缘一般神秘。东港水深草满,传说水中有许多“活死鬼”、“拖脚野猫”。“活死鬼”是淹死鬼的意思。我在随笔《水不是一种液体》写到过“拖脚野猫”。“野猫”在方言里代表妖怪。这种妖怪住在水里,经常抓在水边行走的人,方法就是拖住脚,攥入水中,所以叫“拖脚野猫”。但是我们结伴,不怕。梅家里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河的北岸在我们这边。其实这一带已经属于桐乡。我家所在的地方就像一座岛屿,分属桐乡和德清两县。梅家里属于桐乡。而我所在的东升和相邻的邱家浜属于德清。河的北岸全是桑树地。河滩因为面南,所以常常阳光明媚,水面开阔平静,岸上草丛光鲜,却少有人迹,一片世外桃源的样子。我们经常沿着河滩走,走到尽头,就可以挖到一篮子的“棉絮头”。在这样偏僻神秘的地方,我还与女孩子偷偷接吻,当时的电视并不普及,正因为稀有,我们模仿从八十年代日益开放的电视里难得看到的接吻场面。结果发现,接吻并没什么特别之处,除了心里有些胆怯,身体上并没有什么乐趣,只吃到了别人的口水,有点咸。但因为它的私密性,我们依然喜欢偷偷尝试。小时候,经常会做些性游戏,但是总要做到绝对的保密,不让大人知晓。
春天来了。植物们疯狂生长。许多植物直接可以成为食物。除去家养的蚕豆、豌豆、大豆、赤豆、豇豆、四季豆等等,尚有野生的马兰头、茅草根等等。
茅草根是孩子们的偏好。茅草根十分白嫩,多汁而甜。我们上学须过运河,只有一条公家的船渡我们过河。中午放学回家吃过午饭,我们就在船里等艄公。最初,艄公是每家每天出人,最后逐渐变成职业,由政府发放工资,于是人员基本稳定下来。一般在“毛狗阿爹”和梅家里的一位阿爹(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是我家远亲)之间轮换。毛狗阿爹的儿子“毛狗”在方言里其实是“猫狗”的意思。以前的人给小孩子一个贱名,为的是好养活。这两位阿爹常常迟到,我们等待的时间就十分漫长。所以,中午我们就在船舱里、船头或者岸上写作业、打泥仗、打牌、拍纸片(卡)、游泳、挖茅草根、摘豆子。嫩的蚕豆、豌豆可以生吃。比较起来,茅草根更好吃,更甜,而且不存在偷的嫌疑。有时候,我们去摘蚕豆苗的“耳朵”。豆类植物中,只有蚕豆会长处这种“耳朵”,一般隐藏在靠近顶端的叶子下面,细线一般的嫩枝上长着一只漏斗形的耳朵。并非每株蚕豆苗都会长耳朵,而且长得隐秘,所以在清香鲜嫩茂密的豆苗丛中搜寻起来是件趣事。
等到蚕豆熟透的时候,我们会在水田里点燃稻草,然后将拔来的蚕豆连带豆箕一并扔进去,豆荚就在里面噼啪乱蹦。等到火灭了,拨开灰烬,豆子已经煨熟,吃起来香脆可口。
一些鬼主意多的大孩子,比如湾里的建锋、邱家浜的晓炎喜欢烧茅草。秋冬季节,茅草枯萎,一片枯黄,此时一根火柴就能让绵延数百米的茅草毁于一旦。不过,有时候,燃烧的茅草会殃及附近的稻草垛。他们就会被成人大骂。所以,这样的事我是不干的。我在故乡的这些孩子中,是不太会胡来的。我从小就内向,没有几个年长男孩的野气。我更喜欢挖“棉絮头”或者挑马兰头这样秘密的不动声色的事,而不喜欢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就好像我现在喜欢独自阅读、写作,而不喜欢与他人打交道。这种马兰头不是一般所谓的马兰花。可是,马兰头的确会开花,一种花瓣淡紫、花心橘黄的花,形似向日葵,只有一元硬币大小。开花的马兰头茎杆比较长,有二三十厘米。但年幼的马兰头只有四五厘米,叶子鲜嫩,竹叶状,是食用的最佳对象。如今,上海的菜场偶尔能见到这种马兰头。上海的一些餐馆能吃到一种马兰头拌香干的土菜。小时候,家里很穷,所以香油拌马兰头是常吃的菜,有时候几个人只围着这一道菜吃。所以,提着篮子,带着剪刀,去一些潮湿的角落挑马兰头是我儿时生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兰头喜欢长在潮湿阴暗处。我家屋前的河滩、屋后的桑树地旁就有很多。田埂这些地方的马兰头因为日晒较多,又老又小,吃起来不香不嫩。
村子东边的奥莉家门前的水沟旁长着一丛洋芋艿。其实它真正的名字叫菊芋,方言一般叫洋生姜,我们村上的叫法是有问题的。“洋芋艿”的地下根茎可以腌制后再吃,黑色的,很脆,是什锦菜中重要的一味。前不久与小跳跳漫步沙家浜时,在洲岛上见过一大片“洋芋艿”,当时很兴奋。“洋芋艿”的茎杆大概手指粗,高过人头,花橘黄色,茎杆内部是棉质的东西,小孩子常常把老来的茎杆切成段,点上火,当香烟抽。
南瓜、番薯的茎吃起来是另一种味道。这都是被贫穷逼出来的。不过,南瓜茎、番薯茎的味道其实不差。去皮,凉拌,很好吃。母亲尤其喜欢吃番薯茎。她常常命令我去谁谁家弄些番薯茎来。我则提心吊胆地来到指定地点。我家已经多年不种番薯,所以只能“偷”。虽然偷的不是地下的番薯,但是摘掉茎杆,总会影响番薯的生长,主人总会介意。不过,村里人相互都很熟悉。见到了,只是说一下,只有一些小气的糊涂老头会破口大骂。番薯地经常在一些坟堆的旁边。旧时的坟总是砌成屋子模样,耸立于地面,正面留有十字形的“窗子”,棺材依稀可见,更增添了恐怖的气氛。加上坟边上总是种上些荆棘之类的,十分阴森。我放学回家,一般都是黄昏,日头低垂,天渐渐暗去。在此时摘番薯茎,恐惧随之增加。
清明节的另一个重要项目就是蚕花节。蚕花节就在清明节这一天。蚕花节自古有之,只是中间被历史割断。小时候,清明节总要去“游含山”。含山是距我家几公里的含山镇上一座小山。它的蚕花节恢复得较仙潭要早。“游含山”这一风俗的流传大概就是古时蚕花庙会的蜕变。含山并不高,一百米左右,很小的山。只不过方圆几十里就这么一座,所以稀奇。传说,洪水时代群山见大水来临,纷纷西逃,只有这座山最蠢,没逃。于是留下来成了这里唯一的山。我猜想,所谓“含山”其实是“呆山”的讹化。“呆”在方言里一直念做“ái”。普通话的普及将这个字生硬地统一为“dāi”,新华字典清清楚楚写着,这个字不能读“ái”。方言在国家利益面前总是微弱的。据说含山是马头娘娘亦即嫘祖的故乡,是桑蚕文化的起源地。一到清明节,附近的乡民或步行或骑车浩浩荡荡地往含山进发。在那里,我才知道“蚕花”的意思和模样。原来农民为祈求接下来的蚕茧的丰收,来向马头娘娘拜求蚕花,作为好运的象征。后来仙潭亦恢复蚕花节。仙潭的蚕花节不像含山以神话为依托,而以历史事实为蓝本,是想象的结果。据说西施北上吴国,途径仙潭,遇十二位采桑女在她的轿前起舞,于是她将随身的鲜花散于采桑女,祝愿她们蚕茧丰收。后人为纪念西施散花,发明了蚕花庙会。如今,在西施故里——浙江诸暨就有西施殿,殿内西施长廊画有“德清赠花”,应是仙潭之事。所以,仙潭的蚕花庙会与含山不同之处就是蚕花姑娘。含山的蚕花是祈福得来或者直接购买的;而仙潭的蚕花则由每年遴选出来的“蚕花姑娘”坐在花轿中撒放。是日,仙潭万人空巷,附近村民纷纷云集,仙潭路、健康路水泄不通,蔚为壮观。蚕花节又是仙潭古时的情人节。民间传说,那天,在胭脂弄、寺前弄一带,青年可以光明正大地摸姑娘的乳房。如今,仙潭剧院后尚有一条弄堂叫做“摸奶弄”。现在流传下来的当时民歌《轧蚕花》中亦有露骨的场面:“邻村阿哥早等待,一见阿妹挤身旁。一把大腿偷偷捏,姑娘脸红薄嗔郎。”
“蚕花”其实是用纸或布做的假花。但对于农民来说,它是一种圣物,具有某种超验力量,能够左右我们人世间的事功。比如,清明节,我们会在大门上别一束艾草,用来驱邪降幅。
孩子们盼望的节日,清明过后就是立夏。立夏这天,家家户户要做“立夏饭”。立夏饭的做法很考究,主要突出一个“野”字。一般在野外用砖头搭灶。米、油、盐、味精、咸肉等物可从家中自取,而豌豆、菱角则要从野外“偷”来。所谓“偷”就是不要从自家的地里摘。这一天,孩子们去别家偷豌豆是没有人管的。菱角是湖里捞来的——当然我长大后再也不能在湖里见到随处漂流的野生菱角了。最后一种必不可少的佐料就是“薤”。每家的菜园里都会种。它细细嫩嫩,叶子是线形的,球茎白似珍珠,形似葱蒜,却具有葱蒜所不及的香味。立夏饭的原料主要是豌豆和糯米,但缺少这种薤,味道就会变样。孩子们的野外立夏饭所用的薤必须是野生的。而且这种野生的薤出了东升这个小村庄,都不太能见到。它长在村东桑树地里的两个大坟上。这两个大坟高达四五米,是我们玩耍的好地方。上面的野生薤,比家养的长出数倍,味道更香,且遍布坟头,很神奇。这两个大坟据说是镇上大户人家的。大概已经相当古老,我们从来没见过镇上什么人清明节来上坟。在我去西安大学的后两年,政府平整土地,将这两个大坟挖掉。据说挖出无数珍宝。全被县博物馆没收。村里的人暗自去挖,仍然挖到不少破碎的玉器。一个客居我家在这里打工(挖泥,卖给砖瓦厂)的四川人就挖到一只玉蝉,据说卖了三千块。我没能目睹坟内部的景象,是件憾事。我甚至猜想,这两座坟可能与和明代兵部侍郎胡尔慥有关。史料记载他葬于孟溪村,但不知确切所在。我们竟然一直在吃古人的坟上长出来这种特殊的薤。
烧立夏饭的灶在野外,但最好在桃树下。如果找不到桃树,就在灶旁插一枝桃花。于是,这株桃花随之变得神秘。故乡的这些特定习俗一直在引领我进入世界的神秘一面。
小时候,一直很好奇家乡那些植物的归属。那些桑树地大大小小、形状各异。中间只有浅浅的沟为界,但是它们属于不同的人家。在一块桑树地采桑叶,父母亲就会告诉我相邻的地是谁家的,他们的人品怎样,有过什么故事,他们的蚕养得如何,桑树何时喷过农药,何时才能让蚕食用。喷到邻居喷过农药,交界地方的桑树就要留出半株不采,以免蚕吃了中毒。水稻、豆子、蔬菜也是有主人的。即使随便摘一朵小花,我心里也清楚这是摘了谁家地里的花。
村庄房屋前后的树同样分属不同人家。父母亲经常会指着某棵树说,这是谁家的树。这些树都是父亲一代小时候种下的。每一棵树代表一种记忆。这些树来自于那个遥远而贫乏的年代。他们分布在村子各处,犹如时间一般环绕着我们的生活。家门前那株元宝树是我家的——它可能是现在村上最庞大的树,右边的枣树是文松阿爹家的,榆树是法生大伯家,左边的杉树是法荣伯伯家的,白榆是阿芳家的。我家其他的树则在屋后,是一株梧桐,几年前它在台风中倒掉了。很久以前,炳荣伯伯家旁的弄堂里有自己长出来的株枇杷,村西河埠右边的郭树在死去前是村里最硕大的树,好像是阿芳爷爷的。左边是一排泡桐,大概是奥莉家的。河埠往北的竹林,最大一块为奥莉和阿芳两家所有,小一点的是建伟家的,更小的三角形的才是我家的,其实是我的西海爷爷留下的,没人打理,竹子越长越小。我家竹林对面的几棵郭树是西海爷爷的。他去城关镇为一家做钢材的乡镇企业看门前,就在树下的一间小屋里住着。这是村子的最西边,所以他被叫做西海爷爷。他是我爷爷的亲弟弟。去他家,要经过竹林和建伟家之间的狭长小路。屋后是一个野坟堆,野竹子中隐约能看到许多褐黄的骨殖甏。这是一处极静僻的所在,屋前是竹林以及一条小径,右边就是那一排郭树,屋后是野坟堆,更外面是浩瀚的桑树地,以至于我后来读到某些隐者的住处,直接的想象来源就是西海爷爷的这间小屋。
故乡是水乡。水上多水草。这些水草是用来喂羊的。它们覆盖了整个东升浜。它们同样属于不同的主人,护卫这片水域。水边是一丛一丛的芦苇和芦竹。芦苇细小些,颜色褐黄;而芦竹则是粗壮的,更高大,叶子和身躯都是翠绿色的。故乡的芦苇不多,我家的竹林濒东升浜的地方有一片,在我们这座“岛屿”东北角荒芜地带的水泽里也长了许多。其他环湖和临河的地方一般只长芦竹。芦竹的归属权依据各家的田地。东升浜的东北角都是我家的水田和桑地,所以,东升浜与新开河交界处的一大片芦竹以及“湾斗里”的一长条芦竹都是我家的。这是我十分自豪的事情。因为,一到春天,我们砍下芦竹的花茎,可以做笛子。芦竹的花茎是一枝空管,而且不像竹子那样有节。所以,只须根部一端劈断,顶部本来就是长实的,不通气,纵向划开一条缝,就可以吹响。逋—逋的声音。顶端可以削短,留下一根花须。就是一只很漂亮的“笛子”。
小时候的植物带着各种各样奇怪的信息。可是,我对植物的混乱而神秘的直觉认识,逐渐被一本叫做《植物学》的中学教材规训。我花大力气抄这本姚一平借给我的《植物学》,那是他哥哥的教材。我边抄,边修改,补充进平时收集的其他资料。同时抄录的是我在《天文学》里写过的《多四季论》和《宇宙与太阳系》。我的近视眼就是在这次抄录工程中留下的后遗症。
这本《植物学》有助于建立起关于植物的整个知识体系。我习得了关于植物的分科、拉丁名、生长环境、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或木本、灌木或乔木、真菌或裸子植物、被子植物、根茎叶的命名、哪些部分可以入药或作其他用途。如今我对植物的描述语言,大多还保留着这本书的语言印迹。
我对种植植物的偏爱很早就开始了。我慢慢开始种植植物,想将他们网罗到自己的世界里来。
最早的尝试可能是将河里的蕰藻捞来,放在一只水果罐头瓶里。放上一些鹅卵石,养上在河埠很容易就抓得到的小鱼——一般是大眼睛鱼或者小鲫鱼,以及一两只螺蛳。然后就放在桌上整天端详。看鱼在这个小天地里如何生活。它们缓慢地游着,似乎很满足,但没几天就会死去。我想,这个瓶子太小。我要寻找更大的场地。
我曾经试图囊括整个世界的雄心不知道起源于何处。我在《地理学》里说过要画一张详细到每个村庄、每条河流的世界地图。我又做了一只世界模型,用淤泥塑成地图的样子,然后挖得高低不平,高的地方是山,低的地方是海。我撒上油菜籽,想让“世界”变绿,并且模仿各种植被。我还找来沙子,撒在撒哈拉、塔里木这些地方。另外一个浩大的工程就是在屋子东边的空地上,建一座植物园,网罗全部植物。于是,我开始收集各种各样的植物。
我一边抄录《植物学》,一边临摹书上的植物插图,比照我眼前的世界,看故乡有哪些植物。然后从其他地方弄来各种植物,种在我的植物园里。
这座植物园的雏形是我的“花园”。最早种花的想法来源于小学课本上老舍一篇叫做《种花》的散文。小时候毕竟是一个可以信任任何事物的年龄。虽然,没过几年我就再也看不上那样的文章。
邻居建红姐比我大几岁。他们听崔健、小虎队的时候,正是我进学校、开始生长出各种奇怪想法的年龄。我的“种植史”成为现实和她有关。有一天,她从蜜饯厂里的同事那里要来一种特别的花,藤形的,茎叶很瘦弱,很长,花圆形,淡紫红色,很美,而且花的边缘是波浪状的,犹如铅笔刀削下来的片状物,她说这叫“铅笔花”,就用一只脸盆培上土,放在阳台上。她家的阳台和我家的平台只一墙之隔,攀着墙就可以爬过去。我趁没人时,爬过去,偷来一枝。这种花是可以扦插的。我用小盆放在平台边的屋顶上,可以接受雨露。花活了,但是不久就枯萎下去。我第一次养花的经历并不成功。
四年级的时候,班级里搞花展。同学们搬来了各种盆花。我印象最深的是沈美丽搬来的一盆太阳花。摆放在班级面东的阳台上。太阳花五颜六色。作息与太阳一致,白天开、晚上闭,与睡莲一样。沈美丽给我看了花籽。银色的,就像虫卵。这一次目睹更加助长了我养花的欲望。
有一次,去外婆家做客。剑锋让我去他家玩。我看到了他家院子里密密麻麻的鸡冠花,很是羡慕。于是在外婆家吃过晚饭,就去剑锋家的院子里拔了几株,他家的院子是通外部的。小时候,我经常偷东西,包括前面去摘建红姐家的铅笔花,以及这次偷剑锋家的鸡冠花。小时候当“小偷”,偷一些别人不看重,我却十分重视的东西。我“偷”过学校的铅球。放学后,我看到操场上蹲着一只很大的铁球,就放进书包抱回家,铁球沉得我的书包长出瘤来。第二天潘老师一个班级一个班级的询问。我却不敢支声。当时我的确不知道这是铅球。这只铅球后来被父亲当作废铁卖掉。我们几个男孩曾经去偷过皮革厂的胶水。最惊险的一次是去镇上的造纸厂偷白纸,用来做草稿纸,结果被人发现,穷凶极恶地追了我们很久。偷得最多的是蔬菜。我经常在母亲的怂恿下去偷别人家的南瓜、冬瓜、韭菜、大蒜、豇豆、白菜。最多的时候是在暑假期间,父母都上班不在家,我的午饭常常是去别人家地里偷些菜回来自己做着吃。有时候是去各家地里收集他们收摘残余的豇豆、赤豆、绿豆,回来煮八宝汤喝,解暑。当然我家的东西也经常被人偷走。在村子里,偷东西几乎是人尽皆知,大家相互默契的事。我家的鸡鸭就经常不翼而飞,油盐会无端减少。
在农村,孩子的性格并不会像城市里那样“文明”地进展。我曾经不小心用伞骨打过一只外婆村上红兰家的猫,猫就在我们面前凄惨地死去。我与红兰是好朋友,红兰的母亲与我母亲是结拜的姐妹,可当他们询问是谁打死了猫,我在一旁心跳加速、面红耳赤,却偷偷地不敢承认。虽然,我的确在学校里学到过列宁打碎花瓶坦白错误的故事。
如今我从“小偷”蜕变为一个与文字打交道的人,大概都源于不愿以正常的方式与人交往这一点。
从剑锋家偷来的这几株鸡冠花被我洒上水,放在东门外过夜。第二天我就开始为它们营建一座花园。东门外有一列堆好的瓦片,它西边连接着我家的墙,我就以此为基础,在剩余两面插上篱笆,翻松土壤,种上了鸡冠花。我辛勤浇水,经常去看望它们,起先它们病怏怏的,不久一些叶子和花枯萎了,长出新的枝条。我的这次种植终于成功了。这几株鸡冠花生生不息,在我的花园里繁衍了许多年。
我又从外婆家弄来凤仙花的种子。古代的女人用凤仙花染指甲,所以又叫甲花。但我试过,凤仙花的花瓣的确包含了很多红色的汁水,但不足以将指甲染红。凤仙花的名字正好和小姑姑重名。所以,我对它的感觉是很特殊的。建伟家种的凤仙花则是从我这里移植过去的。建伟是我的邻居,与我同岁。
以后花就慢慢多起来。姨妈村里的张玉是我小学同学,他给我看过一堆美人蕉的块茎,黑漆漆的,犹如涂了油漆。自此以后,我就对美人蕉发生了兴趣。我从剑锋家的院子里挖来一些美人蕉,美人蕉生殖力繁盛,适应性强,长得十分很旺盛。建伟和金金(奥莉的弟弟)就从我这里移植过去一些。我的牵牛花(喇叭花)似乎也是从剑锋家弄来的。牵牛花蔓延开来难以收拾。从一本杂志上学习到可以种不蔓延开去的牵牛花,要不断地剪掉长出来的新枝,让它从藤本植物变成矮小的草本。
这本杂志就是《植物学》杂志。我都已经忘却这本杂志的所在地。我在邮局定了一年,双月刊,六本,当杂志寄到办公室,班主任转交给我时,几乎是扔在桌子上的,并且说: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却像宝贝一样读起来。通过抄录《植物学》我已经了解到许多植物的学名,他们的模样,分布的地带。但是,植物学为我打开了新的世界。虽然许多文章很专业,看不懂,但是我依然了解到桫椤、铁树、葱兰等等各种植物的种类、习性以及分布地带。我从母亲厂里弄来几株葱兰,就是因为看了《植物学》杂志才一眼认出这种葱一样的植物就是葱兰,而且会开白色的纯洁的花。
我的夜来香是从外婆村子里一户人家的屋前搞到的种子。它的种子很特别,黑色,上面有复杂斑纹,酷似地雷。夜来香刚发芽的时候是两片对称的大叶子,就像切开的苹果。植株相对较大,成熟的时候一株夜来香的叶丛直径会有一两米。夏天炎热的时候,正是它的开花时节。芳香四溢。林逋的“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意对我而言就是夜来香在黑暗里游动的夏夜。夜来香会招来一种蛾子。身体很大,嘴细长,就像蜂鸟。它们扇动着小小的翅膀,在夜来香粉红色的喇叭形的花冠里吸食花蜜。
牵牛花的喇叭比夜来香大。长得也不精致。一年夏天,台风将我家屋后的一棵水杉(它是法荣伯伯家的)刮断。我抬过来将它放在花园里,靠着平台。于是,那些被我压抑着的牵牛花终于得以四溢爬行。到最后,我不得不剪断某些牵牛花的花茎,来减轻树干的重负。牵牛花将水杉的树干包裹得严严实实,远远望去就像是一朵绿色的云。夏天,绿云上就会闪烁紫红色的星星。奶奶每次到我家来,总不知道这是什么,就说:这荷兰豆长得这么茂盛!当然,对于奶奶这样一辈子几乎不出村庄的女人(奶奶和我说过,她这一辈子只到过仙潭镇上一次),很多事物是不可理解的。种植是为了收获,为了温饱。种花这样无功利的事当然进入不了她的意识。我一开始就在做这样不切实际的事,以至后来去写作,其实是相承于地理学、天文学、植物学等等无功利的东西的。
花园旁边正好是自来水龙头。浇花是很方便的。再后来,花的家族越来越热闹,月季、菊花、蝴蝶花、太阳花、海棠花等等。我都记不清它们的来源了。
到最后,一个疯狂的念头终于抓住了我。我要建一座囊括所有植物的植物园。
我的步骤是这样的。先把瓦片堆背后更大的一片空地划入势力范围。用篱笆围起来。然后就到处搜罗植物。当然,地里面本来就生长着我以前种的美人蕉。显得很深邃。我把以前种在花盆里的仙人掌移植到这里。我的目的是让各种植物自由生长,让这一块小小的土地变成一个植物群落。瓦片堆背后因为潮湿,长出很多真菌来。它的下面是一条沟,用来排放下大雨时的檐水。我就往深挖,想让它变成一条微型的河。我在靠墙的地方挖了深坑,想让它变成微型的湖。我养上一条鲫和一些从湖里抓来的鱼苗。湖水没有源头,我在园子另一角挖了稍浅的坑作为水源,和前面的坑之间用一条小沟连接起来。小河经过那片葱郁的美人蕉。当然这个水源依然无水。我就一桶一桶从东升浜里拎过来,倒进去。一个小型的宇宙在这里运转。我开心得忘乎所以。
我移植来的植物都是附近村庄所能见到的,除了不能在这个小园子里生长的庞大乔木。我种了桑树、杨树、水草、绊经草、马兰头、荠菜、“棉絮头”、白胡子草、玉米、蓟、笤帚草、鸭舌草、水稻、稗草、蕰草、癞蛤蟆草、葱、姜、蒜、薤、南瓜、黄瓜、西红柿、茄子、野藤以及各种豆类。它们在里面肆意生长。让百草园异常幽深。我就在里边小心地走,观察每一种植物的生长过程。芽如何破土,如何变成叶子,叶子如何伸展,茎杆怎么生长,花如何开放。这是很有趣的“事业”。我在里面学会如何听从大自然的神秘规律,如何获取大自然的微妙信息,如何与万物共处。
扦插篱笆用的是芦竹。扦插进去后,很多就开始生根发芽。有几株甚至长得十分茂盛。有一年,竟然出现了一个麻雀窝,这是对我“事业”的极大鼓励。最后小麻雀们在园子里乱窜,这是我的植物园最繁盛的时期。后来我去城关镇的德清一中上学。植物园就日益荒芜下去。最后被母亲收回,改造为菜园。直至今天,里面的花草只剩下美人蕉、月季、仙人掌、蝴蝶花、桑树。那株野藤攀着墙壁长得十分茂盛,以至于几乎要覆盖住了整个平台,对墙的腐蚀很严重。前年夏天,终于被我和小荣伯伯一起剪除,如今只剩枯死的藤条躺在日益颓败的平台上。那株桑树被父亲折去顶端,一度长得很慢,今年夏天我回家,又看到它的侧枝拼命窜向空中,竟有四五米高了。
我找到一种野生大豆,就兴奋种到我的植物园里来。第一次认识野生大豆是在初一课本上一篇叫做《祖国的大豆》的文章。文章最后提到一种野生大豆。通过文章的描述,我在外婆家附近的草丛里找到了它。豆荚的模样和家养的大豆几乎没什么差别,只是小些,绒毛更多。但它是藤本的,喜欢攀爬在其他植物的身体上生长。我种的野生大豆长得十分健康,结了许多豆荚。文章中说,野生大豆营养丰富,是喂猪的好饲料。我决心“推广”它。我试图推广的还有牵牛花。牵牛花的种子和野生大豆一样繁多。每年我能收获一大堆。于是,我在口袋里装满野生大豆和牵牛花的种子,在上学的路上,沿路乱撒。
第二年,从我家到新联中学的路上,长出无数的牵牛花和野生大豆。我的植物学生涯便在这次浩大的工程中接近尾声。自从我进入德清一中,一个月偶尔回一趟家,已经无力经营这座植物园了。我渐渐陷入文学的沼泽,童年的一切渐渐由事实蜕变为记忆埋伏在我内心深处,就等待词语走过,然后伏击它们。
如今,我每次回家。走在以前走过无数遍的路上,看到路两边的牵牛花和野生大豆,我无比自豪。同时记忆的植株开始迅速生长,将根系缠绕在头脑里。这是我每次回乡不得不遭遇到的事情。
当我向别人指出,这路边蔓延的植物,是我许多年前不切实际的壮举,一般没有人会相信。但是,当重新面对生息了许多代的这些植物,想起我和它们的祖先那些秘密的交往,就令我温暖,这些植物是我与故乡的真正联系。在这片土地上我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没有这段时光,我现在将一无所有。
我相信,这些世世代代繁衍的植物,会代替我,一直守护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