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特简史
2009-04-20许健
许 健
他的戏剧发现了在日常废话掩盖下的惊心动魄之处,并强行打开了压抑者关闭的心灵房间。
——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公告(瑞典皇家科学院)
2008年12月24日,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因食道癌病逝于伦敦医院。忙于庆祝圣诞平安夜的人们直到第二天才蓦然发现,一代戏剧大师已经向这个世界行了最后的谢幕礼。
1930年出生的哈罗德·品特是战后英国戏剧史上最璀璨的一颗巨星,是继萧伯纳和贝克特之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三位英国剧作家。在很多评论家眼里,品特是自萧伯纳之后最优秀的英国剧作家。
二战以后,英国戏剧前后出现了两次浪潮,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不少剧作家随着潮水的退却已被遗忘。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的第一批剧作家中,惟一历时半个世纪而长盛不衰、直到今日辉煌依旧的剧作家就是哈罗德·品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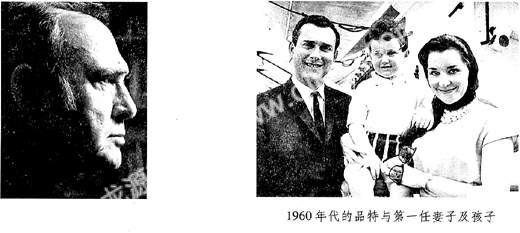
在战后涌现的众多英国剧作家中,品特不仅是最优秀的,也是最有个性的剧作家之一。由于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和接下来威斯克的三部曲的上演,战后英国戏剧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呈现出以关注社会现实、写实为主的格调和色彩。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不论是第一批剧作家,还是1968年后出现的大卫·埃德加、大卫·海尔和霍华德·布伦顿等年轻一代,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社会评论家,因为他们都力图用他们的戏剧来反映社会和改造社会。相比之下,品特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立场、神秘而独具魅力的风格使他在同时代作家中独树一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远离了社会。事实上,品特通过探索戏剧人物的内在关系,反映同时代剧作家所没有触及到的、社会的深层现实,这使品特在战后英国戏剧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一方面,他的艺术风格和戏剧主张不同于同时代的大多数剧作家,但另一方面,他通过人物内心世界关注社会现实,与时代共鸣,从而与主流戏剧最终合流。
家世与青少年时期
1930年10月,品特降生于伦敦东区一个不算殷实的犹太家庭。欧洲的犹太人都是流民,但品特的祖上究竟来自匈牙利、西班牙还是葡萄牙,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个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的问题,却让品特困惑了一辈子。他似乎不断在考证着自己的来源,且在作品中时常有所反映。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品特不仅模糊了人物的身份来源,而且永远将其来源作为一种悬疑贯穿始末。他在剧作中似乎一直都萦绕着询问和思考:“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的祖先是谁?”。
品特的父亲开了个小裁缝铺,夫妇俩都是勤劳本分,沉默寡言的手艺人。尽管他的父母也爱读小说,但这个家庭显然不是个书香门第。品特曾回忆说:“我的母亲爱读克罗宁和阿诺德·班尼特的小说,我父亲则喜爱韦斯特恩的作品。但是我家里的藏书很少,因为我们全都去图书馆借书看。我们买不起书。”
品特从小性情就显得敏感而内向。对于他来说,最美好的记忆是二战前孩提时期,作为家里的独子,那时的他虽有些孤独,但丰富的想象力和充满爱和阳光的家庭环境使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少年品特的眼里,他家屋后那个长着一棵丁香树的花园就是最美好的天堂。他常常一个人呆在这个宁静、和谐的花园里,与幻想的玩伴嬉戏。
1944年的一天,呼啸的炸弹把品特的伊甸园变成了一片火海。二战的炮火葬送了品特儿时生活的恬静。长达数年离开父母的疏散生活给品特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创伤记忆。战争炸毁了他对美好的回忆,炸毁了他所有的安全感,生活和家庭的完整性破碎了。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恐惧和威胁的记忆。作为一名犹太人,盖世太保、大屠杀所反映出的人与人之间的残暴,使他在以后对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暴力行为有一种本能的敏感。
同时,德国纳粹的那些暴行也使品特沉迷于对人类关系内在现实的探索。因为二战给他留下的最大困惑就是,战争中那样惨绝人寰的暴行和屠杀竟然是德国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犯下的。这种文明与残暴并存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内心现实?是何种心理使他们变成了纳粹?品特的这一兴趣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德国情结,为了找到答案,他说他甚至读过海德格尔等一些德国名人的传记。这也是为什么品特在他的戏剧创作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暴力、迫害、恐怖和背叛的主题上来。他试图用戏剧的手段来探索社会暴行外表下的深层内涵。

二战结束了,暴力横行的状况却并未改观。品特生长的哈尼克地区是一个人群混杂而是非滋生的地方。为了躲避两次世界大战,备受迫害的大批犹太人从20世纪初就开始聚集于此。犹太人、英国人、爱尔兰人、黑人等等族群杂居在一起,民族的复杂和沟通的障碍使得居民们为了生存空间,经常冲突和斗殴。而战后新纳粹主义在英国的抬头,让犹太人继续成为众矢之的。对于这段经历,品特曾这样诉说过:“每个人都在这里那里遇到了暴力。……当时,法西斯在英国正死灰复燃,我也好几次被卷入了那儿的殴斗中。只要你看上去稍微有点像犹太人,你兴许就会有麻烦。我去犹太人俱乐部,在铁路拱桥边上,有不少人手里握着破牛奶瓶子,等在一条我们必须要经过的很特别的巷口。要摆脱困境只有两种办法:一是纯粹的身体拼杀,但我们对于破牛奶瓶子无可奈何,我们没有这样的玩意儿。另一种就是对他们说点什么,你知道,就是‘你好吗‘是啊,我好极了‘哦那就好了,是吗?说着说着,就朝有光亮的大路上拼命赶……那时,那儿的暴力事件太多了。”新法西斯分子不断在街头挑衅滋事,更使品特切身体会到暴力和威胁的普遍存在。这些经历使品特对一切不平之事深恶痛绝。
品特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对于品特来说,中学毕业后在哈克尼的那几年就是他的大学生涯。品特和五个毕业于哈克尼唐斯文法学校的朋友形成了一个小团体,这个团体对品特产生了终生的影响。他儿时喜爱思考和想象的习惯在这一阶段成熟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让品特无法忘怀的青春期小群体很像他后来作品中出现的“俱乐部”、“房间”意象,一方面,它意味着品特在青春期对男性知识群体的追求变为现实。哈克尼群体(Hackney Group)是一个由纯男性组成的少年帮会,成员都有着类似的家庭背景和艺术爱好。在他们当中,品特是公认的文化人。他的好友沃尔夫曾这么说:“他(品特)那时对我们的影响很深,是他让我们读托马斯、叶芝和韦伯斯特。”
品特在这一经历中的最大收获是,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外在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一方面,他发现哈克尼群体不仅意味着精神、友谊上的享受,同时,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群体”就像他剧中的“房间”和各种神秘组织一样,也意味着个体成员在个性方面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品特的传记作者比林顿曾写道:“这一群体隐含着一种很强的行为规则,一些不成文的‘法规。就像品特后来有一天意识到的那样,任何违规行为都会意味着严惩,这也在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他对‘背叛这一主题着迷的心理原因。”所以,当他享受着群体带给他的安全感和思想优越感时,品特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对个人愿望的痛苦压抑。也就是说,品特从这一经历中,切身体会到了个体与“俱乐部(小至任何团体,大至社会体系)之间的本质关系:当一个人(成员)向他的组织索取的时候,他为之付出的代价却是个人意志的丧失。
另一方面,通过这一时期的经历,品特还发现人与人之间在心理层面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关系”,是发生在“房间”里的故事。品特觉察到,尽管成员之间有一种忠诚的纽带,但仍无法抗拒彼此间存在的权望,而这种欲望是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因。后来,历经几十年的困惑和思考,他终于发现,这种在心理层面上人人具有的权力欲望就是社会权力的根源。关于哈克尼群体的内部,品特在访谈中很少提及,但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侏儒》( The Dwarfs,1991)中,他运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发生在三个青年身上故事,详细地描述和探索了那一时期的经历给他留下的影响。
青年时期的品特身上似乎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疾恶如仇,另一方面带有一定程度的悲观情绪。在这一阶段,还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即1948年,18岁的品特拒服兵役。对于品特来说,这是他的第一次严肃政治性行为,他说:“我很清楚战争带来的灾难和恐怖。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为战争出力。”为此,他曾两次被送上军事法庭,险些蒙受牢狱之灾。品特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对政府的反叛情绪是他性格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对权力机构的义愤情绪逐渐发展成为对一切恃强凌弱的愤怒,尤其是对政府的谎言、和西方世界自以为是的愤怒,以及对弱者的同情:“在任何情况下,品特都本能地站在受害者一方来对抗任何形式的权威”。

虽然品特为了道德和正义拒绝服兵役,但是他却没有像同期的很多作家那样,把自己的写作目的定位于改变社会现状,相反,他反对政治宣传式的戏剧创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对政客的不信任。品特在1967年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政治让我感到厌倦”。即便是在日后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时,他仍旧对艺术的社会功效深感悲观。
“威胁喜剧”时期
如同莎士比亚一样,他的戏剧生涯也是从舞台走向了剧本。上中学时,品特在戏剧方面就已崭露头角,扮演过麦克白和罗密欧,还获得了专家的好评。恩师约瑟夫·勃瑞利将他带进了莎士比亚、韦伯斯特等戏剧大师的艺术圣殿。他尤其欣赏韦伯斯特的语言,经常和老师一起在散步时大声背诵《马尔菲公爵夫人》(Duchess of Malfi )或《白魔)(The White Devil)中的台词。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品特在一些剧团跑龙套。1951年,他在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中扮演了一个角色。1953年,他参加了一个剧团,开始在英国和爱尔兰各地巡回演出,后以大卫·巴伦的艺名在伦敦的剧场驻场演出。为了维持生计,他做过侍者、邮递员、保安,同时以大卫·巴伦的笔名发表诗歌和小说。他在英国的剧场里演出12年,演了25个角色。据他自己回忆,最喜欢演的是阴暗的角色,“他们让你全身心投入。”他创作的剧本也一向令人不快,终其一生都是如此。“戏剧本来就是冲突、压抑和不宁。我从不写快乐的东西,但我能够享受幸福的生活。”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对品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就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贝克特的作品。品特后来回忆说:“不管你信不信,我是英国最早接受贝克特的读者之一。那时,我正随马克在爱尔兰演出,偶然看到了一本小杂志《爱尔兰作品》……里面有一篇贝克特的《瓦特》片段,那真是一种过电的感觉。而在那之前,我从未听过他的名字。”其实,贝克特只是对品特产生影响的作家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品特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如乔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普鲁斯特和海明威等作家的作品,他们对品特戏剧中诗一般的风格和多声道话语模式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品特的戏剧创作开始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最初,品特的文学写作主要集中于诗歌和小说。1957年,他在布里斯托尔大学戏剧系学习的朋友亨利·沃尔夫请他写一个剧本。它就是品特的第一个剧本《房间》,也是他的第一个“房间剧”。起初,观众对这个充满絮絮叨叨“废话”的戏并不买账,评论界也是恶评如潮。品特却对此不以为然,他曾在杜塞尔多夫冒着观众的倒彩,顽固地谢幕34次,甚至直言要和观众陈旧的审美趣味斗争到底。
正是凭着这份自负的坚持,品特围绕着“房间”和“闯人者”这一基本的框架,写出了一系列的作品:《生日晚会》、《送菜升降机》、《看房人》、《归家》等。直至《送菜升降机》上演,品特才大获成功。1960年的《看房人》连演444场,确立了品特在英国戏剧史上的地位。从前被评论家所诟病的“封闭空间加废话”的戏剧风格也成为了英国新的戏剧风尚,被冠以“品特式”(Pinteresque)和“威胁喜剧”(Comedy of Menace)的名号。
“记忆剧”时期
上世纪70年代,品特成为了英国皇家剧院的副艺术指导,他在这一时期创作上的最大特点是向“记忆戏剧”的转向。这个时期,每当谈到写作时,品特的访谈中就多了一个有关“记忆”的话题。1971年,品特接受法国记者梅尔·格索采访时说:“有些事,你觉得你记得,但实际上,它根本没有发生过……人在脑中想象了那么多的事,这种想象中的念头和真实发生的事情一样真实!”
出于对“时间”和“记忆”的浓厚兴趣,品特在1972年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改写为剧本。但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并不能完全满足品特对“记忆”的探索,他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写出了《风景》、《沉默》、《昔日》和《虚无乡》等一系列“记忆戏剧”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中,时间成了一个可以自由穿梭的隧道,而记忆也成为了一首飘渺的诗歌。
这种创作上的转向,与品特个人生活上的变故颇有关联。品特的第一位妻子维维安·莫珊特是一位女演员,两人50年代在的巡回剧团相识并结婚。莫珊特曾经在品特早期的多部作品中扮演角色,品特也承认自己剧中不少女性角色的灵感来源于莫珊特。但这些却无法阻止这段婚姻从60年代起就出现的裂痕。有7年的时间,品特与女演员琼·贝克威尔暗通款曲。从1975年开始,他又与女作家、编剧安东尼娅·弗雷泽恋爱。正因为如此,爱情与婚姻,忠贞与背叛等悖论成为了品特脑海中纠缠不休,挥之不去的主题。曾在中国热演的《情人》和《背叛》就是这段生活经历的印证。1980年,品特结束了与莫珊特24年的婚姻,与安东尼娅结婚。但莫珊特一直未能从痛苦中走出来,两年后死于酒精中毒。
对于品特来说,整个20世纪70年代是一段极度困惑、压抑的时光。这一系列“记忆戏剧”作品的出现是他在思想、婚姻和写作上坎坷、郁闷的结果。所幸的是,这一状态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得以终结。1982他的《他乡》三部曲——《维多利亚车站》、《一种阿拉斯加》、《家的声音》——仿佛为它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个三部曲从不同的方面抒写了品特在一个人生转折点的复杂情感。如果说《维多利亚车站》表现出的是人生的错位感,那么,《一种阿拉斯加》似乎预示着剧作家压抑了20年的政治激情在不久的未来将再次迸发,而《家的声音》则体现了他在10年的离婚旅程即将结束、新生活的曙光隐约可现时,对未来生活的渴望和对身后“旧家”的愧疚。
“政治剧”时期
1984年《送行酒》的上演宣告了品特思想和创作中的坚冰终于破除。在接下来的《山地语言》和1991年的《聚会时刻》中,他不再用模棱两可的语言来描写不可名状的威胁和恐惧,也不再留恋20世纪70年代的“记忆”世界,而是打起自己鲜明的道德旗帜,着重抒写人世间的“权力关系”和不平之事。西方的评论家只是指出这些戏剧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然后将它们一笔带过,不作深人探讨,导演们也不愿将它们搬上舞台。但品特本人对这些作品却偏爱有加。他在《送行酒》中亲自扮演了警察头子尼古拉。
这批作品在写作动机上已完全不同于早期的威胁喜剧。1989年,品特对格索说,他已受够了“房间剧”,受够了与他性情相背离的政治立场上的暖昧。所以,他说所有的游戏到此结束,一切用玩笑编成的烟幕也到此结束。从此,他要写“短而又短的作品,要更加赤裸裸地反映越来越野蛮的现实。”他相信这些戏剧的简短并不影响它们的丰富内涵,因为“如果你写一首诗,真正要紧的并不是它有20页长还是只有4行。”
品特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他的政治激情的发泄,而且,他攻击的往往是自以为民主的西方国家。当谈到《送行酒》的写作时,品特说:“这个来自我本人的生活和我对生活的领悟。在西方,我们总被误导,相信比其他人在道德上高一等,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优越的社会里。”他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在品特眼里,这些故事不只发生在那些“非民主”里,也发生在他们“可爱的英国”。
这批作品中最为著名的是《山地语言》。此剧于1988年10月20日由剧作家亲自执导在国家剧院首演。品特承认该剧的写作原因是由于一次旅行。1985年,他与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到了土耳其,发现土耳其当局禁止库尔德人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品特对此十分愤慨。但他也明确表示:“我之所以写这部戏剧,并不是因为土耳其;事实上,它讲的根本不是土耳其……它里面的故事离我们很近,我相信,很大程度上,它反映了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事…… ”他又说道:“大多数人似乎没有意识到,在这个国家里,另类和少数派的声音处于何等危险的处境。”
《山地语言》是对压制异己声音的最佳描写,剧中所有的山里人都被剥夺了用当地方言进行交流的自由。上演后,有评论家敏锐地指出该剧的主题是“肉体摧残与语言压制的联合运用”。《山地语言》正是品特所说的那种短而又短但却具有很强爆破力的作品。 在创作中,品特没有指明《山地语言》的背景是哪个国家,从而赋予了该剧普遍的指示意义,它可以指发生在任何国家的事情。
1996年6月19日傍晚,伦敦警察局逮捕了正在伦敦北区排演《山地语言》的11名库尔德难民,因为有公民报告说,看到其中有人拿着武器对着他人。在被拘留的5小时内,演员们“被禁止使用自己的语言—其情形与他们正在排演的剧目非常相似。”这个偶然的事件充分展现了该剧与当代生活的紧密联系。
政治生活与晚年
如果说品特的前半生属于戏剧,那后半生无疑属于政治。从上世纪70年代起,品特的戏剧发生了变化,他早年作品中耐人寻味的荒诞感不见了,它们的篇幅变得越来越短,政治化色彩却愈加浓郁。
品特经历过战争,幼年时与家人在炮火隆隆的逃亡路途上,亲眼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景象,与死神一次次擦肩而过。因此,他认为自己最有资格对战争说“不”。品特反对北约轰炸南联盟。2003年英美攻打伊拉克的战争打响后,他又花了大量精力投身于反战活动。他热心参与了左翼名人弹劾英国首相布莱尔的运动,他还给布什写信说,“亲爱的布什总统,我确信您和您的战争同伙托尼·布莱尔饮茶正欢。请就着一杯血咽下黄瓜三明治吧,不成敬意。哈罗德·品特,剧作家。
然而,英国主流社会对英国政府参与对伊战争是支持的,相比较而言,品特是孤独的。2003年初,他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时,多次遭到右翼人士的攻击,抛掷的鸡蛋、怪异的口哨,在他的身前身后时常出现。但这一切没有动摇品特参与政治活动的决心与信心。他写文章,与政敌辩论,定期组织集会,坚持到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请愿示威,要求英国政府早日从伊拉克撤军。唐宁街10号开始注意这个叫品特的老头子,一个权威人士说,一个犹太裔作家成了编制外的反对党。品特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永不妥协的立场,不仅在英国,即使在欧洲大陆,也是人尽皆知的。为了扼制英国政府的对伊军事政策,安抚在伊拉克战死的英国士兵家属,品特一面在公共场所阐明事理,一面募集资金,去赈济阵亡士兵的家属。他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批评布莱尔和布什,一再强调他们在说谎,在欺骗世界。
2005年,品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把获奖演讲词也当作了一篇讨伐伊拉克战争的檄文。他说:“……伊拉克战争,开战的理由是说萨达姆·侯赛因有非常危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些可以在45分钟内发射,给我们带来灾难。开战者对我们保证这是真实的,但这不是真实的;我们也被告知,伊拉克和恐怖分子‘基地有关系,和2001年纽约的‘9·11事件有关。开战者对我们保证这是真实的,但这不是真实的;我们被告知,伊拉克威胁世界和平。开战者对我们保证这是真实的,但这不是真实的……”
品特如是做,才如是说的。1998年品特出版了政论集《不同的声音》,1999年出版了《退化的能力:媒体与科索沃危机》,2000年出版了《宇宙的主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巴尔干圣战》,2003年出版了诗集《战争》。《战争》是对伊拉克战争的异议与抗议,出版不久,便获得下年度的威尔弗雷得·欧文奖。
2006年,品特在75岁生日那一天最后一次登上舞台,演出了贝克特的独角戏《克拉普最后的录音带》,之后宣布停止戏剧创作,把更多精力放在政治事务上。“我已经创作了29部剧作,已经够多了。现在我已经找到了新的方式来释放能量。”对于品特的政治热情,评论界有不少惋惜的声音。对此品特不以为然。他对《卫报》说过,“我怀疑他们一定也考虑了我的政治活动(才授予我诺贝尔奖),因为我的政治活动是我作品的重要部分。”
品特与中国
对于中国戏剧界而言,哈罗德·品特既熟悉又陌生。早在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荒诞派戏剧选》就收入品特的《送菜升降机》。次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又收录了《看房人》。此外,曾经写过若干电影剧本的品特,也因《法国中尉的女人》一片而被国人熟知。
80年代末开始,品特的剧目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实验剧场演出。1990年,还是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的孟京辉,导演了《送菜升降机》。1991年,林荫宇在中央戏剧学院排演了《情人》。同年稍后,李容制作、赵屹鸥导演的上海青年话剧团的版本则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曾创造了连演45场的票房纪录。到了1993年,竟然出现了全国多家剧院争相排演《情人》的现象,成为了中国第一波“品特热”。
然而,因文化背景和社会状况所限,很难说当时的中国戏剧工作者和观众真正了解品特。《情人》讲述的是一个拯救婚姻危机的故事:一个表面看来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的“幸福家庭”,一套远离城区的高级住宅,一对夫妻看起来生活得安逸而舒适。但每天丈夫与妻子彬彬有礼的吻别后,两人又假扮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以各种假设的身份谈起了恋爱。在话剧的最后,丈夫厌倦了游戏,品特最终还是让两人复归于好,显示了作者仁慈的希望。品特试图通过此剧体现三个意图:一是人自身的双重性格,二是环境本身的双重叠现,三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疏离。然而,国内媒体宣传此剧的噱头却是中国第一部“未成年人禁止观看”的X级戏剧,在社会引起争议的并不是品特戏剧的主题思想,而是能否将性爱内容半隐半显地呈现在舞台上。
90年代第一波“品特热”过去之后,品特作品在中国戏剧界销声匿迹了将近10年,成为了只被少数戏剧圈内人知道名字的作家。直到2004年,品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日益高涨之时,中国戏剧界和媒体才再次将目光聚焦于这位英国剧作家。2004年4月至7月,北京人艺小剧场再次排演《情人》,导演徐昂。2004年,谷亦安重排该剧,在上海艺术剧院演出10场。令人遗憾的是,品特的作品虽然被搬上中国舞台不少,但很多都是在小剧场演的,看的人并不是很多,影响依旧不大。更令人遗憾的是,时间又过去了10年,国人对品特的兴趣仍在《情人》,对品特“记忆剧”时期之后的作品似乎茫然无知。
无论如何,品特对于世界和中国的价值决不仅仅限于对性爱和家庭关系的反思,他敢于独立思考,具有平民意识,不顾及个人得失,保持了人类的一种难得的清醒。中国戏剧界想要进一步接近和了解品特,译介和排演更多他“政治剧”时期的作品则是必由之路。
品特,一个深陷于艺术和政治的人,一个为了正义敢于挑战强权政治的人,凭着信仰,即使到了天堂他也不会偃旗息鼓的。
许健:中央戏剧学院
责任编辑:傅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