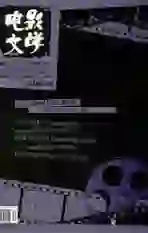《生死朗读》与西方“纳粹浩劫”题材电影的嬗变
2009-04-15李颖
李 颖
一、“纳粹浩劫”的历史在西方文学
和电影艺术中的表现
德意志第三帝国制造的大屠杀将人类的残忍性发挥到极致,被看做是20世纪最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之一,成为西方文学艺术作品表现的重要题材。这次对人类基本价值观念带来冲击的大浩劫为后世文学和艺术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二战后西方文学中,出现了大量以纳粹大屠杀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活跃的作家多为大屠杀的受害者、幸存者。
纳粹“大屠杀…浩劫”指二战时期,在希特勒的指挥下,纳粹德国系统地对欧洲的大约600万犹太人和其他民族进行的种族灭绝性杀戮行动。受害者不仅有犹太人,还有许多欧洲其他民族和社会群体,如:吉普赛人、波兰人、俄国人、苏联战俘、残疾人、同性恋者、持不同政见者和宗教反对派等。
“大屠杀”的历史随着纳粹德国的垮台而为世人所知,造成前所未有的震撼,这无疑对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形成了巨大冲击。战后,大屠杀的亲历者、幸存者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记载这段悲惨的历史。到20世纪60年代,“大屠杀”这个词汇开始为文学界所接受,特指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性大屠杀。70年代,美国经常出现带有“大屠杀”字样的电视连续剧,使之渐为大众所接受。
随着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逐渐老龄化,用何种方式保留劫难的记忆成为文艺界关注的问题,因此出现了以大屠杀为题材的纪录片。它们强调真实感、历史感,尽可能少进行加工,代表作如:法国导演阿仑·雷乃(AlainRenais,1922-)的《夜与雾》(1955)采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方式进行拍摄,它用黑白片与彩色片将过去和现在完全分开,黑白片表现了纳粹令人惊悚的大屠杀和集中营的残酷,如对使用犹太人尸体脂肪来制造肥皂的描写。它的真实性受到评论界的赞扬。它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小人物的历史责任问题,被看做是经典之作。再如法国导演克罗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1925一)的纪录片《浩劫》(1985)是这种文献纪录片的代表作。它的拍摄历时13年。片长达9个小时。与传统的纪录片不同,它没有按照某种意识体系进行整理,没有制造流畅的历史感,而是采访大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亲历者,如看守、纳粹分子、幸存者、附近居民等,一一作证,通过这些人的亲身经历,每个人的证词,以丑陋的真实表现出这段悸动的历史。
与早期描绘集中营中的肉体磨难相比,20世纪60年代的纳粹浩劫题材电影关注的焦点在于表现浩劫中亲历者在道德上的两难处境,普通人陷入其中而无法脱身,在群体上人性的泯灭。许多电影关注于那些纳粹的帮凶,他们或直接参与,或被动地支持了纳粹的行动。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新的方向,突破了五六十年代的定式,以更加主观化的态度处理素材,开拓出新的思想深度。
二、“纳粹浩劫文学”的题材特色
以“纳粹浩劫”为主题的文学、艺术、影视作品在题材上围绕着种族屠杀的特征进行表现。第一,广泛地参与到大屠杀当中的纳粹国家官僚机构在“纳粹浩劫”题材文学中有大量表现,如:教堂和内务部提供出生证明,确定犹太人的身份;邮局邮寄驱逐出境和取消国籍的通知;财政部将犹太人的财产没收;德国企业开除犹太裔工人,剥夺犹太裔股东的公民权;大学拒绝招收犹太人,拒绝授予在读犹太人学位,解雇犹太裔学者;政府运输部门把被驱逐的犹太人送到集中营;德国制药厂在集中营关押者身上试验药品;企业家们为争夺火化场建筑招标合同而讨价还价;官方列出受害者的详细情况,制作精细的屠杀记录。关押者进入集中营时,所有个人财产被德国政府没收,详细记录在案,然后送回德国重新利用或者循环使用。
第二,意识形态成为大屠杀行动的导向,其规模前所未有。历史上发生的大屠杀的目的都是出于对领土、资源的占有,可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不同于以往,它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完全以纳粹主义者的幻想为基准。他们认为国际犹太人有排斥雅利安人、统治世界的阴谋。这种完全基于传说和幻想,抽象不实际的、意识形态式的大屠杀前所未有,没有任何国家曾经从政府的主导意识角度上宣布某一特定人群,从老人、妇女到儿童都应该被迅速彻底地消灭干净,并由政权提供全方位的支持。纳粹德国却在其广大占领区内,极有效率地从事这种屠杀行动。1939年东欧有700多万犹太人,其中500万人被杀,包括波兰300多万,苏联100多万。纳粹还宣传把这项计划推向整个欧洲。只要祖父母辈分中有三四个犹太人的就是纳粹消灭的对象。在人类历史上的其他大屠杀中,人们只要改宗就可以得到保护;而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都在被消灭之列。
第三,使用活人作为医学实验品。大屠杀文学的另一个重要题材是在医学实验中大量使用活人。这种屠杀的手段非常理性、实际。德国医生在奥斯维辛、达蒙、布痕瓦尔德等多个集中营进行这种活体实验,集中体现了大屠杀的残忍性。
三、《生死朗读》中体现的“纳粹浩劫文学”新动向
由本哈德·施林克原创,史蒂芬·戴德利导演的电影《生死朗读》与传统大屠杀题材电影的不同,它开拓了新的思维方向,由外部世界的描写转向内心世界的描写;关注的焦点由战争、屠杀、虐待、流血等外在冲突转为亲历者的内心冲突。在这个新领域的开掘中,对德国民族表现出的对人性的冷漠进行了批判。男女主角麦克和汉娜清晰展现了战后德国社会中生活在大屠杀阴影下两代人的困惑,这种困惑如何通过书面和口头媒介顺利表达出来,在20世纪晚期至2l世纪早期的描写大屠杀的文学中处于中心位置,因为随着大屠杀的受害者与幸存者的去世。这段记忆越来越淡化。“当我们还能够真实地写作它时,不应该让伟大的题材消逝。”
小说的叙述与战争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距离,与以往的大屠杀文学产生了距离感。而且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也由受害者转向了作恶者。纳粹经历的后一代人的负罪感和德国两代人之间的“代沟”问题构成了本剧的主题。纳粹罪恶之后的一代人是如何在其阴影下生存的?历史和过去限制着他们,但是他们却只能生存在其中。这一代人考虑父辈僵硬的责任感所造成的悲剧,但是他们却很难在这个意义上对父辈进行指责。在麦克和汉娜之间也交织着这样的问题:麦克觉得很难对汉娜的历史谴责,也难以理解其中的思路,只能在两者的矛盾中徘徊,形成了复杂的道德意义。麦克和汉娜之间的不对称、不合法、不均等的关系表现了二战后德国两代人的尴尬关系,正如麦克所说:“由于我对汉娜的爱使我经历的痛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这是德国民族的命运。”
作品从小人物的角度对德国那段老而又老的纳粹大屠杀主题进行了充满新意的阐释。小人物的内心冲突取代了战争和屠杀中的外在暴力冲突成为作品的主题。这一转向表现出战后德国人对纳粹历史反思的深入和在新领域的拓展。在荒诞面前,艺术化地处理了作为个体的人与公众之间的矛盾斗争。它不再关注那些惨无人道的罪行,也没有
惨烈的画面作为刺激,而是把焦点放到了一个普通女性小人物身上,通过她的生活转变来折射出那段罪恶的往事。“并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是刽子手,更多的人都是不知不觉就参与到了罪恶之中,像汉娜一样……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只是没人关注过他们而已。而实际上他们往往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正是从这个独特的视角出发,作者对“纳粹浩劫”题材进行了新的导向,获得了奥斯卡评委的认可。正如斯蒂芬·戴德利的评论:“我很惊叹作者本哈德·施林克的独特视角,过去很多人提及二战中纳粹灭绝人性的历史事实,关注的都是一些惨绝人寰的罪行,但他的小说用了另一种视角,关注在战争中普通人的所作所为,和对这个战争所带来的影响。也许并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注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更多的人会像汉娜这样,不自觉地参与到罪恶当中,自己也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受害者,只是从来没有人关注过他们。这部小说提供了这样的思路,我们终于可以明白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中更多的事实真相。”0施林克的小说和同名电影在德国和美国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国批评界也关注了其提出的“文盲”的象征意义。
四、评论界的批评
评论界对其看待纳粹历史的方式提出了批评。作品故事情节与早年流行于以色列和美国的描写纳粹女看守的色情文学相似,这部作品也被看做是“文雅化的色情文学”,因此有人认为它在篡改伪造历史。电影的倒叙结构也使得结尾过于突然。
电影艺术化处理纳粹种族灭绝政策制造的恐怖,也引起了评论界的批评。“这部电影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没有抓住素材中令人恐怖的实质。”它简化了历史,强迫读者予作恶者以认同。“这是一部试图转变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对臭名昭著的纳粹军国主义认识的小说。”批评者们从历史主义、写实主义的角度指出,德国民族应该深刻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罪恶目的。
施林克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说:在以色列和纽约,老一代人喜欢本书,而他的同代人更倾向于批评麦克没有能够完全对汉娜进行谴责。他说:“我听到很多这样的批评,但都不是源于老一代经历过这个历史的人。”0可见有过这段历史经历的人的思考不同于后一代没有经历的年轻人,他们更多地从自身的经历出发,理性地审视这个难以化解的矛盾,而不似后一代的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