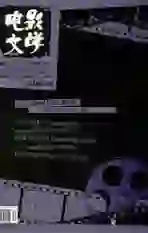《奥罗拉.李》的性别解读
2009-04-15范翠华
范翠华
[摘要]本文从性别研究角度,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诠释了勃朗宁夫人的长诗《奥罗拉·李》中的女主人公形象。探讨了勃朗宁夫人笔下的女性形象是典型的被男权社会内化而自我奴化的一个卑微对象。勃朗宁夫人在作品中试图论证女性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取得社会的认同。但结果却昭示了女性自身被男性同化而使自己依附于男性的观点。
[关键词]内化;性别研究;《奥罗拉·李》;勃朗宁夫人
如同许多其他英国19世纪的女性作家一样,勃朗宁夫人的文学创作始终关注着那个时候的主流意识形态——女性的地位与解放。她的大多数作品表面上充分揭示了女性所受的性别歧视,想摆脱附加于女性身上的传统规范。而本质上却表达了她也如同当时的大多数家庭主妇一样的愿望——成为“家庭中的天使”。对勃朗宁夫人的解读在国内最早为人们所知的是她与勃朗宁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以及她为之创作的《葡萄牙十四行诗》的译介与评论上;而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国外学者对她的文本的解读纷至沓来,即便是这样,国内对此的研究却鲜有涉及。这也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1949年,随着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出版,深化了20世纪的女权运动。在这本书中,渡伏娃以她那句精辟的话语“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指出了女性是如何成为“女人”的辛酸历程。20世纪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提出“性别”这个概念,她们将性别分为“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两部分。她们指出,社会性别是后天的和社会的文化设定,它区别于父权制文化仅以生物学的性定义女人。社会性别理论尽管以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却关联着互为主客体的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两性关系。纵观女权主义的发展史,尽管女权主义理论千差万别,但几乎所有的女性批评家都在下列这点取得一致:父权制不是自然地形成的,而是人类重构的一个要素;既然社会性别是后天的社会文化设定,便是有可能改变的。女性作家通过自身的社会性别意识或无意识,潜在地或曲折地折射到文本中,影响了文学文本的人物塑造和话语方式。这无疑为我们解读勃朗宁夫人的《奥罗拉·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一、女人需要什么
1857年,勃朗宁夫人出版了她的自传诗体小说《奥罗拉·李》。小说一出版即受到当时文学界、评论界的关注,是英国第一部“由一位女性作家创作的,其主角也是一位女性作家”的作品。这部长篇诗体小说共写了9部,比弥尔顿的《失乐园》还长,故事情节则相对简单。诗中女主人公奥罗拉·李出身在佛罗伦萨,其父是英国人,而母亲则是意大利人。幼时便失去了双亲。随后她被送往她英国的老处女姑姑家;在那里,她阅读了其父亲藏在阁楼上的书籍,成为一个“有知识”的女孩;在她20岁生日之际,也是她正当自己认为摘取了诗歌桂冠的时候,其远房表兄罗姆尼向她求婚并要求她放弃诗歌写作,她拒绝了;之后,她只身远赴伦敦等地,专心从事创作,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在诗歌的最后,罗姆尼因为与他的社会人文主义的追求者们产生了矛盾。在一场火灾中失去双眼。奥罗拉与他最后幸福地结合在一起。
这个故事情节和《简·爱》十分地雷同。初读文本,我们把这首长诗解读为女性对父权制社会的揭露是不足为怪的。然而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这首长诗实际上是女性对男权制的妥协,是被男性同化的过程。在诗歌的一开始,奥罗拉·李被作者塑造为一个柔弱无助的女孩形象,“可是,/我成了没有母亲的孩子四处流浪,/直到现在还在到处寻找,/却不清楚究竟失去了什么?……”“没有母亲…‘四处流浪…‘哀哀哭诉的小羊”等给奥罗拉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果说母爱的缺失给奥罗拉带来了恐怖,但那却不是致命的,因为,“但母亲的微笑会照亮整个脸庞,使它变得比自己更美丽生动。”而随之而来的拳拳的父爱却给幼小的奥罗拉一种慰藉。父亲把“他人生所悟的精华传授给我……他让我了解人们的种种无知……”“爱吧,我的孩子,爱,爱!”。奥罗拉今后的人生目标便在父亲一遍又一遍的“爱”中确立了:要懂得爱——爱丈夫,爱孩子,爱家庭。要学会悲痛,即要充满柔情地对待周遭的一切,这就是女人的全部。
在她父亲死后,奥罗拉被送往英国她老处女的姑姑家中。因为姑妈喜欢“有指导的虔诚”,她要“我读数十本学习之道。以证明/如果女子根本没有思想,/这些会教会她们思考。”她们天使一般的美德……总之,她们对任何事情的才能都在于/放弃她们的权力。”奥罗拉意识到了作为女人的悲哀,于是试图对她姑妈的教导予以抗争,但是无济于事,只能以“在我的内心世界之外,世俗无法侵犯的地方/那里足以容纳我的意志与才智,容纳/我的五脏。”。她无法被传统的社会理解和接受,只有求助于常人触摸不到、看不见的精神层面。她尝试着写自己的诗歌。以此反抗这样的传统。她也认识到表兄“之所爱,/并非女子,罗姆尼,而是事业,/你之所需,并非主妇,先生,而是助手。/一位妻子以帮助实现你的目标——但对她却非结局!””于是她断言道“我热爱自己的艺术,决不希望贬低它/以适应我的水准。我热爱自己的艺术/你会承认即使是一位女子也可以热爱艺术,/因为将真正的爱情花在任何事情上/都太女人气。……”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奥罗拉渴望的独立是把自己变成男人似的女人;如果她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得舍弃爱情。在这里,勃朗宁夫人刻画的女主人公的女性身份的确立乃是以男人为标准。无论奥罗拉今后的发展如何,其结果都会是使自己迎合当时的性别传统,从而使自己贬低自己。因此,奥罗拉全盘接受了男权社会的标准尺度,无论于她合适与否,只要像男人那样思考。那样行动,就会取得成功。于是,她只身来到男性的世界里,希望得到男性社会的认同。“我不停地写作,/穿越黑夜与白昼的围栏,/……我不停地奋斗……”她成功了。却感觉到了“我在游戏艺术”。奥罗拉原打算借助写作反抗男权社会赋予女人的卑贱地位,最后却变成了不得不“严肃地游戏下去”的工作。而且,以写爱情诗闻名的奥罗拉,面对自己空白的爱情生活只能唉声叹气,“又有谁来爱我?我最亲爱的父亲,美丽的母亲……”她懊悔她曾作的选择,表兄罗姆尼的话使奥罗拉琢磨不透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奥罗拉犹豫了,厌倦了她所选择的职业,因为,“男人对女人的需要/总胜过女人对男人的追求。而且更容易满足。男人要得到的/是女人,/而我们寻找的却只是一个人,理想化的,/也是实际的。我们渴望失去自己,像白珍珠一样溶化在他人的酒杯里,……”至此,奥罗拉在罗姆尼反对她从事写作时所做的辩解全被“男人要得到的/是女人”这句话消解了,她最后不得不承认“我是这样失误,这样高傲,这样软弱,这样无助,/仅仅是个女子!”。直至最后,当她得知罗姆尼因为自己所追求的事业遇挫,爱情又极不顺利时,奥罗拉深深地责备自己:“如果我曾经是个女人,/像上帝造就的那种女人,用爱去拯救男人,/用我的爱本可以拯救这个
人,/给世人留下一首更高尚的诗篇/胜似我所有失败之作。可我在这一点/也失败了。现在他迷失了自己!只因为我一人的缘故。”她的自责,无疑是把自己视作男人的守护“天使”。为了爱情,宁愿抛弃一切,“艺术象征着天,但爱情是上帝。”这就是奥罗拉所追求的,也是她父亲曾教导她的那样。
二、“集市货架上的布娃娃”
众所周知,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即男主外,女主内;而女子的一切财产都是丈夫的。对于19世纪的女性作家,她们意识到了父权社会强加于女性的从属地位,也曾试图消除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可是,对“大多数女性作家来说,她们首先是女人,然后才是作家”。因此,女性作家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掩盖自己是女性这一事实。诸如,玛丽·安·伊万丝以笔名乔治·艾略特发表文章;艾米莉·勃朗特甚至没告诉出版商自己的性别。在勃朗宁夫人时代,女人要么变成像“男人式”的人(其结局只能独身);要么回归自己原来的位置“家庭”中去。虽然奥罗拉在诗歌中大声斥责“因为将真正的爱情花在任何事情上/都太女人气”。可是最后连她自己也讨厌自己,“我头脑中有个男子,让他行动,/不去理睬可怜意识中的忧虑/那是被称做女人气的东西。”然而,“当女子最强有力时,她们也有和男人一样软弱的肉体/在她们最软弱时,又有最邪恶的灵魂,/所以女子如何能与男子并驾齐驱!”这就是典型的“厌女症”。之所以如此,并非她真正地讨厌自己的生理性别,而是因为她意识到“我们只是一堆布片拼凑而成,与那些把漂亮脸蛋/倚在集市货架上的布娃娃没有什么不同”。社会性别规定了女性是男性的助手兼精神引导者,又当牺牲品,女性能够放弃的只是她的自我、她的女性主体意识乃至于女性的肉体存在了。奥罗拉在最后对罗姆尼爱的表白暗示了,一个健康而富有的女人等于一个“精神高尚”的眼盲的男人。通过这一“幸福”的结合,勃朗宁夫人在诗歌中表达了她理想中的伟大女性作家的形象——位高尚而又贞洁的“天使”形象。因为她生为女人,她就应该像女人那样生活:结婚生子,相夫教子,个性顺从,思想独立又要贞洁迷人。在诗歌中,奥罗拉的爱情就这样在牺牲自我、放弃自我中完成了。至此,男女双方洞察力的互换,男女性别中女性的身份地位就这样被边缘化了。女性就是一个“倚在集市货架上的布娃娃”,是一件任人挑选的商品。
三、结语
通过对《奥罗拉·李》的文本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勃朗宁夫人的自由的女权主义思想由于奥罗拉·李最终献身于男性指引的生活而与现实社会达成了妥协。这就陷入了男权社会赋予女人的传统定位。在诗歌的第一、二卷中,奥罗拉·李被塑造为一个激进的女人形象,她想挣脱社会的传统;渐渐地她认识到,如果她一味地追求自己的东西,她势必处于孤独的境地,这是她不希望得到的结局。诗的最后,她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试图证明女性经历的千辛万苦只是为了得到男性的“嫣然一笑”。最终也只能被男性内化成自己的“产物”,因而贬低女性自身。正如奥罗拉所说:“如果我,在那一天,作为我那样的女孩子/曾多一分温柔,少一分傲慢,/并不会使我受到伤害。”奥罗拉心甘情愿地为爱泯灭自我,最终也就在男子的视阈下把自己给空洞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