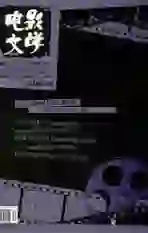论余华小说叙述方式的转变
2009-04-15陈昭明
陈昭明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余华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叙述方式上,他抛弃了先锋小说的叙述方式,完成了向传统艺术的回归,主要表现在故事讲述、人物塑造、语言风格三个方面。
[关键词]余华;叙述方式;转型
反叛传统,偏爱语言的游戏形式,打破时空顺序,消解故事情节的完整性,故事被漫不经心地展开,事件没有开头,没有高潮,没有结局,人物符号化等是余华早期作品推崇的叙事艺术。而到了后期即20世纪90年代,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小说中的叙述方式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故事讲述由叙述人主体性向人物主体性转变
余华早期作品中人物符号化、抽象化,所有人物只是共同地发出叙述者单一的声音。余华多采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叙述者如同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幽灵,无所不在,全知全觉,告诉读者一切场合发生的各类事件,他试图通过第三人称客观地叙述这个黑暗的世界。而少量的第一人称,也只是单纯地充当故事叙述或抒情的主人公,没有更多叙事结构上的意义。在《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三部长篇小说中,余华选用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或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作者与叙述者分离,放弃了叙述的权利,退隐到“聆听者”的位置,孙光林、福贵、许三观们是小说真正的主人,他们按自己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生活,用自己的话语述说经历,表达感情,不再充当图解作者意志的工具。
如《在细雨中呼喊》以“记忆的逻辑”组织结构,时间是双重的——过去和现在,与此对应,作者选择了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为主的叙述方式,回顾性视角赋予“我”双重色彩——“我”既是一个受冷落、受歧视的孩子,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于是便存在两种眼光:一种为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种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经历事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以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余华选择非成人的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视角,进入回忆之门,讲述主人公童年时代的心理感受。无论是孤独、寂寞、痛苦、绝望,还是对世界温情和幸福的期盼,都深深地烙上“我”的个性生命体验和感悟。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联系为一体,随着叙述的深入,我的生命体验和感悟也不断深化,生命的意义也不断升华。不仅叙述者,甚至叙述行为本身也参与了作品意义的创作。
与《在细雨中呼喊》相比,《活着》中的主人公形象(福贵)更为清晰。文本采用双层叙述模式:第一层次是听故事的“我”,即表层叙述者采集民谣的“我”;第二层次是讲述故事的“我”。即采集民谣的“我”在乡里碰上的那位老人——福贵,他以主人公和自己叙述者的双重身份,采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经历。故事第一层次“我”——倾听者的设置。一方面展示余华对生存境遇的正面关注,出示他的情感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也使阅读者参与倾听人类在遭遇生存苦难的重压时,应如何承受生存苦难的压迫。故事第二层次的“我”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特有的双重聚焦,即叙述者与主人公为同一人,既直接体验死亡对人类生存地盘的侵犯,又使文本真正回到小说,还给小说以真实的形象。在这里,余华充分肯定了福贵的生存,他活着就是为了更好更平静地生活。他们以生命的价值征服了诸多的苦难之后,虽然死亡是必然的,但作为个体的意义已经显现。
二、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塑造
余华自己经历了一个对小说人物的不断理解的过程。以《在细雨中呼喊》为界,之前的作品中的人物,不过是他叙述中的符号,人物脱离了生活的土壤,仅仅只是演绎作家自身主观世界的道具。他们缺乏个性而面目模糊不清,甚至以阿拉伯数字为代号没有自己的名字。对此,余华曾经说过:“事实上我不仅对职业缺乏兴趣,就是对那种竭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也感到不可思议而难以理解。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艺术价值。”在余华的创作视野中,人物仅仅等同于河流、山川、树木之类的自然物象而已。但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作家开始意识到人物在长篇小说中应有的地位!虽然此时的余华并没有像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将人物形象的塑造置于小说创作中的核心地位,但已经开始尊重其小说中的人物并努力倾听他们的声音。曾经将笔下人物等同于山川、树木的余华这样谈到:“小说中人物每一次的言行举止,都会让作家反复询问自己:是这样吗?是他的语气吗?是他的行为吗?或者在这样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和这样说?”从余华前后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前后期的余华在创作中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看法已经大相径庭了。如果说余华早期小说中的人物只是被叙述者所主宰的话,那么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人物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鲜活的人物形象也随之出现。到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更是开始出现了富贵、许三观这类具有典型化倾向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在《活着》的整个写作过程中,富贵这个主人公自始至终牵引着作家的主要注意力,而《活着》的完成及其成功也正是余华“贴”着富贵这个主人公写的结果。在这两部小说中,余华并没有赋予富贵和许三观激烈的外部性格冲突,也没有对他们的生存心理进行直接剖析,而是让二者平凡的人生、朴实的话语“自动”地在小说的时空中呈现,在这种呈现中,二者的丰富、复杂、厚重被无限地放大了。
作为一个典型必须具备两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是概括性、普遍性,即应当能使人由一个人物而联想到一大群人,甚至能联想到千千万万个和他同属一类的人。二是独特性,即他必须是一个不与别人雷同、重复的,自身有着丰满血肉的人物形象。当然,概括性越广泛,独特性越鲜明,典型人物自然就具有更高的意义了。就富贵和许三观身上的概括性而言,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过去几十年无数天灾人祸中苦苦挣扎的中国底层普通民众的身影。战争、文革、三年自然灾害……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经历正是我们的父辈的亲身经历,这些发生在富贵、许三观身上的人生经历复活了我们对于那段岁月的历史记忆,而记忆的复活更加深了我们对于富贵们的认知。毕竟,那是我们的父辈,是千千万万中国的普通百姓所走过的道路。在那些数不清的苦难日子里,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别的庇护和依靠,他们能依靠的只有家人之间的互相关爱和邻里的相互救助以及自身的乐观顽强的精神气质才得以熬过来。余华曾经讲过,《活着》讲述的就是“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典型人物还必须具备鲜明的独特性,必须有着不与别人雷同的艺术生命,即成为不可替代的“这一个”。在富贵和许三观身上,两个人显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命运的发展轨迹。富贵出身地主家庭,少年浪荡,好赌成性的他赌光了家中的所有家产,而后,他洗心革面,浪子回头,担负起养活一家人的责任。在经过了被抓壮丁的九死一生的经
历之后的他,开始了相对平稳的家庭生活。也就是从此开始,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又一个个相继死去,老来的富贵只落得和一头老牛一起过着形影相吊的孤单生活。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中国人常说的人生三大不幸几乎无一幸免地落在富贵的身上,富贵的一生几乎是尝尽了人生的不幸与苦难。不同于富贵。许三观的独特人生经历体现在卖血上,体血发肤受之父母,去之不孝,而许三观这个身无所长的小人物只能用自己的鲜血去换取困境的渡过和一家人的继续生存。
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二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独特性对于典型化中的独特性而言还只是外在的,浅层次的,此二人典型化中的独特个性更集中地表现在二者的精神内核上。也正是这种在精神层面上所表现的独特才最终提升了人物的典型化深度。在艰苦贫困的生活面前,富贵咬咬牙挺住了,在无力地面对亲人相继地离去这些灭顶之灾面前,富贵顽强地活了下来。许三观在每次家庭遭遇不幸变故时,一次次地卖血以使家庭渡过难关,虽然一次比一次不易,一次比一次艰难,他还是挺了下来。在多灾多难的宿命面前,在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像富贵和许三观这样的草根阶层能做的就是无言地承受,顽强地挣扎,并乐观地活下去。顽强、乐观、甚至还有那种穷人所特有的苦中作乐的幽默感构成了富贵、许三观们的主导性格,也正是这种主导性格成就了他们作为典型人物的独特个性。
三、叙事语言从冷漠走向温情
早期作品中余华采用那种保持距离的冷漠的叙述风格,在不动声色、冷漠而细致的叙述里大肆涂抹人类的各种苦难意识,又极力回避应有的价值判断和理性审判。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早期超然物外,纯客观地冷漠叙述里,多了充满温情的人性发现与揭示。在《在细雨中呼喊》回顾性的叙述中,叙述话语的基本格式是“至今还记得”,“现在回想起来”等,引出的小说内容或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分析往事的因果,或抒发叙述者由某事件引发的感慨,或对童年阴影与自我性格成长的反思。如《友情》一节中写“我”与苏宇的交往,由于缺乏家庭的温暖,“我”对苏宇一向很羡慕。因为从表面看,他们的父母知书达理,和蔼可亲,后来苏宇对“我”说他有一次深夜做噩梦,哭醒后却招来母亲的训斥。小说写道:“独自回想这些时,我才逐渐看到敏感的苏宇,从童年起就被幸福和绝望这两个事实纠缠不清了。”在现在时态的“独自回想”中,作者感叹的是人间温情的难得。余华开始正面构筑起某种意义,肯定一些情絮,温暖自己的同时也温暖别人。如我与国庆等人友谊的描绘,鲁鲁对其母的真情渲染。一贯冷静的余华在描写他们时表现出对他们不幸命运的同情。对他们执著韧性的肯定,对他们智慧、从容、懂事的性格的赞赏,给人以温暖与鼓动。
余华在《活着》自序中表露对“活着”的同情与理解:“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生命赋予我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叙事感情由冷酷漠然到平和自然,亲切幽默而不伤情,叙述者已不再是冷冰冰的物,而是温热热的人。面对亲人的相继死亡,作者不再像早期作品那样残酷地展现死亡的恐惧过程,而以温情悲凄的语调重复亲人的离去:“家珍像睡着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如此安详与平静,余华对死亡的表现就是生命的消失,抽取了传统意义上政治和情感的内涵,生命本体的意义便突现出来。
以温情冲淡冷酷,使作品呈现暖色,《许三观卖血记》中处处可见。许玉兰坐在门槛上哭诉,街坊邻居七嘴八舌地关心询问;许三观看在一乐叫他9年爹的情分上,决定继续收养一乐;许三观反复用“做人要有良心”的朴索道理,劝说一乐去为何小勇喊魂,“怎么说何小勇也是个人,只要是人的命都要去救”;在一路卖血去上海的途中。河岸人家给他送来盐与热茶;远方来的老头主动借猪给许三观取暖,这些温情的话语和场景多次出现,说明余华原来的冷酷的自我在不断退后,冷静的笔调中饱含激情,充满理想地表现了一个普通人内心深处关于生命的真实表达。也正是许三观所表现出的无私、仁义等高尚品质的持久驱策,人类才有望在生存之重的过度挤压下,活出人所应有的精神境界。
余华的小说创作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看都成功地实现了其转型。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人物的复活,清晰的故事及温情的语言都使余华在20世纪90年代的影响更大,不仅赢得了国内读者的喜爱,且被译成英、法、德、意、西、日、韩等多种文字。这两部小说不仅使余华获得了市场效益,同时也为他日后的创作起了一种激励作用。而余华的成功转型必然会给中国当代文坛带来繁荣,并因此而激励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