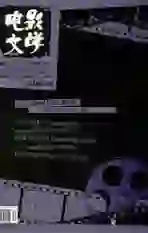再戳《英雄》的叙事软肋
2009-04-15庄君
庄 君
[摘要]张艺谋的《英雄》不仅带来了中国电影票房上的规模性成功,也引起了各类观众对于第五代导演叙事能力的质疑,《英雄》的成功与失败都必定也必须引起广泛而长久的关注和反思。本文借用结构主义语义学家格雷马斯的三组二项对立武六个动素的模型,尝试从所谓“结构主义理论实践的重要脉络”叙事学的角度对《英雄》的叙事进行分析,探讨其在故事和叙事上的缺陷和成因。
[关键词]叙事;叙事学;英雄(叙事学概念范畴)
对于“叙事”,电影理论家麦茨曾经这样精彩地论述它之于电影的作用:并非由于电影是一种语言,它才讲述了如此美妙的故事;而是因为它讲述了如此美妙的故事,它才成为一种电影语言。叙事缘起于语言的出现,也成就了语言的形成。因此,对于电影而言,叙事成就了它作为一种艺术的成立;对于一部影片而言,叙事也使得它的故事和内容成立,使得观众的接受成立。
“所谓‘叙事学所指并非关于叙事/虚构性文学作品的研究,而是特指结构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脉络。”…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通在对古希腊神话传说的研究过程中试图指出“古往今来不同时代的人类叙述行为共同的社会功能就是通过千差万别的故事,共同呈现某种潜在于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矛盾,并尝试予以平衡和提供想象性解决。”俄国学者弗拉基米尔·普罗普在研究了大量的俄罗斯民间故事而后发现了7种“行动范畴”(功能)、6个叙事单元和31个叙事功能的叙事元素。他所谓的行动范畴或者说角色并不等于故事中的人物,而是在故事中的不同段落、情节在发展的不同时刻所具有的叙事功能。这两位可以说是开启结构主义时代理论灵感的大师。在普罗普的7种“行动范畴”的基础上,结构主义语义学家格雷马斯经过进一步修正和深化,试图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叙事分析模式。因此概括了三组二项对立式6个动素的模型。
此外再加上茨维坦·托多罗夫、克罗德·布雷蒙等关于叙述性文本的叙述范式的论述,叙事学不断丰富发展成熟完善。本文主要使用格雷马斯三组二项对立式六个动素的模型对《英雄》的叙事进行分析。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以旗手的姿态再次引领了中国电影大制作的风潮,扛旗之作便是2002年出品的《英雄》。《英雄》出世,一时间纷争四起,票房的不断攀升和评论的一片骂声“相映成趣”,形成2002年末的一道娱乐奇观和文化风景,似乎批评越猛烈,票房将越火爆。各方评论、批评集中于电影的故事本身。几年过后,狂潮淡去,重新分析这部影片,试图从叙事的角度探讨究竟这个故事出现怎样的问题以及这样的问题是如何出现的。
相较于张艺谋以前的作品,《英雄》的转型性质明显。在李安《卧虎藏龙》的启发下——尽管导演本人多次重申《英雄》的创作初衷和《卧虎藏龙》的成功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英雄》的剧本筹备要远远早于《卧虎藏龙》的出现,但是,此后几年中国电影的制作状况呈现的事实是,自《卧虎藏龙》以来,没有成熟类型片观念的中国电影因袭了一个类型片的路线:武侠片的路线。同时,《英雄》作为张艺谋的转型作品,为了有所突破必然要有所“创新”。
影片在形式上的创新是一种自我风格的夸张展现:色彩原本就是张艺谋的长项,在这部作品中,更是极尽其所能——青黑的冷萧凝重,红与黄的绚丽缤纷,绿的苍翠饱满,蓝的冷静练达,白的浪漫飘逸。
影片的故事和剧本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作品,从《红高粱》开始,他的电影几乎无一例外地改编自成熟的文学作品,这里面融入了导演和编剧的极大创造,不得不承认。小说本身为影片提供了成熟而稳定的叙事架构。然而《英雄》不同,《英雄》虽然出自于“刺秦”这个人所共知的传说故事,但是恰恰在导演试图创新、转变的历程中肩负起在成规中有所突破的任务。因此,为了在题材的旧酒瓶中装上新酒,“新”从何而来?必须逆着走,旧故事为了具有原创性的途径之一就是逆原故事而行。因此,虽然“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已经妇孺皆知,但是导演仍然选择挑战人们的既定认识,张艺谋要创造一个新的“英雄”观念。这一切都无可厚非,但是影片出来之后。商业的成功并不能掩盖人们对影片所传达观念的反感。作为一个商业文本,票房是其成功的强有力证明,但是如果把影片和随后大面积的批评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文本进行研究时,不能不说《英雄》败了。
任何的创作者都应该知道这样一个常识:故事的接受者在讲述者讲述之前对故事已经有了自己的态度,这里并不是说读者或者观众有多么神奇的未卜先知的能力,而是因为社会人已有其先于故事的某些观念,比如秦始皇的出现,在观众头脑中唤起的是“暴君”的形象,唐太宗的出现唤起的就是一个“明君”的概念,尽管他也曾在玄武门杀死了他的亲兄弟。当然也不是说既然如此,传统故事再也没有新的创作空间了,在起点(刺秦的故事)和终点(不同以往的刺秦故事)都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如何从起点完满地走向终点,叙事成为这个过程中的担当者。因此本文以叙事学的方法尝试剖析《英雄》的故事从起点到终点的叙事缺陷。虽然《英雄》是原创剧本(编剧:李冯故事:张艺谋、李冯),但是刺秦的原型故事是久远流传的,因此也不能忽视它的民间故事的既定性。
人类的叙述行为的渊源和人类的语言一样久远,伴随着人类的进化和人类语言的发展而发展,并将伴随人类终生。有语言的地方就有讲述,远古的人类围坐在篝火旁开始讲述人类的第一个故事。从此叙述行为在人类童年时代便开始了。
《英雄》的主题,是以“天下”来消解暴力,但其最终却是维护甚至美化了真正的暴力。《英雄》不被接受的正是它所流露出的这种文化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我们准确读解出叙事文本的动素模型,我们已经初步把握了叙事文本的叙事结构。尤其是一部叙事性作品的时代或者说历史特征与某种文化意义定位。因此,从反方向的角度来说。当我们已经发现一个文本透露出的某种不被接受的文化意义,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使用关于叙事文本动素模型的分析来弄清其文化观念不被接受的原因。
影片是以无名的讲述展开的,也可以说在无名死之前他是故事惟一的讲述者,编造了青、红、绿、蓝的四个有真实成分的虚假故事,这不同于中国以往的武侠片,因此可以说影片在讲述方式上做了一些努力,这里且不谈张艺谋是不是在《英雄》这部武侠片中套用了黑泽明《罗生门》的模式。影片的外围框架是无名的行动、结局以及长空、残剑、飞雪包括秦王的结局;在这个框架之内,又有四个不同颜色代表的刺秦或者刺秦的前戏故事——青:长空于无名的棋馆决战;红:残剑与飞雪的感情纠葛;绿:残剑与飞雪共刺秦王以及飞雪的死(假);蓝:飞雪助无名刺秦。这四个故事单独存在并没有叙事上的破绽。主要是影片外围框架的故事与这四个故事联系之后呈现了逻辑上的矛盾。《英雄》的故事概括地说就是四个赵国刺客刺杀秦王最终失败的故事。我们从格雷马斯的主体——客体、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