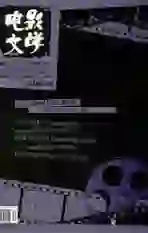《生死朗读》:从影像到对话
2009-04-15吴舒婷
吴舒婷
电影《生死朗读》改编自20世纪末德语成长小说代表作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在《时时刻刻》之后,导演斯蒂芬·戴德利苦寻良久,决定将《朗读者》搬上大荧幕。面对小说中所呈现的复杂的政治、道德、人伦、人性,戴德利说:“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只是没人关注过他们而已。而实际上他们往往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也正是这样的独特观点,才使《生死朗读》从斯蒂芬·戴德利的选择中闪耀出不一样的光辉,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提名,而女主角汉娜的扮演者凯特·温斯莱特最终凭借其精湛的演技荣获第8l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笔者试从电影镜头、段落、语言等方面解读其主题与人物,解析其深刻的人性内涵。
一、“不伦之恋”“历史罪人”阴影下的孤独成长
成长小说的“成长”有“塑造”“修养”之意。成长小说是一种着力表现稚嫩的年轻主人公历经各种挫折、磨难,得以顿悟,最终长大成人的心路历程的一种小说样式。改编自成长小说《朗读者》的《生死朗读》也是一部成长电影,讲述了一个超越社会伦理的悲情成长故事:15岁的德国少年米夏从肉体到精神爱上了36岁的列车售票员汉娜。诗意朗读的爱情场面,汉娜的不辞而别,孤独的痛苦给米夏的人生留下了难以逃避的阴影。8年后,作为见习律师位列审判席的米夏遇到作为纳粹集中营狱警的被告人汉娜,他放弃了为汉娜辩护的权利,而汉娜在终身监禁和承认自己是文盲的两难境地中选择了前者。米夏结婚后离婚,跟女儿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却依然为狱中的汉娜朗读世界名著,并录成一盒一盒磁带寄给她。苍茫岁月中,米夏和这些磁带成为汉娜惟一的安慰,并激发了她读书识字的热情。18年后,米夏准备迎接出狱的汉娜,却发现她用自杀作为人生最终的谢幕。
影片开头的第一个场景,是1995年的德国。中年米夏有条不紊地准备着早餐,洁白的瓷具、洁净的桌面、整壁的书柜以特写镜头的方式展现在观众眼前,这暗示米夏具有安静、独立、博学的性格特点。“没叫醒我,是你不能忍受跟我一起吃早饭”,一位赤身裸体的女子打扰了这份宁静。她简单的开场白让我们心中留下一个疑问:米夏为什么不能忍受和自己喜欢的女友吃顿饭呢?接着,这个女人又问:“有没有哪个女人跟你在一起,弄清你脑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一个女儿。”米夏尴尬地站在那里,一个人,似乎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女人离开,他一个人站在未整理的卧室,呆呆地看着白色的床单;一个人伫立在窗前,眼前飞驰而过的列车上,似乎有他曾经的自己。接着,他大力关上门窗,想要把不能说的秘密关在窗外。一切都是无助的,回忆的巨大推力促使他来到1958年的西德,他15岁。那是下着雪的冬天,米夏得了黄疽病,却意外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汉娜,由此拉开了他由天真、受挫到迷惘、顿悟的成长历程。这段历史也回答了影片起始段落女友的问题,他是一个有秘密的人,他不愿与人分享过去,而这个秘密就是他15岁时迷恋着36的汉娜,那个健硕美丽、爱听他朗读名著的汉娜;他23岁时痛恨并爱着44岁的汉娜,那个前纳粹狱警、迷失人性的汉娜。之后的许多年,他重复着失败的爱情、亲情、友情,她的女儿在影片中含着泪说:“我以为你一直不喜欢我。”他的母亲说:“你父亲去世,你也没有回来过。”谁叉知道米夏的痛苦?
“恋母情结”的惊世骇俗、得知恋人是前纳粹成为米夏的不能承受之重,汉娜的双重身份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只能保持沉默。影片进行到20分钟时,米夏的老师在课堂上说了这么一句话:“秘密是西方文学的重要部分,你可以说角色的所有想法在小说中都被人们所持的特定信息所否定,这是有很多原因的,也许是因为固执,也许是因为高尚,他们决定不去揭露。”从15岁开始,米夏的一生在他人看来是神秘的。因此在面对家人对他离家出走的审问时,米夏独自沉默;在青年时期的法律课堂上,他独坐一隅;在纳粹集中营遗址里,他独自徘徊;在结婚生子后,他抛妻离子……《生死朗读》中的青年米夏、中年米夏,总是拉长着孤独的身影出现在电影里,被周围棕黑色的景物包围,淡淡的灯光照在他单薄的身躯上,显得异常孤独。米夏给我们留下的,永远是寂寥的背影。
二、“朗读情结”以文学体验
超越罪恶生存的逆向反思
汉娜突出的性格是自尊自爱。个人尊严是汉娜的生存底线,她为了守护自己不识字的秘密,放弃了西门子公司的升迁而盲目选择了做一名纳粹狱警。在8年后的审判席上,汉娜再次做出同样的选择,情愿用自己的后半生交换“我不是文盲”这一可悲又可笑的尊严。当听到法官宣判她被终身监禁的时候,我们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恐惧,从她身体的颤动中感受到隐忍。无论如何,她愿意承认这样的结果。她的秘密与米夏的不同,米夏的秘密是不伦之恋,大部分源于社会压力,而汉娜的秘密则是自我认同的压力。她的自尊自爱与纳粹的非理性仇恨融合在了一起:她听孩子们朗读,然后送她们去集中营进行屠杀;她监管300多犹太人,为了所谓的“职业道德”不肯开教堂的大门,让他们活活烧死在烈火中。她的罪过既不来源于戈德哈根《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中“消灭主义”的普遍文化信念与思维方式,也不是阿伦特《极权主义之源》中的极权暴力三步杀人法,她的暴虐仅仅源于一个没有文化的妇女对知识的渴望。这种执拗的“朗读情结”与法西斯主义的凶残带给了她人生的一系列灾难,她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在电影镜头与电影段落的充分展现中,汉娜的语言、动作都试图以文学体验超越罪恶生存。在影片开始的50分钟里。导演用写实主义的镜头直白展现汉娜与米夏的肉体之爱。裸露的身体几乎贯穿了他们的每一次见面,36岁汉娜主动引诱未成年的米夏,并从他身上索取青春的激情。看到这里,仿佛汉娜对米夏的爱只限于感官的快乐。随着影片的深入展开,我们看到汉娜主动要求米夏为他朗读经典著作,并将其作为他们交往的首要条件。电影加快视觉节奏,呈现不同场景的朗读场面:在床上、沙发上、浴池里,他们都赤裸着,米夏读得非常认真,汉娜听得非常入迷,复杂的视觉脉动使得他们每次见面的主题成为“朗读”,逐渐冲淡了情爱的因素。艺术消解了欲望,朗读使汉娜找到了作为知识人的尊严与自信,在狱中她以这样的方式和米夏保持着联系,并因为热爱书本中所渗透的审美艺术而读书识字,终于使自己能够自由畅游于艺术的博大与宽广。相信老年汉娜用手一一对照“A Woman with the Little Dog”这六个单词的电影画面感动了无数观众。当汉娜终于可以写信给米夏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罪的生命可以转化为超然的灵魂,改变世界最大的力量仍是人伟大的心灵。
三、交往合理性“有效对话”后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从人本主义出发反对工具理性,强调人与人之间通过有效对话、交流达到相互理解。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合理性的作用是达到理解,其目标是导向认同,共享知识,彼此信任。认同以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
性为基础。汉娜与米夏的孤独感与罪恶感源自内心的禁闭与拒绝交流的姿态,通过与自己、与他人不同方式的有效对话,他们重新认识自己、接受自己并最终放下了过去,实现了自我救赎。
汉娜的人生充满罪恶感,她通过朗读认识自己、完善自己。通过与文学作品的有效对话对自我进行了救赎。根据影片情节,除了米夏这位少年恋人,她没有家庭,也没有朋友,深居简出在电车公司的集体宿舍。可以这么说,她是一个与社会绝缘的人。汉娜的现状没有污点,她是一名兢兢业业、业绩突出的售票员。可她不愿意对米夏说出自己的姓名,面对写有文字的菜牌她会心慌,而签字这一动作可以让她决定从米夏的生活中悄然消失。这所有的电影段落都预示着她过去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她的秘密不是爱情,而是作为前纳粹狱警的卑劣身份。她赎罪的方式非常特别:在与米夏的乡村之旅中,她来到教堂随着唱诗班的歌声流泪。也许是为了因她的冷血而遇难的300犹太人;在学会读书后,她阅读了大量与集中营有关的书籍和文献,开始摆脱无知者无罪的状态,深刻反省自己的人生。汉娜曾试图在狱中用仅有的文字“Write to me”联系米夏,却一直没有收到回音。她明白在米夏的内心深处始终没有原谅她,就像犹太妇女和她的女儿一样对她曾经的无情、罪恶采取决不宽恕的态度。最终,她在书籍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她用生命的结束换取世人的宽宥。得知汉娜去世的消息,米夏蜷缩在她生活了18年的牢房里恸哭,相信这一意外的结局让米夏彻底原谅了汉娜对他整个青春和人生的伤害。在犹太女作家收到汉娜在狱中存放零钱的破旧茶叶罐时,曾说自己没有权利收下汉娜给她的7000多马克,因为收下这些钱仿佛就是原谅汉娜屠杀犹太人的罪孽,“我没有权利代表所有遇难的人原谅她。”但是,她把茶叶罐放到自己的梳妆台前,以个人的名义完成了汉娜赎罪的心愿。
哈贝马斯所认同的交往合理性是基于语言行为而建立起的主体间的理解和认同的活动。我们的历史理性关注点应该从“主体——客体”结构向“主体——主体”结构转换。正是主体间的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可以消解感情被异化的性质,因而被哈贝马斯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电影结尾。米夏通过与女儿的促膝谈心达到了主体间言语的有效性。汉娜的离去启发了他,使他有勇气像汉娜一样直面自己的秘密。他和女儿来到汉娜的墓前,用手轻抚汉娜的墓碑,以平静的语言述说自己的15岁:“那一年,我得了黄疸病,有一个女人救了我……”米夏与女儿之间多年的情感隔阂与不解在这一霎烟消云散。如果没有这段对话,米夏在亲友眼中仍然是那个“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的孤僻怪人。影片通过对汉娜和米夏个人历史的“重建”,以全新的理解方式实现了他们对彼此、对历史的个人救赎。
四、结语
《生死朗读》的电影风格简洁凝练,画面没有被刻意艺术化的痕迹,保持了这段个人成长历史的原貌。导演也没有对这个故事作多余的价值判断,观众却在中年米夏不停朗读、老年汉娜醉心欣赏的快速切换画面中感动流泪,超越了历史的局限,达到了对人性复杂性的个体认同:作恶不是简单化的想法,汉娜以个人尊严与时代之恶、制度之恶的结合给予观众一个崭新的视角——离奇大恶不一定有离奇的行恶者。
不得不说。凯特·温丝莱特饰演的汉娜还原了那个时代普通德国人的心理状况,无论是她的语言、动作还是神态,都与小说原著《朗读者》中的原型十分贴近。温丝莱特说:“饰演她的那种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了。而由于这个角色身份的特殊性,也让我在演戏时多了一份责任感,使我不得不全身心投入,认认真真来扮演她。”是温丝莱特精彩而准确的演绎,让汉娜的形象加入到夏洛蒂、洛丽塔、黛茜这些人类文学史上爱情女主角的行列,以经典性的不断解读呈现在一代又一代观众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