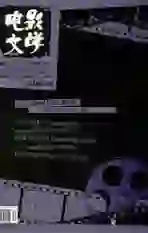《生死朗读》的修辞学解读
2009-04-15金蕾蕾
金蕾蕾
奥斯卡一向偏向于政治。特别对二战纳粹题材情有独钟,从《辛德勒名单》到《钢琴师》均获得“小金人”的青睐。2009年的《生死朗读》虽然新鞋走老路,可它走出了以往电影描写战争暴力与蛮荒的模式,走向深切与沉实。影片以“战后一代”德国人对“战时一代”德国人的盲目的爱——无由的怨——释怀的哀来诠释战争对人的伤害,以及人类应该从战争中反思什么。正如电影原著《朗读者》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所言,人们看到了包含在其中的某些相通、共同的东西: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而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中去,并将由此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下一代于这罪恶的阴影之中——这一切当然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主题。从这一点而言,《生死朗读》超越了之前此题材的影片。
一、从亲密到间离: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流转
从修辞学的角度出发,《生死朗读》具有三个相关层面的叙事视角。这三个相关层面是:(1)内部层面,是由汉娜·施密茨叙述的:关于她在二战时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做女看守的故事,此故事可称之为汉娜的故事;(2)中间层面,是由米夏·伯格叙述的:关于他与汉娜从偶然邂逅到阴阳两隔的一段人生经历,这是米夏的故事;(3)外部层面,即导演史蒂芬·戴德利作为隐含的作者所描述和构想的层面:戴德利与其隐含的和真实的读者进行的大体上说是隐秘的交流,即叙述者讲述的米夏所讲的关于汉娜的故事的故事,这属于戴德利的故事。
电影的前半段陷于米夏的故事中。从15岁的米夏在一次巧遇中认识并热恋上36岁的妇女汉娜讲起,直到汉娜突然消失,这段隐秘的恋情宣告终结。然而,当米夏作为法律系大学生参与法庭实习的时候,审判的战犯之一竟然是汉娜,并知晓这位让他初食禁果、由此通晓生命隐秘的女人,竟然是纳粹时期臭名昭著的女看守。米夏哑然了。读者也哑然了。至此米夏所有的震撼都能够严丝合缝地传递给读者,让每个受众都感受到从爱的天国瞬间坠入地狱的失重之感。于是,秉承着要拯救汉娜的信念,读者跟随着米夏一起走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些不同于历史书上的真相,为纳粹时代的“魔鬼”找到一线救赎的希望,哪怕是零星的同情。
摄影机跟随着米夏走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故事便从庸俗的情欲主线悄然转化为严肃的历史主线。米夏穿越铁丝网,打开木质门。走在如同监狱一般的营房里,毒气室外如山般的鞋子,焚尸炉旁无声的定格,都像一个个幽灵死死盘踞着米夏的心灵。仿佛每一双鞋子都在伸出骷髅般的双臂,撕扯着米夏的衣裳,也撕咬着读者的心灵。不由得,我们一边放弃了对汉娜的救赎,另一边又不由得慨叹人在历史的大灾难面前的渺小和脆弱。此时米夏对汉娜的爱与恨仍各占一半。直到法庭审判时,当所有的女看守把责任都推到汉娜的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人性之恶,它并没有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而从人的血液中抽离开来,而是根深蒂固地蛰伏着,等待机会再跳出来反吃他人一口。汉娜最终为了保留最后的一点尊严。而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她宁愿死去也不能活得没有尊严。终于,在这一刹那,人性的天平上,善的同情彻底战胜了恶的谴责。
从法庭宣判之日起,电影的镜头逐渐走离了米夏的内心世界,趋向于导演史蒂芬·戴德利的故事。原本以为,米夏在经过这场回归历史真相的朗读之后,能够站出来为女看守说些什么,但很遗憾他没有,他除了保持缄默,没有任何的举动。这种遗憾归因于电影的导演戴德利,在他的故事中,他并没有勇气站起来。与历史作一场辩论。米夏的退却,亦是戴得利的退却。在探寻真理、还原历史真相的这条朗读之路上,戴德利抽身而去,却将重心放在了后面的感情纠葛之上。就如同马上可以掀开上帝华美的皮袍,一窥究竟,但戴德利却怯然收手。这组镜头应该是这部电影最大的败笔。
二、从倒叙到顺叙:历史与现实的视角变迁
电影作为艺术的基本样式之一,其与历史之关系不能简单以对抗一词来说明。迈克尔·伍德在论及文学与历史之关系时指出,“文学与历史(的书写)距离太近了,以至无法抗拒它,而且很多时候文学就是历史,只是披上了比喻的外衣。然而文学有着一份脆弱的自主权,一种隐私和游戏的因素,它离超越还有一大段距离,但也正因为如此而更显重要。”作为一部糅合了情欲与理智、叛逆与皈依多重矛盾的电影,历史在这部影片中超越了男女主人公,晋升为第一主角。它通过错综变换的时空镜头,向我们讲述了一个遥远且虚幻、切近亦真实的故事。按照历史的角度出发,遵从于汉娜的故事演进时间,电影原本应该是采用顺序的时间,因为顺序手法更真实。但是它却采用了倒叙和插叙贯穿的手法,即将汉娜的故事通过米夏的话语讲述出来,这便出现了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的“错位”结构。
按照电影中米夏的话语时间次序:
A我离婚,并与别的女人同居,但没有结婚。(1995年)B15岁那年,我邂逅了汉娜,与其相恋,但她却突然消失。(1958年)C大学时,我旁听了对汉娜的审判。(1966年)D二战时,汉娜曾经杀害300名犹太人。(1944年)E离婚后,带着女儿回到故乡,开始给汉娜寄录音磁带。(1976年)F汉娜死去。(1988年)G我给女儿讲述我和汉娜的故事。(1995年)
而电影中故事的时间次序:
(1)二战时,汉娜曾经杀害300名犹太人。(1944年)(2)15岁那年,我邂逅了汉娜,与其相恋,但她却突然消失。(1958年)(3)大学时,我旁听了对汉娜的审判。(1966年)(4)离婚后,带着女儿回到故乡,开始给汉娜寄录音磁带。(1976年)(5)汉娜死去。(1988年)(6)我给女儿讲我和汉娜的故事。(1995年)
两个时间对比,则出现如下格式:
A(6)、B(2)、c(3)、D(1)、E(4)、F(5)、c(6)
错落的时间顺序,打乱了正常的阅读感受,让读者在无序中体会到一种情感的跃动、时空的变迁。影片中不断出现的时间印记,像一个个历史的符号在无言地表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是通过回忆的方式讲述的这个故事,则不断颠覆这种真实,造成玄虚的效果。历史永远是今天的历史,我们无法回到现场,也无须回到现场。毕竟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要学会跳出时间段落去沉思默察,而不能禁锢在历史教科书所描述的片断中不能自拔。细致地审视这段暴力的历史,不要让杀戮的鲜血模糊了善恶的分界,让上一代人的罪恶成为下一代人的精神负累。如同本哈德·施林克在《朗读者》中所写到,过去的可怕历史上已经积满了一层尘埃,我们用力地把窗户打开,让最终能卷起这种尘埃的风进来。
三、从法庭到教堂:他审与自审的身份置换
格雷马斯曾指出:“所有的叙事文本乃至全部文本中,一定包含着一个意义的深层结构;而这一深层结构是一组核心的二项对立式(设定为A/B)及其他所推演出另一组
相关且相对的二项对立式(-A/-B)建构而成的。”按照这样的解释,故事中人物关系往往出现六对三组关系。其中A与B、-A与-B之间是对立关系,A与-B、B与-A之间是互补关系,A与-A、B与-B之间是矛盾关系。
但《生死朗读》中的汉娜和米夏之间不存在A与B的对立关系。汉娜虽然是纳粹集中营中的女看守,道德法庭的罪犯,但是在故事的开始,她无私救助得了猩红热病的米夏,便必然不会成为米夏批判的对象,甚至逐渐成为米夏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女人,以至影响到他后来跟任何女性的交往。即便当米夏在法庭上识破了汉娜的真实身份,他们之间也没有建构起对立关系。所以在电影中,承担起对立矛盾的两个角色,不是男女主人公,而是以教堂和法庭为象征的审视身份。
教堂代表着救赎,她以平和的心态去化解人间灾难:法庭代表着惩罚,她以复仇的心态去消解世间矛盾。更确切地说,对于汉娜来讲,教堂意味着生,而法庭意味着死,决定生与死的,不是人本身,而是历史本身或者说社会身份。正如汉娜对米夏说的,“在审判前我没想过过去,也从不用,现在我怎么看(过去)不重要,怎么想(过去)也不重要,人死不能复生。”米夏原本作为法庭的代表,在汉娜出狱之前准备再次审问这个纳粹的女看守,但是,这种他审是如此的无力,它经不住汉娜的回驳。就如同汉娜当年驳难审判长时所说的,“如果当时你是我,你该怎么办?”在历史的面前,人是无助的,既无法改变历史,更不能规避矛盾,全身远离。在上帝的面前,人是被审判的对象,没有人能永行善事,远离罪恶。可是在法庭之上,更多的人选择逃到道德的庇护下,用是否合法或者合道德的眼光来审视他人,任意阉割他人的生命意志,却没有以上帝悲悯的眼光放生命一条光明的出路。
最终汉娜选择了自杀,这样的方式不是屈服于法庭的裁夺,在他审的状态下负罪地死去;而是自审其人生旅程,在摆脱文盲进入现代文明之后,顿觉无颜苟活于世间。如同《圣经》中亚当与夏娃,在没有偷吃苹果树上苹果之前,无所谓善恶对错;而一旦吃掉了象征现代文明的苹果。便被逐出了美丽的伊甸园,带着重重的诅咒与罪恶行走于人间。米夏为汉娜的朗读,就如同一口口吃苹果树上的苹果,一声声将汉娜从“黑暗”引向“光明”,从麻木变得自尊,从自尊踱向自卑,并最终与“黑暗”一起灭亡。无意之间,《生死朗读》再次印证了西方启蒙主义的悖论,启蒙将愚昧之人变得敏感,但最终却加速了他们的死亡。米夏以为可以通过朗读改变汉娜的精神世界,却没有料到加速了她死亡的进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生死朗读》的主题。
《生死朗读》不同于当下美国电影流行的纳粹或屠犹的题材,更不是教人皈依于道德的众口一词,服膺于清晰的善恶标准。它是关于罪责的一部电影,受鞭策者绝不仅仅是手持屠刀的魔鬼,而是关于文明与愚昧、道德与野蛮、启蒙与愚众、自然与心机、真实与谎言众多悖论支撑的“人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