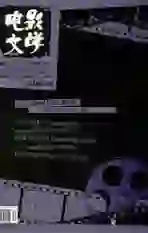“杀人”或“衰老”:杨德昌电影世界的两面
2009-04-15李骏
李 骏
[摘要]本文从形武、风格、内容、主题、文化内涵等层面探讨了杨德昌电影的两面:“杀人”或“衰老”。“杀人”或“衰老”既是杨德昌作品中的剧情表征,也是导演思想深层的精神折射。“杀人”意味着抗争与批判,“衰老”意味着宽容与平和。自《一一》始,杨德昌不再以“杀人”来排解整个时代的压抑与苦闷,“衰老”成为导演的真实心态与境遇。影片《一一》体现了导演由批判现实到超越现实的终极人文关怀。
[关键词]杨德昌;导演;“杀人”;“衰老”
在杨德昌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一一》的结局,导演借小男孩阳阳之口。以稚嫩的口吻脱口而出这么一句:“我觉得。我也老了。”童真的话语却触及观者心底最深的柔软,作为自我电影乃至人生的终结之作,导演以一种包容与平和的姿态画上了句点。这是一个曾经叛逆、曾经愤懑、曾经忧郁、曾经焦虑的儒者的衰老,在经历了一次次叙事的矛盾与焦灼后,仿佛有了洞悉世事真相以后的智慧。“杀人”或“衰老”,是杨德昌电影世界的两面:“杀人”是批判,是对立;“衰老”是宽容。是平和。如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张扬着青春期的抑郁与悲痛,小四的杀人事件则是导演对传统、对世俗的抗争与不妥协,那么,10年之后的《一一》呈现的是明朗的现实与衰老的容颜。
作为对民族传统充满悲悯的儒者、对现代社会保持警觉与自省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杨德昌深受东西方两种文化价值的交融影响。在他的影片中,无时不体现着传统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的对接与冲撞。在李安的影片里,东方传统浓缩于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形象中。父一代的权威岌岌可危的20世纪,为子一代的青春期造成了先天的价值真空;家庭中父子关系的纠葛与矛盾正是传统与现实的隔阂与调和的暗喻。身处同样的时代语境,父子关系的主题也是杨德昌乃至侯孝贤影片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线索。《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保守、传统、固执、耿直的内地父亲,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与时代氛围下,难以维系自身坚守的信仰甚至其作为父亲的尊严;《麻将》中,父一代的价值信条在现代城市的魔咒下被彻底异化并坍塌,子一代是继承者、叛逆者,也是回归者一从1996年的影片《麻将》结局中的少年杀人事件始,杨德昌影片中的传统与现实不再是对立与不可调和的两极,子沿袭了父、皈依了父、与父握手言和,这才进而有了《一一》中的父子之间的朋友般的默契。
台湾影评人焦雄屏说:“杨德昌是世界性的。”杨德昌电影的世界意义体现在他对于现代文明的深刻批判上,从这个意义而言,台北既是台湾的也是世界的。杨德昌在西方学习、工作、生活多年,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城市文明有着诸多深刻的体察。而杨德昌电影里的台北就是他在深刻批判以后建构的一个城市标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北在现代化都市的建设进程中飞速发展,实践着其对于西方的现代性想象。杨德昌电影中所展现的台北的城市空间光怪陆离,有一种让人窒息的局促与压抑,与诸多欧洲现代主义影片所表达的主题相近,涉及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强烈疏离感、人性的异化以及个体生命不可名状的孤独。因此,杨德昌既是一个地方性、区域性的导演,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现代意义的导演。
杨德昌总是善于把具有尖锐批判性的理性哲思转化为影像,固定镜头与大景别的镜语,体现了导演冷眼旁观的叙事风格。《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杀人场景,以固定的长镜头的远景表面表现夜色下台北街头被动、无知、凄惶的少年小四的哭喊,导演越是克制镜头的运动与距离,也就越是表达了被摄人物强烈的孤独与无助。《一一》中有两次出现NJ的主观镜头,都是固定镜头大景别的画面,一次是在电梯口目送着自己的初恋情人阿水远去,纵然心中有万语千言,但在面对面的一瞬间,也只是沉默寡言,远景镜头表现了NJ在命运、感情方面的无助、被动与隐忍;另一次是在NJ去日本出差前拜会某富豪,隔着私家泳池远观对方,体现了中产阶级与上流社会的巨大差异与遥远距离。在杨德昌的作品中,固定镜头摄影不仅作为一种造型形式语汇,更是一种语法与风格。《恐怖分子》的一系列固定镜头的剪辑让人印象深刻,不同的人物活动在各自的空间,前后镜头的组合并不必然以具有时间线性的行动为线索,他们在剪辑的意义上是上下关联的,但画中人彼此的心灵是局限与隔阂的。《一一》中婆婆瘫痪在床、众人一齐在家的场景,即使是缩减到一户家庭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范围,我们依然看不到众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婷婷、阳阳、NJ、敏敏、阿弟,每个人只是在面对失语的婆婆时才流露出真我的状态。NJ去东京出差前在家收拾行李,婷婷打开家门,NJ临行前关照女儿,导演并未让父女二人身处同一画框之内,只是在狭长的房间两端给以正反打三镜头,三镜头中父女的形象惟一出现在同一构图内的。是拍NJ时同时出现了他身后的镜中的婷婷。
同为台湾电影的领军者,侯孝贤似乎更善于表达台湾乡土、一个前现代的台湾社会或者处于变迁与转型期的台湾社会,而杨德昌的电影无疑是属于城市的,他心系城市,观察城市,记录城市,也批判城市,他的影片是地地道道的城市电影。因为杨德昌是一个理性思考并且毫不留情地批判现实的电影作者,他批判的焦点集中于资本主义现代城市文明的诸多现状,所以,台北的城市空间借由杨德昌的影片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杨德昌的镜语对于城市空间的表达是风格化的。此时,空间凝聚了他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空间就是现代都市中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生活的舞台,空间表达了导演对于孤独而无助的人物的深沉关怀。电梯与玻璃是我们在《一一》中最为习惯见到的两种重要的场景。电梯让剧中人物一次次尴尬地遭遇,局促的空间与疏离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戏剧化的碰撞。玻璃则被导演借用来构成更为广泛而深刻的隐喻。影片中多次出现人物面对窗外的夜色悲伤或哭泣的情景,影像巧妙地把室内的人、室外的城市夜色合二为一,迷人而又黑暗的城市夜景,潜伏了人物悲伤的心绪——而这悲伤的情绪,这迷人的夜景,究竟谁是幻象?同时,又有一些场景,导演把机位隔绝在玻璃橱窗之外拍摄店铺内的人物的活动与言行,严格地限制住自己的视角。杨渭汉的摄影风格与李屏宾有些许神似。在莉莉因发现母亲与老师的关系而大闹一场,机位被局限于门框之外,表现了婷婷作为旁观者的视角。在侯孝贤的影片中,这种框式构图的风格更多地被用来表达人与空间合二为一的和谐氛围;而在杨德昌的作品中,它是一种冷眼旁观的视角与立场,导演刻意保持着自身冷眼静观和理性陈述的姿态,而不是急于介入并表态。
看杨德昌的作品,我们常常会感到彻骨的冷漠与寒凉,这不仅来自于他叙事的内容,也来自于他叙事的姿态。在他的作品中,人物与人物是疏离的,而导演作为叙述者,与他所创造的人物也是疏离的。因此,杨德昌是一个冷眼旁观的写实风格的电影作者,大量的固定长镜头、大景别画面、有源音响的应用,都证实了这一点。在《一一》之前的作品中,对于社会现实的冷峻记录渗透了导演对于现实的尖锐批判,这是残酷而又让人绝望的黑暗现实。在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在《恐怖分子》中,在《独立时代》中,在《麻将》中,黑暗,是杨德昌对于现实进行描摹时所使用的最深最重的底色。《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多次出现在黑暗场景中完成的屠杀或杀人事件。如果说黑暗是现实,那么,杀人就是个体生命内心所有愤懑郁结的悲情释放。杨德昌的作品中,杀人更像是实施者的抗争与呐喊,与时代抗争、与现实抗争,杀人者正是需要社会给予关怀和同情者,因为杀人事件本身揭露了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怪诞与病入膏肓。
可贵的是,杨德昌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不仅停留于感性的抗争与呐喊的层面,他的批判是理性的、全面的。他对于庞杂叙事的把握与掌控的能力极强,这或许得益于他接受教育的背景。1986年的《恐怖分子》初步奠定了他的群像电影的叙事风格,而2000年的《一一》更使他的复调叙事风格日臻定型与成熟。他要的不是对于一人、一事的讲述,他关注的是对于整个社会现实的记录。在他的影片中,常常是众多人物各自的线索彼此交替被叙述,在结构上互相关联,让人在总体上反思社会现实。影片《一一》中,一边是NJ在东京与初恋情人约会,追忆往昔,一边是婷婷在台北的街头开始了自己的初恋。结构上的交织暗示了父女之间生命历程的某种神奇的关联,上一代的故事竟然在下一代身上宿命地重演。《一一》中主要讲述了五个主要人物:NJ、敏敏、阿弟、阳阳、婷婷,各自的生活轨迹都是孤立发展的,但导演巧妙地借由一些人生或家庭重大仪式,让各条线索汇集到了一起。影片中贯穿了婚礼、出生、死亡这样一些人生重大仪式,借由一部影片的讲述,观者仿佛经历了人生风云,而导演借此关怀了人的一生。
如果说,《一一》之前的杨德昌电影延续的是对于社会现实的猛烈批判,那么《一一》开始,一种强烈的终极人文关怀超越了批判与愤懑,年岁渐长,杨德昌开始思索生命与生活的本来意义。影片中阿弟和即将生产的妻子在医院观看显示屏上腹中胎儿的画面时,导演以声画分离的形式穿插了NJ在办公室正在进行的会议:“我们目前无法超越只能打人、杀人的一般电脑游戏产品,并不是我们不够了解电脑,而是我们还不够了解人——我们自己。”本片依然保有深刻的批判,更重要的是,自《一一》始,杨德昌显得平和而感性,这不再是那个以杀人来排解整个时代的压抑与苦闷的青春故事,衰老成为远离了青春期之后的作者在当下的真实心态与境遇。NJ与阳阳是杨德昌在影片中的两个代言人,NJ诚实、坦荡地面对生活的焦虑与无奈,阳阳则大智若愚、洞察世事。《一一》的色调变得明朗了,杨德昌从疏离到重新回归生活;《一一》中的杀人事件不是没有,但也在叙事上被淡化了……相比于“杀人”的母题,《一一》更为深刻地表达着“衰老”。
《一一》的平和并不意味着与现实的妥协,批判的气质在影片中依然延续着,但《一一》中我们更多感到的是杨德昌在超越现实之后对于人生的彻悟,是超越了理性的思辨之后的诗意与感性。在影片结局的一场睡梦中,婷婷与婆婆相遇,婷婷不再孤独,重温了婆婆的微笑,而梦幻中婆婆的笑靥,现实中竟是婆婆的离世。梦境与现实、生与死、苦与乐在杨德昌的影片中构成了诗意的对接与轮回。现实中求之不得的,在梦幻中憧憬,曾经愤世嫉俗的杨德昌以梦的方式对人生的悲苦酸甜置之一笑。梦幻的结局在《恐怖分子》中也有应用,李立群饰演的公司小职员在梦境中杀人,在现实中自杀,梦幻与现实仿佛都是叙事的两种假设——“杀人”或者“衰老”。现实或者梦幻,成为杨德昌电影世界里一直延续着的一分为二的双重主题。在对于现实的猛烈批判的意义上,杨德昌的电影是写实的,在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探究上,杨德昌又是超越现实的。东西方的双重教育构成了他的思想与人文背景,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他的作品中读解到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微妙融合。
从电影美学来看,写实主义的杨德昌又从不忽略戏剧化与技术主义,他的叙事结构与镜头语言的严密与精确在华语电影中堪称罕见。他寻求把对于社会的批判与悲悯以一种社会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传达出来。他的作品中人物的普遍话语过剩0成为杨德昌电影的标志之一,喋喋不休的台词让人印象深刻,这让他的电影看起来显得颇为说教。作为负责任的电影作者、独立思考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以这样的方式揭示时弊。而归根到底,夸张的独自只能表明言说者的孤独,因为这是一个人与人心灵的沟通。有着严重障碍的当下社会,越是表白自我,越是说明聆听被稀释。所以,杨德昌电影中的人物是孤独的,而杨德昌自己也是孤独的。智者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