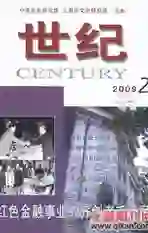海派收藏异彩纷呈
2009-04-13吴少华
吴少华
海派收藏,是当今中国民间收藏舞台上的一面灿烂旗帜,也是上海城市文化品格的重要体现,更是解读海派文化的一个窗口,本文从海派收藏的形成、发展及特色作介绍,让读者对海派收藏有所了解。
一、肇始于上海开埠的海派收藏
上海自宋末建镇,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建县,到了明嘉靖以后,上海已发展成为我国“东南之都会、江海之通津”的重要港口。清康熙年间开放海禁,老城厢小东门外沿黄浦江一带帆樯林立,万商云集。此时的上海已成为我国一个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它在社会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为民间收藏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843年的冬天,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上海打开了对外开埠的大门。1845年以后,英、法、美三国次第在上海老城厢北面建立了租界,从此上海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这样大潮汹涌的历史环境下,它使上海的本土文化迅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欧美的洋文化抢滩上海,另一方面国内其它区域文化也浩浩荡荡地进驻上海。这便是海派文化的肇始渊源。清同、光时期,有一位因避太平天国战火而旅居沪上的杭州人葛元煦,他在上海生活了十五年后,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以一个文人墨客的感触写下了一部叫《沪游杂记》的著作。这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写真集,应该说是当时上海滩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在《沪游杂记》中,有着颇多的关于古玩、书画、工艺品、收藏品的记载,可让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例如在第二卷中,编列了“书画家”、“笺扇”、“照相”、“油画”、“拍卖”、“百虫挂屏”、“玻璃器皿”、“古玩”、“藤器”、“雕翎扇”等条目,其中既有传统的“书画家”、“古玩”,也有外来的“照相”、“油画”、“玻璃器皿”,还有传统外来工艺的“百虫挂屏”。 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与历史环境中,海派收藏文化迈开了它的前进步伐,出现了最早的收藏家群体。
自上海开埠后,最早出现的收藏家群体,大多来自上海周边的江、浙、皖、赣的州府,例如苏州、常州、扬州、绍兴、湖州、宁波、徽州、南昌、芜湖、江宁等。这些州府地属富饶的江南地区,又是传统儒学深厚的区域。那些来自异地客籍人士,不少本身就是富甲一方的名门士族,他们离乡背井来到这个开放的热土,有的是为避战乱,有的是为图发展,更多的是慕名来享受物质生活当寓公的。这些来亦匆匆的各色人士,带来了金钱,也带来了细软,这细软就是珠宝、书画、古玩。清末有竹枝词写道:“寻常巷陌藏珍宝,半壁江山在申城。”其所描写的就是上海滩最早出现的民间收藏盛况。这些藏家所珍藏的无疑都是中华民族最最传统的古玩艺术品,也诞生了一个个在近代收藏史上名彪史册的收藏家,例如书画收藏家庞来臣、藏书家瞿启甲、古玩收藏家袁寒云、青铜器收藏家李荫轩、甲骨收藏家刘晦之、钱币收藏家丁福保、文物收藏家卢芹斋、吴启周等。这些富家的旧藏,不少至今可在国家博物馆见到其身影,它们见证了海派收藏传承民族精萃的功绩。
在海派收藏群体中,演绎与蕴藏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民国时期,被溥仪带到长春伪皇宫“小白楼”原北京故宫的1190余件文物流失,这些流失的皇家文物,史称“东北货”。现在提及“东北货”时,必提到大收藏家张伯驹,其实当时上海也有一个致力于收藏保护“东北货”的收藏家圈子,他们是收藏家庞元济、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集宝斋主人孙伯渊、嵩山草堂主人冯超然、韫辉斋主人张珩、密韵楼后人蒋谷荪、宝来斋室主人周湘云,以及鉴赏家王已千、徐邦达、谢稚柳与画家刘海粟、张大千等。这些收藏家们的收藏,其中不少解放后都先后捐赠给国家,例如周湘云将传世珍品唐朝怀素的《苦笋贴》及大小两具齐侯罍等青铜器捐入上海博物馆。孙伯渊1958年10月将4000余件金石碑文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又将李北海岳麓寺碑等宋拓法贴10种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馆,显示出一位藏家的高风亮节。
提到海派收藏群体,必定要提到一位女性收藏家,她就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潘达于,她所捐献的两件西周时期的国之重器——大克鼎和大盂鼎,如今成了上海博物馆与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潘达于的精神是感人的。她是清末著名大收藏家潘祖荫的后代。几十年间,她为了守住潘家百余年来的收藏品,机智地闯过了乱世灾年的种种磨难,仅抗战苏州沦陷时,潘家就曾先后闯进七批日本兵,其他财物损失不计其数,唯独伪装深埋在庭院地下的青铜大鼎丝毫不损,这位江南奇女子的胆识,令人折服。
申城的收藏群体,是从四面八方涌向上海的客籍人士,解放前后,在这个收藏群体中,又有不少走出上海,走向全国乃至海外,走到北京的有书画收藏鉴赏家张珩、徐邦达,走向海外的有收藏家张大千、王已千及陶瓷鉴赏家仇焱之等。
值得一提的是王已千与仇焱之。王已千是我国近代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书画收藏鉴赏家,早在193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准备参加在伦敦举办的“中华艺术国际公展”时,王已千被聘为艺术顾问,其时,年仅28岁。抗战爆发后,王已千举家从苏州搬到上海法租界,放弃律师职业,变卖掉房地产,专事收集书画。1947年首次访美,一年后定居纽约。王已千既是书画家,又是鉴赏家。据目前资料显示,他是搜藏宋元画作的首屈一指的收藏家。仇焱之早年师从上海昔古斋古玩店老板朱鹤亭,终成民国时期我国南方最著名的古瓷鉴赏家,1949年移居香港。仇氏生前与上海博物馆多有交往,1979年6月和10月,曾两次向上海博物馆出售古陶瓷器藏品共167件。
二、出现了海上收藏家群体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社会发生骤变,以大运河漕运为代表的内河文化走向了衰退,海洋文化正在撩开面纱。新生的上海滩冲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弥漫着自由自在气息,追求开放理念成为一种时髦。新思潮、新事物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不拘一格的上海人接受新潮的热情,更激起了这座新生城市的无限活力,塑造了前所未有的人气文脉。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周边区域的艺术家纷纷来到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原本风格各异的画家,为适应市场的需求,走到了一起,并形成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区域画派——海上画派,代表画家有赵之谦、虚谷、任伯年、吴昌硕、蒲华等。他们迎合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锐意求进,大胆革新,创造出清新活泼的画风,为收藏家们提供了让人们眼目一新的“现玩”。海上画派的崛起,开创了上海滩现玩受宠之先河,也塑造了上海民间收藏的人文底蕴。
随着社会的繁荣发展,上海人对现玩的热情,从书画辐射至更广泛的艺术领域。景德镇的“珠山八友”瓷板画的发祥与走红,是在上海滩形成的。玲珑剔透的浙江青田石雕,从上海滩走向了欧洲。精美入微的沈寿苏绣作品耶稣像在获得世博会金奖前,主要的追捧者在上海。当代紫砂泰斗顾景舟,1942年来上海就应聘标准陶瓷公司。后来,他又通过老城隍庙“铁画轩”老板戴相民,结识了一批沪上著名书画家,如江寒汀、吴湖帆、来楚生、谢稚柳等。江寒汀非常器重顾景舟的紫砂壶,顾景舟于1948年为江精心制作了一把石瓢壶,并请吴湖帆作画题书,一面为竹叶,另一面书题:“寒生绿罇上,影入翠屏中。寒汀兄属,吴倩并题。”当代紫砂大师徐秀棠在他的《紫砂泰斗顾景舟》一书中,记载下这段上海民间收藏的佳话。紫砂壶在沪上受宠并非只有顾氏一人,民国时期在上海滩上行俏的紫砂艺术家有一个灿烂的群体,例如俞国良、冯桂林、蒋燕亭、裴石民、程寿珍、王寅春、朱可心等。当时上海滩有诸多专营紫砂的商户,出名的有铁画轩、吴德盛、陈鼎和、利永、葛德和等。
上海的收藏家并非一味追尚现玩,更多的则是古、现并举,兼容并收。以吴湖帆为例,他可称得上是海上藏界一巨擘,其斋名有“梅景书屋”与“四欧堂”,均取自他的收藏,前者源于宋刻《梅花喜神谱》与米芾《多景楼诗帖》,后者出自所藏欧阳洵《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等四件碑帖,每一件都是国宝级的藏品。一身傲气的吴湖帆好古而不薄今,他还有个“二十四斋堂”的斋号,便来自于他的现玩收藏。这位大收藏家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收藏当时丹青名家的作品,他们是沈剑知、吴华源、郑午昌、吴待秋、冯超然、陈小蝶、张大千、樊少云、刘海粟、应野平、陆俨少、唐云、谢稚柳等24位画家,前后二十年,共两长卷。吴氏玩出了名堂,也玩出了海派收藏家的风采。
在上海滩收藏家们矢志不逾地传承精萃时,由于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特殊的地理、经济、社会的条件,西风渐入,洋收藏品率全国之先登陆上海滩。1912年,在沪外侨成立了“上海邮票会”,一个名叫李辉堂的中国邮商参加该会,并担任最早的中国籍理事。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集邮组织。1922年8月,为与上海的外国人邮票会分庭抗礼,一批中国集邮者在沪成立了“神州邮票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有影响的集邮组织,首批会员22人,也是中国最早的集邮家群体。1925年7月,“神州邮票研究会”正式改名“中华邮票会”,其主要发起人便是“邮王”周今觉。
在早期的民间收藏活动影响中,除了邮票外,就数钱币。钱币最早的收藏组织也在上海。1926年,著名的古钱收藏家张叔训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集币组织——古泉学社,并出学术刊物《古泉杂志》。该社成员不少系当时的社会名流,如罗振玉、董康、宝熙、袁克文、陈敬弟、丁福保等。虽说这个集币组织只生存一年的时间,但对全国的钱币收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36年2月23日,一个更大规模的集币组织在上海诞生,它就是“中国古泉学会”。会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历代古钱大辞典》的编篡者丁福保,叶恭绰与张叔训担任副会长。到了1940年,著名集币家罗伯昭来沪发起创办了“中国泉币学社”,丁福保再次出任会长,这个组织后来发展到全国,成为一个拥有近200个社友的全国性泉币组织,同时也是解放前历时最长的集币组织。云集了当时国内集币最强势的人物,他们是丁福保、罗伯昭、郑家相、王荫嘉、张絅伯、蔡季襄、戴葆庭、张叔训、张季量、杨成麒、陈仁涛、孙鼎、马定祥等。
据有关资料显示,最早的火花集藏社团也诞生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什么这些民间收藏组织最早都问世于黄浦江之畔?源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创新的巨大活力,冲破了传统的束缚,适应了这些社团走向更广阔社会的追求。那些我国最早民间收藏组织的发起人与创办人,清一色都不是上海土籍,而是来自异省他地的客籍人士,这就是海派丈化的魅力所在。在这种城市文脉的沿袭下,当民间收藏在“文革”结束后再度崛起时,中国最早的省市级法人收藏组织——上海市收藏协会便应运而生(当时叫“上海收藏欣赏联谊会”)。
三、民间收藏交流进入市场化
清同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862年的6月2日,一艘西洋式三桅船鼓帆驶入黄浦江,这是来自于日本的“千岁丸”幕府官船,开始对上海的访问。此时的上海战云密布,太平天国的大军第二次围攻上海,恰值多事之秋。随船而来的有一位叫纳富介次郎的专业画师,他也是位收藏家,故较多接触到书画古玩市场,后来写了一本《游清五录》书。这位很具慧眼的日本收藏家,还是买到了许多真古玩,在他的游记中,留下了很多出入申城古玩店,寻觅古玩,交流书画的记载。
清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战火燃遍了江南大地,为避战火,江、浙、皖一带的富贾士族逃往上海,随之而来的艺匠与古玩商人也涌到上海滩了。这些从事古玩经营的人士,大多来自于南京、镇江、扬州、苏州一带,他们来到上海后,便在老城隍庙的西侧旧校场及侯家浜落下脚,为我们留下了“旧校场年画”的遗产与海派玉雕及海派红木家具的生产制作技艺。买卖古玩的,形成了老城隍庙古玩市场。最早的古玩市场设在侯家浜即今侯家路上,那些从业者以回族人居多,且眼力极佳,故有“回回识宝”的说法。后来,古玩商进入了室内,在城隍庙的茶馆聚集成市,据清宣统元年初版的《上海指南》卷八载,城隍庙“四美轩”有前后之分,“前四美轩”茶馆饮客古玩帮为多,“后四美轩”则以翡翠帮居多。当时在茶楼里进行的交易,大多为同行间的“叫行”。进行交易的古玩商有两类:一类是穿街走巷的收购者,称之为“抱筒子”,他们到茶楼是为了放货;另一类是专门将古玩送货上门的掮客,他们到此是为了搂货。
民间收藏交流的市场化,促使了海派收藏的有力发展。申城收藏的繁荣,又推动了古玩业的火红壮大,从而孕育诞生了“五马路古玩街”,即今广东路。清末,最早进入租界的古董生意人聚集于一个叫“怡园”的茶社,它地处五马路江西路口,与老城厢对应叫“北市”。到了1921年,因怡园茶社楼房不敷应用,由上海清真董事会董事长马长生等人发起,募集资金建立“中国古玩商场”,是为上海古玩商业史上最早的一家室内交易场所。到了1932年,因商场摊位拥挤,且房屋又年久失修,为拓展业务,又增设“上海古玩市场”。后两个市场合并经营,1946年成立了“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
五马路古玩街全盛时期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的古玩店铺达二百一十家左右,特别有海派特色的是,这里不仅经营着五花八门的古玩器物,还有洋人开设的中国古玩店。“史德匿古玩行”即是其中一家颇有影响的店铺。业主史德匿,于20世纪初来华就职于上海中国江海关出口古玩检查部,精于鉴定,其个人庋藏宏富,除金石书画外,古瓷尤多,以宋代定窑器而著称沪上。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冬,史氏还举办过一次个人收藏展,获得吴昌硕的赞赏。当时,史德匿经常出入于五马路古玩街,被人称为“黄胡子”。1937年,这位洋人在英租界宁波路7号开店,初名为“古迹洋行”,1937年移址于五马路口江西路上,直至1946年才退出古玩经营界。
在谈论旧上海的古玩业,不能不提及“卢吴公司”,它不仅是上海的最大古玩公司,也是我国开办最早,经营时间最长与影响最大的古玩经营机构,同时它又是北京琉璃厂的最大买主。“卢吴公司”成立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结束于1941年,由江浙财团领衔人张静江牵头,湖州的卢芹斋与上海的吴启周等人在沪创设,故称“卢吴公司”。1952年,吴启周移居美国,原“卢吴公司”遗留上海的3075件存货由吴的外甥叶叔重代为捐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现在我们能在上海博物馆大厅的文物捐赠铭刻牌上重温这件历史往事。
四、无雅无俗之尽显大雅大俗
无雅无俗是精明的上海人收藏雅俗观的特征。所谓无雅无俗,即指所有的收藏对象,只要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就不存在高低、雅俗之分,清末明初时,集邮被传统人士嗤之以鼻为小儿科时,是上海人举起了集邮的旗帜,并使之走向了民众。
在上海滩践行无雅无俗的先驱,是那些义无反顾的文化人。大家知道,名医丁福保是被誉为近代集币界的泰斗人物,其子丁惠康自幼受父亲的薰陶,同时他亦继承了父亲的收藏爱好。丁氏早在1939年春,联合刘海粟等收藏家发起“中国历史书画展”。他又致力于古陶瓷收藏,曾汇编成《华瓷》一书,收录晋至清珍瓷90件,由大收藏家叶恭绰作序。除书画、陶瓷外,他还热衷于文物收藏。某次,为收藏文物曾卖掉四十幢里弄房屋。正是这么一位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收藏家,他流传后世的收藏业绩,不是传统的“雅”藏,而是其“俗”藏。丁氏的“俗”藏是台湾高山族文化“专题”,大多为土巴溜秋的民俗器物。1948年春,丁惠康在沪上南昌路法文协会举办“台湾高山族文化展览会,”翌年10月,丁氏应北京清华大学邀请,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会后即将全部展品五百余种捐赠给国家,现存中央民族学院。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为此向他颁发奖状,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聘其为顾问。丁惠康的实践诠释了收藏品无雅无俗的内涵。
在海派收藏家的跟中,雅俗是玩出来的,“雅”藏,如是沾满铜臭味,也会俗不可耐。而“俗”藏,同样能雅玩,所谓大俗淋漓即为雅。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如海上画派巨擘任伯年收藏贺年卡,篆刻名家丁辅之收藏手杖。又如玩火花的钱化佛、朱其石、梅兰芳、胡适,他们将别人弃之远避的玩意捡起来,积少成多,堆沙成塔,玩出了别有一番情趣,“俗”藏雅玩,大俗大雅矣。如果说上述事例还不能证明海派收藏的大雅大俗观,即再举康有为例证。1898年10月19日,康离开香港去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环球流亡生活,在他“经三十国,行六十万里”的同时,留心中国流落海外的艺术品,觅得唐宋元明清各代书画数百幅以及其它文物,回国后藏于上海辛家花园寓所,后又迁至愚园路游存庐。有意思的是,这位传统文化的卫道士,随同他的大量书画文物藏品一起带回国的,还有大量的明信片。原来康氏每游一地,必购有当地景物的明信片,并在其上手书地名或作记录,以作珍藏,要知道,如此收集明信片,当时的国人是前所未闻的,而康有为玩得有滋有味,玩出大雅大俗的风度。
正因为“无雅无俗”与“大雅大俗”的风范传承,铸就了海派收藏的兼容并收、共繁共荣的优良传统,玩出了民间收藏的真谛。当“文革”结束后,上海的民间收藏再次兴起,迅速成为“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势,形成了群众性热潮,涌现出上海滩最早的一批收藏明星,也是当今全国民间收藏最早出现的群体。例如已故烟标收藏家朱大先,这位解放后曾六次被评为全国劳模的老先进,业余时间酷爱收藏中外烟标,藏品近5万枚,又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个人收藏展,引起轰动。又例如著名钟表收藏家王安坚,生前致力于古董钟表的收藏,并于1984年率先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座家庭博物馆,影响深远。再例如算具收藏家陈宝定,在收藏算具的同时,发出了创立民间收藏学的呼声,引起了国内藏界的关注。如果说,民间藏界人士是这样,那么海上文人又如何呢?文人也同样如此。请看:杜宣收藏烟斗,峻青收藏奇石,程十发收藏照相机,陈巨来收藏打火机,郑逸梅收藏名片,陆春龄收藏笛子……。这些在收藏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独特审美理念与情趣,折射出了海派收藏文化的雅俗观。
海派收藏的“人弃我藏”与标新立异,肇始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一位奇人——钱化佛。钱氏江苏常州人,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的遗作《三十年来之上海》一书记载着他的收藏活动,据郑逸梅先生说,该书撰写于1946年,原载于《新夜报》与《今报》,以此上溯三十年,亦即1916年左右。钱氏在《三十年来之上海》中的“火柴盒之集藏”一文中,开头即写:“人弃我取,这是鄙人唯一的宗旨,所以鄙人好比是个拾荒者,越是无价值的东西,越是要集藏起来,自以为寓价值于无价值之中。因为有价值和无价值,没有一定的标准,我以为有价值,便算有价值了。”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钱化佛开创了火花、烟标、请柬、戏单收藏之先河。他甚至收藏起报丧的讣闻与日寇的布告,可谓标新立异得出奇。钱氏居然举办过一次讣闻展览,让惊讶的世人刮目相看,展品中居然有孙中山、哈同、黄楚九、史量才等人的讣闻。
当时,敢于向世俗挑战的钱化佛,在上海滩上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一个以文人雅士为核心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大名鼎鼎的国学巨擘胡适之与京剧大师梅兰芳,均喜爱收藏火花。当年梅大师出访日本与苏联时,还为钱化佛带回了大量的异国火花盒贴。有“补白大王”之称的郑逸梅先生,也是一位标新立异的收藏家,他在《我之“博爱”》的文章中写道:“名片也是我收藏品之一。”冯孙眉先生也是民国时期上海滩收藏香烟牌子的风云人物,他还在宁波同乡会所办的宁波公报任《卷烟画片》专栏主编,介绍香烟牌子知识,推广他的收藏经验。跻身于这种人弃我藏与标新立异的行列中的人,还有作家周瘦鹃、画家朱其石,甚至象沈钧儒这样的“七君子”人物,亦有此奇癖,津津乐道于山野荒漠上的顽石。
其实,在上海滩早在钱化佛前,就有人痴迷于标新立异的收藏,此人便是清代海上画派的巨匠任伯年。他喜爱搜集贺年卡。贺年卡,又称飞贴、拜年贴,在任伯年生活的那个时代,贺年卡是不入收藏行列的,但这位画坛大师恰偏偏爱上了它,经他收集的贺年片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总计达19000余张,其中有单片、合页、连页、书笺等式样,堪称一时之最。
任伯年、钱化佛、郑逸梅之流的收藏,换成今天的时髦词眼,即所谓的“另类收藏”。为什么历史上的“另类收藏”会发端于上海滩,并形成一种文化气候,这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
五、治学研究与著书立说
海派收藏,具有治学研究与著书立说的好传统。
丁福保,字仲祜,又字梅轩,号畴隐居士,近代著名的杏林人士,曾创办上海虹桥疗养院。同时,丁氏又是一位名垂青史的大名鼎鼎的海派收藏家,在古籍、钱币与甲骨上,多有建树,其中尤以钱币收藏最为杰出,民国时被古泉界尊为领袖人物。1936年2月23日,中国古泉学会在上海成立,丁被推为会长。此公非常注重治学与研究,经多年的努力,他将自己收藏的古钱及大量的古泉史料,选出六千余枚拓片,按辞典编序篡编了一部《古钱大辞典》。开创了民间钱币收藏的新领域,这是一部公认的集币界必备的工具书,至今仍具有它的权威性。与丁福保有同工同曲之美谈的,是沪上另一位邮票大藏家马任全,马公1956年捐献国家“红印花加盖小字一元旧票”,至今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马氏上世纪30年代始集邮,被公认为国邮的权威,得赖于他1947年出版的《马氏国邮图鉴》,这是中国邮票最早最具权威的工具书。
陈梦家,这位与罗振玉为同乡又与汪庆正为好友的海派收藏家,原是一员新月派诗人,师从诗人徐志摩,其16岁时,即以一首《一朵野花》之诗,名噪文坛。后来,陈氏转攻古文学,同时又迷上了明代家具的收藏。1985年,当代家具研究泰斗王世襄著录的《明式家具珍赏》在香港出版,其中有38幅彩版,就是陈梦家的旧藏。解放初期,陈氏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以后,由于其在文物研究上的成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工作环境的变化,使他的著书立说走上了“井喷”程度,1954年完成了洋洋70余万言的《殷墟卜辞综述》,紧接着完成了另一部巨著《西周铜器断代》。1956年,陈氏又汇编了《中国铜器综录》。原来会更有作为的陈梦家,遇到了多难的1957年。陈梦家的成就在海派收藏史上,并非孤例。现在,文博考古界都公认郭沫若为当代甲骨学的权威人士之一。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奠定郭氏甲骨学权威地位的扛鼎之作《殷契萃编》,其成功来自于一位海派大藏家,此人便是上海小校经阁主人刘晦之。刘氏以藏书闻名,他不仅重收藏,更注重研究和著述。但作为一位收藏家,更难能可贵的是,1936年时,刘获知东渡日本的郭沫若研究甲骨缺乏资料而痛苦不堪时,刘晦之毅然将自己整理编撰的20册《书契丛编》,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到日本,转交给郭沫若。刘氏在谱写中国当代文博一段佳话的同时,也折射出海派藏家的学识风度。
当代的海派收藏,继承了治学研究与著书立说的好传统,并演绎出新的篇章。自上世纪80年代海派收藏再次崛起时,一大批海派收藏家,在收藏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灿若群星的收藏、著作群体,在国内收藏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家文物局等单位举行的“20世纪具有影响的100本图书”选目中,有一本《中国收藏与鉴赏》,该书1993年10月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当代收藏的第一部大型图书,该书就是由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与海派收藏家合作的结晶,这本大型图书见证了当代海派收藏著书立说的风貌。
(作者为上海市收藏协会会长)
责任编辑 秦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