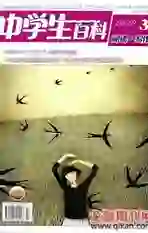你看,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2009-04-08张静
张 静
7岁以前,我几乎就是一个被父母“囚禁”的孩子。我说话结巴,走路也不利索。父母带我去了很多医院检查,都没有查到原因。我的口舌不存在任何毛病,双腿没有缺陷,大脑也是正常的。然而,这么不幸的事情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7岁那年,在上学的路上,调皮的程远飞扯了我的辫子,然后做个鬼脸,迅速地跑开。着急心切的我,撒腿就奋起直追,嘴里的呼喊声居然也是一气呵成:你给我站住……遇见程远飞的这个9月,很奇怪地,我说话不结巴了,双腿也利索了。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件传奇的事情,一直在我的亲戚之间传播。
从小学到初中,程远飞时常敲着我的脑袋要挟我:罗小柏同学,你要记得,我的出现换来您老人家健全的四肢、聪明的头脑、巧舌如簧的口才。该怎么报答,您自己看着办。对于程远飞这样厚脸皮的男生,我总是不耐烦地擂他一拳:怎么着,再跟我废话,下次月考甭想我帮你辅导功课,你就抱个不及格去跟阿姨交代吧。
我罗小柏,早就不是7岁时的那个罗小柏了。我没有上过幼儿园,可是我学东西很认真,也很快。从小学到初中,我成绩优异,爱好广泛,写得一手好字,是老师的得意门生、父母的心肝宝贝。我现在的生活与7岁时的有着天壤之别。
16岁,程远飞又和我同时考上一中。我们之间的不同在于,我是以全区第一的身份考入这所高中的,而程远飞差两分,父母借两万块钱帮他“要到”一个名额。我与程远飞的差距,就这样拉开。他小心翼翼地穿梭在校园里,我则在压力繁重中混得如鱼得水。偶尔碰到程远飞,总是能看到他尴尬的笑脸和小心翼翼的眼神。
进入高中,开始住宿生活,青春期的叛逆开始发作。特别是想起以前来自父母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心里就特别难受,特别想要自由自在地做一回自己。父母打电话过来,我要么不接,要么接了也是声音冰冷地嗯哦两声便匆匆挂断。他们会焦急地来学校看我。我的表情冷漠,话语不多。他们越忧伤,我越觉得快乐。
再然后,我做了更出格的事情,那就是跟一个学美术的“校草”打得火热。我会旷课陪他去写生,去看电影,在老师面前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偶尔碰到程远飞,他总是背着大画板,手里提着颜料箱,低着头在校园穿梭,神情落寞。“校草”笑着说:那个呆子,也想要学画画呢,现在正在学最基础的东西,话不多,跟个傻子似的。我擂了他一拳,不满地说:什么傻子?他是我哥儿们。话刚说完,我就觉得心里有点堵。
我与“校草”的故事,因为一次偷盗事件而结束。那个寒冬,他因为在超市偷窃一个钱包而轰动了全校,同时被连累的还有我。各种各样的眼神向我涌来,有嘲讽,有幸灾乐祸,还有闪躲。所有人都以为我和他是一丘之貉。我愈发变得孤单。“校草”选择转学一走了之,剩下我一个人独自承受风雨流言。
程远飞开始频繁地来找我。他苦口婆心的安慰,却换来我的破口大骂。我看着面前这个高瘦的男生,突然觉得伤感。从小学到初中,我们曾经那么熟悉,而现在,对于我的数落,他低着头不敢再说一句话,亦不敢像从前那样扯着我的头发开着无聊的玩笑。突然地,我蹲在地上,泪流满面。程远飞小心翼翼地说:罗小柏,我知道我文化成绩差,但是我很努力地学习绘画,走艺术特长生的路,就是为了能和你考一个大学,我可以读艺术系的。他说:罗小柏,如果你不上学,那我也就不上了。
因为考同一所大学的梦想,我从梦里醒了过来,重又开始努力学习。而程远飞在绘画上的天赋也逐渐显露,画功有了很大的进展。后来,他参加了几所大学的艺术考试,都过了。我们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近。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因为文化课的成绩并不理想,程远飞终究没有考入我报考的学校。我跟他说,程远飞,这样的结局也很好。他笑了笑,欲言又止,眉角间依然有着令人不解的忧郁。
18岁的末尾,我踏上南去的列车。大学的生活让我觉得单调又烦闷。程远飞的短信总是发来,抚慰远在外地的我,这让我倍感温暖。而每当我问起他在学校的情况,他总是用“很好啊”、“不错啊”之类的话搪塞。
寒假回家,在小县城的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居然是程远飞。他推着小三轮车,车里有包子、茶叶蛋、饮料。他扯着嗓子在那里喊:各种小吃,欢迎选购啊!我站在原地,只觉得浑身冰凉。脑海中浮现的,是他以前羞涩与不安的神情。现在,他完全变成了市侩的小商贩。而且,他也欺骗了我,并没有去读大学。这一切,我之前一无所知。
程远飞说,没和你考入同一所大学,我总觉得没意思……他的声音哽咽,眼神里充满了惶恐。他说,罗小柏,你看,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