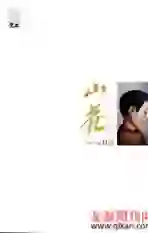画农民
2009-03-27段建伟
段建伟
我第一张表现农民的作品是1981年的毕业创作。当时很自然地选择了这个主题,是因为我有农村生活的经历,我对这些生活片断念念不忘。另一个原因是那时候接触的美术作品包括刊物介绍的外国作品也大多是表现农民的。所以我就觉得画农民是一个正题。现在看来,这张表现了一对农民父子进城的毕业创业显得幼稚,而且带有模仿的痕迹,同时也显得土气和笨拙。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之后的作品里,这种土气和笨拙一直伴随着我。我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技术的原因,而更多的是气质和选择,它也许包含了我的认识,也包含了我对观察的理解。在最初的时候,我以为可以有很多选择,但现在看来,这像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我对农民的感情,我的本分和对新鲜东西的不敏感让我只能选择画农民。我是一个有农民的情感,有农民气质的人,我来画农民,正合适。
在毕业以后的几年中,我比较零乱地画过一些画,工人、家民、藏族妇女什么的,都画过几张。在表现手法上,也是一会儿古典,一会儿表现,这和大部分同样年龄的同行差不多,感兴趣的东西很多,无论题材还是手法,随心所欲地变化着。1985年前后,我认识了段正渠,一个同样有着农民气质的画家,我一直被他的才情和气质所吸引。我们一起下乡画画,一起喝酒打牌,一些想法和看法也不谋而合,于是,我们开始合计着在中央美术学院画廊办画展的寧。这时候的思路似乎慢慢清晰起来,不再敢随意地画自己看到的一切,想让自己受到一些限制,让自己画更熟悉、更感兴趣,画起来也更有感觉的农民。1991年,我和段正渠的两人画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画廊举办,我拿出了十七张画,全部表现的是农民。我没有想到的是,画展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一些老师也给予我们充分的肯定。这对于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更加坚定了我画农民的这种想法。在以后的作品中,我一直是通过画农民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一些想法也慢慢顽固起来,我也逐渐在其中找到了一点自信,并在这种局限中找到了更大的自由,从农民身上也找到了越来越多我要画的东西,在这几十年中,我逐渐看到了自己的局限和不足,也看到了自己的所长,让我明白了自己能够做什么,怎样才能一点一点地把它做好。
我小时候随父母住在河南中部的许昌市,离老家莲花池一百五十里地。有一天早晨,二十来岁的叔叔竟然赶了一夜的路,在我没睡醒的时候来到我家。这是一件“大事”,让我惊奇和兴奋。之后,我常常被接到老家和爷爷奶奶叔叔一起生活。
叔叔和他的朋友们常常会带来一只他们掏的麻雀,麻雀的腿被拴上绳子,在我的控制下飞来飞去,有时候他们会带来几只大河虾,把虾放在火塘里烤一会儿,就会变成又黑又红的颜色。夜里,叔叔他们经常抽着纸烟,在煤油灯下聊天、说笑。冬天的时候,他们会在屋子中间拢上一堆柴火,围羞烤火;柴火快燃尽的时候,在火堆里放进几个红薯,慢慢地红薯的香气就会弥漫整个屋子:火光跳跃着,把每个人的脸都映照得红彤彤的,我就挤在他们中间,暖暖和和地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一群奔跑着的孩子引起一阵狗的狂叫,它们显然被孩子们的热情所感染,也跟在孩子们身后奔跑起来,这是一种毫无目的的奔跑游戏,它的用意可能大一点的孩子心里隐约存在;在他们中间,我也尽情地跑着,也跟着喊叫,激动得满脸通红。
多少年后,在某一种场合,也许是一条狭长的村路上,也许是村子的一个拐角处,我总会和一些人不期而遇,他们那样的脸庞,那样的神情,一下子就打动了我。我就像被击中了一样,陷入一种混乱的思想中,记忆中的东西慢慢复活。这种记忆和现实的混合成了我画中的形象。那种特定的的场景和擦肩而过的眼神,像是某种暗示,让我沉浸在一种熟悉的状态中。于是,我在画中画出了一个神情,想表现那个遇到的神情,但它出现在画面上时,已经成为另外一种东西,我无法复原那种神情。这让我郁闷,同时也促使我一张接一张地画下去。在另外一个地方,又一个神情出现了,一个少年一步一步地走近又消失。但它存进了我的记忆里,和记忆中的另外一个形象融合,变得模糊,变得没有细节,我越想把他们清晰地表现在画布上,他们反而会越来越不具体,我现在再去想这个少年,他会像老电影里的梦境片断一样云里雾里起来,但当他走近的时候,就又像是我小时候在农村认识的某一个小伙伴了。
少年时期的农村生活经历影响了我的半辈子。农村生活给了我滋养,也让我形成了顽固的习惯,在以后的生活中我没有多少改变。在很多时候,我都会不知不觉地露出我的农民天性,它影响了我的为人也影响了我的绘画。和村子里小伙伴们在一起的片断,在记忆中常常被放大,改变,他们的脸庞常常会有些模糊地在我的眼前晃动,我会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在想象中完成。在我读一本小说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和书中的人物混淆,这样,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就鲜活起来。成了一个一个很有情节的人,他们的命运也在我的想象中丰富多彩起来。但事实上,我知道,他们大都平淡地生活着,和别的农民一样下地干活儿,一样到了年龄娶老婆,生孩子,然后,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头发越来越白。
有些事件是可以具体描述的,它们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他们有更多的故事性,它们由现场的人和背景造成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吸引了我,故事性同样吸引了我。如两个人的相遇,一场争执,一次险情,一个和某种东西较上了劲的人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一个真正的事件,在我眼前摆开了一个一个舞台。小时候的阅读和对早期绘画的偏爱让我喜欢这种故事性和描述的方法,让我把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看得很重要。这种事件形成的气氛把画面中的所有东西都笼罩在里面。它给人一种隐隐的紧张感,人物关系包含了某种隐秘的让人捉摸不定的因素。它们超出了事件本身的意义,让这个小小的事件有了多元性。一个有意思的动作会带来一种不确定的东西,有点像火上浇油,让气氛更加紧张和不好捉摸,让这个事件显得更加有意思。这些动作和道具或者背景的加入,让这些事件显得不那么简单也下那么清晰了。这些事件和对事件的改变,让一张画和另一张画有了某种联系、一个事件提供给了我一个绘画的理由。
豫西是绵延的丘陵,邙山从陕西延伸过来,穿过了整个豫西,村子坐落在山坡上,房子错落有致,它们成为我大部分画中的背景。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们和我画中的人物是吻合的,但有些时候,我需要去掉更多的东西,让背景单纯起来。有时候需要强调一些东西,让它们加强画面中的气氛。有一个时期,我几乎让背景成为一个平面,像一块农村照相用的衬布一样挂在人像的背后。这样,我的人像就会像这块布前站着的人一样醒目,有时候甚至显得突兀,像要从画面上逃出来一样。人像和我之间少了一段距离,它们压在一起,远处的房子变得触手可及。有时候,需要压制一个想画一个漂亮背景的欲望,因为画里的人像是要等我给他一个更合适的背景那样站在那里,合适的背景应该是和站着的人浑然一体的。更多的时候,我觉得画出一个合适的背景是困难的,我总要在背景上反复地涂抹好多遍才肯停下来。
农村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库,一棵树,一座坡上的房子,一声呜叫,或者一个靠在墙边的农具,都给过我启示。我漫游在通往一个又一个村子的路上,和一个又一个农民擦肩而过,我领会着他们的动作和表情的含义。我走过一个只有一排房子的学校,里边传来整齐的朗读声,是我也学过的著名的童话。这童话因为朗读者的浓重的乡下口音而成了乡村童话。我听着就开心地笑了。
(此文曾收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解读意象》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