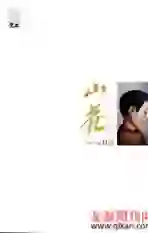建伟的画
2009-03-27何向阳
何向阳
建伟的画。属于很难诉诸于文字的那种,倒不是他画中传递的艰涩,恰恰相反,是他笔触叙说的简单。有时候,它们简单到只是一两个音符,但好像要表现的心声又已全然托出,待坐下来想细细回味与捕捉时,它们又天籁一般。无迹可求。近年,这种神秘萦绕,虽然,建伟其人,一如既往地朴素,而他画中的人物,更是一天天地与他一起做着“减法”。羚羊挂角。是一种奇异的体验,教人欲辩忘言,而且,随着对他阅读的深入,会越发觉得叙述的难度。建伟的画,对传统评论构筑着考验。你必须找到一种与之对位的视线,才能解决语言不逮的困窘。换句话讲,你必要首先进入他的语境,才有可能真正触到他的内心。
1991年,美院画廊曾办过正渠、建伟的二人展,引起不小震动。画的力量之外,原因之一还有它们携带有的一种与当事时艺术完全不同的创作风貌,距离85新潮之后不过六年,而且大多作品恰恰创作于这新潮余波的六年,这两位段姓河南画家,正处青春喜新年龄,竟能全无潮流人身的印迹,在一片形式主义的旷野中,生生种出了打上自己胎记的高粱和玉米,着实让人暗暗吃惊。正是这次展览,使两位画家一扫当时的西风流行,而以清新泥土的乡气传递着油画这种西式烘培表现出的中国味道,回望当时,他们也许并无后来评论总结出的更为清晰的意识,也不是为了反叛与清理的理念先行的创作,而是在河南——这块最深厚亦最古旧的文化土壤中浸泡得太久,从父兄到个人,从生身到前定,他们,无法不画出他们耳濡目染的风情,他们一下笔,那农民的叔叔、黄河的船夫就一跃而跳到了纸上,他们无法拒绝这种要求的表现,那亦是他们的一种内在本能,这种本色,被后来的评论放大为一种有意识的理念,并以“新乡土”画派冠名。我想。较之意识而为,两位更多是本心而动。只是他们拿出来的结果,给了众人如此的印象。这次规模并不大的画展,在他们创作中的界线意味,也是不经意中的,他们,避开了风行潮流的那个“艺术的大众”——无论是创作还是审美,而依从内心本能的指引,其结果是,他们的创作在当时有着另一种“出位”与“另类”。好像是事先谋划的“另辟蹊径”。无论如何,他们的画,展示了一种温和的勇敢,这种勇敢,就是,他们把自己从潮流里面“摘”了出来。昭示世人,还有另外一种思想,一种与坊间关于艺术的观念不同的方向。当然,一切艺术上追寻个性的画家都会或早或晚地做这样一次“减法”。十七年前。建伟四十岁,这种减法,不早不晚。
这次联袂,使建伟、正渠各获感知同时。也被画界此后以“二段”相称。当然,这个命名绝非表现手法和绘画风格的相似,而指他们拥有的理想、深入的土壤的一致。虽然这个命名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抹去了两个各人的界线,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刚刚摆脱要裹挟他们进去的艺术风尚时代激流,却不意撞上了另一冰山,一时间,乡土、农民、风俗、质朴,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词汇一股脑地盖在头顶,这样一摞帽子戴起来是很暖和的,给人以昏昏然的感觉,但是冰山坚硬,它们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里面封存凝固着纪念与文物,很多人——许多起初有个性的艺术家都乐于这样的高帽定位,它们暗含着一种艺术的至高承认,甚至是一种历史的权威证明,“新乡土”,给人的诱惑巨大而暧昧,一方面,它与历史的乡土派相联,这是正宗的、经典的、本土的、主流的一系列话语系统的创新性延续;一方面,它又于前人深耕的厚土之上赋予了一切艺术与生活的传统以前沿的、新颖的、创造的、个性的空间。这是一种承前启后的评价,而这个前后新旧的接点上,站着的正是这两个渴望开天辟地的年青人。难道,你会舍得甩了那帽子吗?现在想来,他们确实勇敢,是一种温和的方式,他们没有摘了那帽子,而是顶着帽子前行,一方面不致被那赞誉压垮和圈囿了,一方面提醒与警惕于那出于好意的赞赏后来的类型化的暗示。反类型,是他们创作的初衷,既然他们肯将自己从“类”的新潮艺术时尚中“摘”出来,必定,他们也须将自己从“类”的经典艺术历史中“摘”出来。他们果然做到了。1993年的四人展,如果说还是一部分沿着1991年的路数给予放大的话,那么,到了1996年的“中间地带”联展上,建伟、正渠都拿出了自己不同以往的画风。
不做风尚艺术家,其进一步的坚定性还在于:亦不做风俗艺术家。
两场减法做下来。那么,什么,谁,是建伟想要、想成为的?
自己。
只是自己吗?
不!
“一个荷锄者从身边走过,直直地就盯了你,远处坡上的渡槽,在坡顶形成了一个向上的突起,当我被其吸引心生敬慕和庄严的时刻,一队形神兼备的小猪直扑跟前,不由你就发笑了”。
形神兼备。是他习惯的幽默。
“在巩县鲁庄后林的一个坡道上,迎面一个吃力地推着自行车的少年的目光与我不期而遇,让我蓦然觉得这个陌生的生命和我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我的眼睛曾经被木偶戏前台的热闹所吸引,却没想到过那双诡秘灵巧的手。一些儿时生活的片断,我无法逃脱的血脉,那些特定的时刻和景致,都一下子清楚地和眼前的东西重叠起来。我重复着别人的提问:你为什么画农民。你为什么画农民。我就又一次口吃了。迎面一个农民伸出右手接过我递过去的一根烟。生命的本质几乎就写在这张脸上。它笑着,我迅速被它感染着。这种生命的活力我在别处见过,在一棵树身上,一个湿漉漉的土坡上,一两声鸣叫中,一个动作中,一句省略了的话语中,鲜活自然,直接而有力。我看重这些平淡,世俗生活中的日常景色和几乎无法辨认的表情。我快要看到那双手了,诡秘而灵巧。我被这些平淡的生活吸引。被它的捉摸不定和模糊的含意吸引。我揣摸着和领悟着。有点犹豫地向前迈了一步。我逐渐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我用这样的语汇去诉说,他们就用这样的语汇和眼神来回应我。这像是一桩秘密交易,我得到了我要的东西”。
诡秘灵巧。是他追溯的庄严。
两段引文出自建伟本人的《回望乡土》。这部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画家画语藏着建伟于交错路径中自我选择的秘密。那成画前的草图与速写单纯直接,一只手,一个拿烟的动作,一张脸,一种不易觉察的笑意,均简要明了。与溢出线条与墨碳的少许文字一起勾画着当时的心绪。这部不足100页的小册子,出版于2000年,而其中的草图多为1996年,于此推测,文字写作的时间约1996至1999年之间。那一节,真的是对乡土自己的回望了。这回望的咀嚼,当然包括对此前——1991年的乡土画作的反刍。
至少,1996年,是一个拐点。记不得是“敞开的壁炉”——河南青年油画家提名展还是“中间地带”联展,已不止四人,曹新林是策展主持人,关键不在人的众寡,而在,建伟当时参展的画,教人吃惊。河南画院展厅,一进大门,展厅左手,是两幅顶天立地的巨人,农民子弟,少年到青年的脸上平漠稚气,两幅画上各有一人。一人拿唐诗,一人拿宋词,漫卷诗书,却没有欣喜若狂的样子,或者是一人拿了一把扇子,两
个人对称地站着,像两个门神,唐诗、宋词或者可能就是扇子在各人手里也对称着,两幅画,两个人,像两个对联,一左一右。我不禁愕然,建伟的加减如此神速,但是那画中增加的因素却是我不习惯的,也很难说上喜欢,当时我只觉得是一种观念跃出了画中,破坏了由《抱玉米》《大风景》《指天》《花鞋垫》《队长》《抢救》《打狗》以及《麦客到来》建立起来的自然,犹如正在行进的田园乐曲,突然闯进来了一个不谐的音符,将整个前行的阵脚改变了。同时期,扇子好像还发展为一个“扇子系列”,教人瞳目。和谐不见了。道具的滥用让人忽而陌生。我第二次在他的画里看到了破坏。——第一次是他80年代的作品,那幅画了穿着四兜中山装的《父亲》。记得我正在那幅画下碰上也在端详那幅画的他的农民作家父亲,两个“父亲”在同一个地点,一个站在一个的前面,有一种文字难以描述的诙谐在里面,如画里的温和与反叛。然而这次,建伟通过古书与扇子这样一些传统文化符号想传达的东西,却不甚温和,它有了锋芒,它想说明的东西,也许是,你们不都当我是一个擅画农民的画家吗,我其实并不如你们想象与定位的那样,你们不都认为农民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状态吗,农民也未必如你们想象与评说的那样。这个变奏,及藏卧其中的急促与傲气,我起初不以为然。而同室展出的正渠的画却动人心魂,《英雄远去》华章一般的再现,那些荒芜的废墟、大地撕开的伤口,那些没有人作为主体的断壁残垣,却处处聚着哀伤悼念,在一个巨人留下的硕大背影面前,无由地不被它吸引,指引,以致久久不能将心平息。这是正渠的一次减法,他把人抽象了出去,已不见陕北的高亢激越,却以另一种酷烈冰凝住了他想表现的如铁意境。比较起来,建伟的转身寂寞沉静。而这一点,建伟了如指掌,此后不久,我读到了他为正渠画册写的题为《英雄远去》的前言,他娓娓道来,从容梳理,那些文字,我以为画出了正渠的灵魂。文如其人。长久以来,我思忖着建伟的改变,他变了吗?以往我们熟悉的画中人,他们变了吗?现在回眸,我把1993年的《唐诗》《宋词》和1994年的“扇子系列”视为回水。反题材,是他不甚成功但苦心可鉴的一次试验。也许,建伟只是用了加法的形式再做一次筛减,从别人也许是他自己要把他放在一种贴了标签的“箩筐”里的筛减,我不在这儿。这个“箩筐”不是我的终点。
那么,“我”在哪儿?
观摩1996年的画或可找到一把钥匙。我说过,1996年,是一个拐点。就在“扇子”的同期创作偏后。建伟很快抹去了文化符号学的“入侵”——也许更多是有意为之的“反动”,重新步入乡野。
这一次,铅华洗却。
但就是这一阶段,建伟仍然是犹豫的。一方面,他重拾1991年至1994年集中于《抱玉米》《花鞋垫》《队长》《抢救》《打狗》《麦客到来》中或隐或显的叙事性,画出了1995年《雪原》之后的《换面》《放炮》《发烧》和《亲爱的叔叔》,它们延续着自《抱玉米》《抢救》开始的农业情景,那些生根于土必将回归于土的农民,他们简单的家事生活,从打猎到庆典,从家族子裔的天伦之乐到平日生计的柴米油盐,一切都错落有致,井然有序,俨然是他记忆中或理想里的乡村。这些姑且算作文化叙事学的画,连同自1991年以来的一系列乡村景致,都带有这种梦想冥思的色彩,它们不是现实的镜子,更非生活的写实,这些乡土新吗?好像再原始不过,古往今来,他们,人,就是这样一个样子。这些乡土不是实实在在的吗?好像再真切不过,人,我们,难道不是长着与他们一样的面容,拥有着与他们一样的诚实?那么,建伟是不是回到了从前,不全是,较之《大风景》中的人,人放大了,风景变小了,人的顶天立地性在这时发挥到了极致。这还是其次,画中的人更加结实,色彩也渐渐浓郁,人的肌理感得到的强调,前所未有,在他,这是某种自信的宣谕。另一方面,他试图放下自1991年始以《花鞋垫》《抢救》等为他创作起到奠基作用也成为他艺术代表符号的人文叙事性,画出了向1994年他自己作品《红衣少年》致敬的《读书少年》《靠墙少年》《行走少年》。这一年,1996刚过,1997来临,建伟站在画布前,左右地看着他的时光与记忆,景致万物向后退去,同时,不知是谁的手将犹豫的他有力地向前推,就这样,他站在了自己前面,而那童年的“我”的面影也在时间的幕布上悄然展现。这一年,是画者于而立走向不惑路上的一个本命年。
细心的话,可以看出,《少年》系列并不孤立,他们很久地沉睡隐藏于成人后面。1993年《眉清目秀》里那个手牵大人但直视画面的小男孩,1995年《教育》里那个侧跪在拿着擀面杖要对子女实施教育的父亲面前认错的儿子,1995年《父子》里那个自豪地坐在父亲肩膀上手执纸叠的飞机把村庄远远甩在后面的男孩,他们,在成人世界中,一直做着配角的角色,一直在与成人的关系中确立着自己的位置,有时候教人觉得,一旦失去了某种承启的关系,他们会一下子坠入真空,而找不到纵横坐标中的自己。那么,建伟就是让这些未成人的“人”走上前台,他祛除了叙事,他抽掉了用以证明他们存在的坐标,他甚至到了最后将那隐隐的村落背景也涂改成了黑灰,1996年,我们还能看到一群少年走在《夜行》中的乡村路上,我们还可以凭借时间地点与环境这些画面信息猜测他们或许是在去看夜戏或是走在露天电影散后回家的路上,但是此后,这一场景越来越少,几近终止。
1996年,是他创作最具爆破也沉潜到最深海域的一年。这一年,犹如协奏曲中的两个调式,它们争夺着发出高音,又如两个音色绝佳难分伯仲的乐器,它们在争夺着演奏者的手势。一时间,建伟的画面出现了难见的胶著与矛盾,但很快,交锋之上的新的和谐到来了。他服从了。与其说,他驾驭了乐器,不如说,场景让位于生命,形象让位于性情。本能战胜了意识。1996年是一个埋在心底的界碑。这个界碑,或者就是1996年那幅《小孩》。这个小孩,已不再是情景中的配角,而站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正面,他凝视着你,表情稚拙而平静,然而那乎漠里又有一种难以祛除的决心。他的后面,是已沉入黑灰暮霭的村庄,或者山脉,已不重要,他穿着上世纪70年代儿童常穿的三个钮扣的衣裳和系带的老式鞋子,也不重要,他来自哪一个具体的省份具体的村子具体的农家,或者他本人就是一个城市的孩子,他是不是正是画者自己,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孩子,左手插兜,站在画面上,他的嘴角隐忍,那将要盛满生活的苦,他的眼睛坚定,那里已贮藏了迎对人生的信念。此后的作品,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对战场的打扫——对叙事的清理。
反叙事,也许,有得有失。
但是,画者已无法控制。
本命年后,建伟与他的童年不期相遇。这个成人,无法拒绝孩子的召唤。
十年后,2006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孩》。里面的作品近百幅。无论是中国油画创作史还是他个人创作史上,这种取材以及他执拗地要表现的东
西,都不可思议。一个画家用了创作生命最壮实的十年,只干了一件事,近百幅画,好像只在画一个小孩,这个画家不是疯了,就是受了更具疯狂力的某种指引。我深知后者的力量。
谁知道他赌的是“命”呢?
或者根本什么也不是,只是“命”教它完成的篇章。
一个艺术家,真正遇到了自己的宿命,并将它通过自己表达出来,我知其难,但我更知遇到的人无路可退。
从《大风景》到《麦客到来》到《亲爱的叔叔》再到《靠墙少年》,到《小孩》。画面上的人越来越少,背影、侧影直到正面。再到只剩了人的肖像,与之同时,建伟减去了乡土绘画的类型、农民题材的定位,直到减去了乡村母题的叙事,这样一路下来,由反类型到反题材到反叙事,他同时规避着朝他扔来的圈索和他本人已掌握娴熟的处理,以致在一个大的空间领域好像他的画没什么突变,实际上那来自内里的变化已经悄然奠基。反类型,反题材,反叙事,他一层层地脱掉了外罩、棉袄和夹袄,从成人到少年再到小孩,他又同时一层层脱掉了时间加于生命之上的毛衣、秋衣,与他以往创作的反摄影反写实以致反正常人物比例反审美习惯一起,诸多减法,已使他走到名符其实的“裸泳”境地。
小孩子画面上真切地看着他。
注目于他从繁复到单纯、从艰辛到从容的“泅渡”。
从那清澈的目光里,他似乎得到了某种鼓励。不然不会反复于画布上,篇篇针脚细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求证,又有什么力量,他几乎只在完成一个孩子的面容头像!小孩大一点,小一点,年纪上,小孩读书、朗诵、行走、伫立和冥想,小孩按照自己的法则活着,时而多思,时而沉静,那个成人无法进入的世界,有着无限的生长的可能。
后路切断。
这是一段祛魅的历程。
那来自世俗与艺术的双重诱惑。
向内掘进,他几乎以此拒绝了现世的成功。
其实,如果深入建伟创作,他的小孩并非降自空中。1996年再往前推,真正的诞生也不在《眉清目秀》与《父子》。1991年,正是他《大风景》《贵香》《春耕》同时,有一幅画不应被时间和评论湮没了,它高125,宽106,以厘米算,和横幅的《大风景》不差毫厘。然而它的方向却在另一条路。它是此后十年的深深伏笔。它的名字是《盲童》。画面上,一个孩子站立于他的村庄之上。村子、山脉只是他的一个远远的背景,他站着,正面于画面犹如正面于人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建伟第一次让小孩成为顶天立地的主角,但是站立着的这个孩子,虽然脚旁的野花与头顶的浮云,于他都不可见,然而却绝非无关,这个失明的孩子,右手拄木棍为拐,左手有着微微向前触摸的手势。他双目紧闭,两耳前后一开一合,嘴角是我们熟悉的隐忍,全身心感知着这个盛放着他的世界。无庸隐讳,这是让我流泪的一幅画。我深深地感动于画者想往传达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既非农业,也非城市,它高于它们,这些具像与物质。然而它又深深植根于它们,有着可触的实体与大地。这是世上罕见却一直存在的火。我以为,这幅画,就是建伟的心象本人。
自此再过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由“盲童”牵来的小孩可能更聪慧内敛,清健有为,但是我无法不惦念这完美的开端。
诗篇早已开始。
那发自内心的赞美。
这第一句诗。第一个字。第一次坦露的诚实。
教人想起张承志对额吉的不倦书写,他重复地将她写进《黑骏马》,《金牧场》,以致《黑山羊谣》连他自己也困惑于这样的书写,为什么,长达十年,“为什么我要一年复一年地描写一个蒙古老太婆描写了那么久那么多页纸手都写酸了心都写累了但是我还顽固地写着呢?”这种超越自我的灵的吸引正是他生命之弦断裂仍能不舍不弃追随美的法律、焦渴疲惫憔悴仍能艰忍穿越沙漠的东西,这是一种原型,一种感应,一种大地——母亲向他源源不断输送的血液,异曲同工。建伟在对小孩长达十多年的刻画,在评论家可能的误读与不解中,在对以往熟悉的技艺、题材和表现方法的牺牲与放下后,重拾陌生,重回源头,重把自己“归零”。这其中必然藏着他不能不如此做的缘由。一种在工业发展、时代变迁、技术进步中沉淀出来的高贵、宽厚、温柔、善意、单纯和坚毅。一种沉静柔弱,却又不折不挠,一种坚定忍耐,却又仁义深厚,一种天真,却有着支撑它的成熟,一种平实,却有着充盈于内的圣洁,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不可抵御的神启,是一个民族,不,是曾像“盲童”一般的人类整体穿越黑夜走到今天的最初记忆。
1999年初冬,建伟、正渠、瑞欣、王顷、唐亚、丁昆六人曾赴济南举办“6人”展,我曾为之作序。那时,建伟拿出的画已清一色的小孩,记得一幅手肘扶着山梁的小孩,教人忽而安静,是地气血脉贯通后的乎和安宁,一边是光怪陆离声响噪乱欲望高涨,一边是观念更叠思想演进潮派日新,两间一卒,建伟能够不动声色,不狂躁,不凄怨,亦不颓废,不清谈,这番定力之下的删繁就简,使他减除情节动作表情后的画。获得兼容能力,亦有消薄气派。
一切并不复杂。
神性的谜团就在我们自己里。
“我的眼睛曾经被木偶戏前台的热闹所吸引,却没想到过那双诡秘灵巧的手。”
反类型,反题材,反叙事——姑且这么说——而至的“裸泳”使他置于自由与尴尬的双重境地。——是呵,我们交换眼色,像是完成一件秘密的交易,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另一方面,也使他必须以臻于完善的严谨和能量来构筑补充他因故事、环境、背景诸多人文因素的抹去而留下的空白。
这是一片难以伪装的裸露地带。
把心剖开。在时尚变幻的今天,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异数。
画神容易画人难,画人容易画魂难。毫无修饰,绝无添加,一脸诚实的“小孩”成了他绘画的检验与考量。
1997年之后的创作,“小孩”的队伍不断壮大。然而,你会发现,除了少数孩子譬如《送菜》《杀鸡少年》《水库少年》仍然延续着原有的最少量的故事信息外,以《靠墙少年》开始的《蹲的小孩》《月光少年》以及两幅不同姿态的《飞》,均有着一种梦幻冥想的色彩。他们无所事事。保持着与年龄对称的心境,他们若有所思的神情,从某些方面又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年龄,他们像一个个哲学家那样,煞有介事,或蹲或站。或立或行,在一片空茫的世界上,一边打量,一边梦想,而夹在这两种作品之间的,是1997年的《守卫》,1998年的《持剑者》《吹号者》,2002年的两幅姿态各异的《朗诵》,以及2004年的《刻字》。画面上的人从两岁、五岁到十岁不等,他们手里握着的是他们不等年龄里的各自梦想,然而是刷了红漆的木刀——他想做一个勇士,守卫国土或者占山为王;是同样刷着红漆的木剑——他想持剑行侠,成为英雄;吹号的小孩,眼睛曳斜,尽管手中的号角是暂时的塑料玩具,他仍在企盼求证是不是自己能够胜任一个将领;还有那手持书本的默念或诵读的孩子,或为济世,或者只为做一个合格的书生。当然,还有也许什么都不想做的孩子,既不想做英雄也不想当将领。他
的梦想就是爱一个人,将她的名字深深地刻入成长的生命。在叙事与梦想之间,建伟并未彻底拒绝道具,但是他让那道具成为“无用”,成为只在预设的场景与梦境中才能实现的象征。
反功用,建伟脱掉了最后一件背心。
这里,有一幅《手指受伤》。诞生于2002年。我将之视为十一年后向1991年《盲童》致敬的作品。画面上,少年左手大拇指受伤,整个左臂被吊在脖颈系着木板的布绳上,但仍有右手揣兜的自在与从容,他一脸淡漠,满眼忧伤,而他身后的平原与村庄不见了,只是一片广漠如浪的灰色山脉,远远地,衬托着这个孩子柔弱的刚强。
这幅画中,集中了建伟早期的幽默和庄严,随着岁月的加减,他在这幅画中还郑重植入了疼惜与神性。或者这么说,是疼惜与神性自己长在了他的画中。
由民走向人,由人走向“我”,民和人都包容在“我”里。将“神”请到人间。用心传递日常生活中的神性。也许所有的磨练,都为迎接这一刻的降临。这时的画,梦幻幽冥,宏广神秘,优雅而宁馨,充满自然的暗示与隐喻,又同时深具神性的平实与率真。这时的画者,已不属于任何一派,他深居无法定义与命名的地段,他跳脱于史、论之外,他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站在画面上。
是一个孩子的形象。
温柔敦厚。圆通自足。
也许。他想通过这个孩子,来验证自己的童心。那通向深广人性的真正启程。
这可能正是他的画,虽不宏大,却有着慑人的力量。
也许,他想通过一群孩子,来考量人间的耐心。日常生活中的神性就隐藏在这最柔弱亦最刚强的眼神与手势的微妙传递中。
这可能正是他的画,始终做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也许,他想通过孩子,对自己的人生做一清理。那包括生命自我的一种艺术达成。
这可能正是他的画,有着羔羊的品质。我想说的是,他试图回复与返归某种生命中幽冥的本能,不独只是画面人物脸部表情呈现的动物性。
动物性?是呵,也许我们所从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阴沉的卓越
像是天堂
“我快要看到那双手了”。
没有事件,没有哲理,没有指向,没有秩序、必然与规律,没有范畴、节次与等级,它只是一种或然,像生命原来不被涂抹的样子。在生命面前,事件、哲理、秩序都会暗淡,因为生命是一种或然,它超出规律,越过等级,甚至否定必然,我们关于人生及与之相关的任何成型的理论,梳理。已知与结论,比起生命而言,都是暂时,都是截断,支言片语,只有生命本身,它依照着自己的节奏,向前递进。只有或然,永恒于我们的所能找到的一切表达的语言。
万物有灵。只是我们羞于承认。
建伟平视着他们,如尊重掂量着自己的内心。
全新的圣洁
平凡的光
而且陌生
自我乡愁的眼中
这时的乡愁,已经跨越了河南,中原,农民,乡村,跨越了地域与具像的疆土,向无边的内心延展。
这时的画面,已经路过了墨西哥、法国、意大利,路过了卢梭、弗朗西斯卡、乔托,诸多民间与大师伫立着的不同地段,有着更为深广的神性。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听从内在的指令,只有心要到达的地方,值得我们拋却一切,奋然前行。
“我揣摸着和领悟着,有点犹豫地向前迈了一步。我逐渐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万籁俱寂。四野肃穆。
久长与广静的平原。
一个孩子站立于他的村庄之上,山脉只是他的一个远景。他双目紧闭,两耳开合,左手微微触摸向前,嘴角是茹苦的隐忍,表情喜悦而新鲜,全身心感知着这个对他开放的世界。
那颗赤子之心,是他向这世界郑重交付的礼物。
他站着,不发一言。正面于人生犹如正面于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