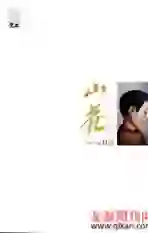探险与冒险
2009-03-27崔庆蕾吴义勤
崔庆蕾 吴义勤
在70后小说家中,来自河北的李浩给我一种很独特的印象。与70后人整体意义上的时尚、夸张、另类、极端、张扬甚至华丽相比,李浩似乎显得过于平实和本分了,他的长相忠厚而粗犷,言谈木讷,表情羞涩,对于人生和文学都显得低调。尽管曾在北京文学界漂过多年,但在感觉里他始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乡下人”:默默无闻,埋头耕耘,谨小慎微,不仅不自信,甚至还处处表现出一种自卑。
但这显然不是真实的李浩,它不过是小说之外的李浩给人的一种假象。在小说中的李浩是坚硬、执着而崛起的,他的小说有着一种自信凌人的气势、有着独具一格的自信与追求。他似乎以一种不与别人和解的偏执的姿态走在他自己营造的文学梦幻之国里。他醉心于对人性丰富与复杂的发掘、对人心之幽深微妙的甚勘探、对人之存在可能性的寻找与发现。他是一个在小说世界里充满探险精神的作家,他乐于把小说当作一种精神、思想与艺术的探险,在探险中拓展小说的宽度与深度,在探险中创造包蕴深广的小说话语空间,也在探险中完成自我的解放与救赎。
然而,探险与冒险又是相伴相生的。李浩对理想小说的艺术探险是卓有成效且值得肯定的。但探险是在艺术边界内的探险,探险需要敏锐的意识和时刻反省的自觉,否则突破了某种边界,探险就会成为冒险,因为对于某种艺术的探索一旦陷于偏执与极端,也许就会走到艺术的反面,从而成为自己的局限。
一、丰富而多义“世界”的建构
谈及创作,李浩有这样的话:“或者鼹鼠,或者飞鸟,或者……我的意思是,在一个有责任感和敬畏心的写作者那里,他可以像鼹鼠那样专注于人类存在之谜、人类存在的可能性和人性隐秘的发掘,可以像飞鸟,呈现飞翔的轻质,提升人类对世界、对过去和未来的想象。他也可以像别的什么,他可以是鼹鼠与飞鸟之间的中间状态,他也可以同时兼具鼹鼠和飞鸟的双重……”
这是李浩对于一种小说理想的描述,他追求的是小说意蕴的丰富性与多义性,梦想的是一种既在现实之上,又能让思维自由飞翔的审美空间。与此对应,李浩小说的叙事视角是多元变幻的和叙事主题和审美内涵则是异彩纷呈的。
(一)“另类”的文革叙事
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文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占据了文学创作的舞台,它或成为文学叙事的背景,或成为文学叙事的对象。“文革”叙事的热潮自“伤痕文学”开始,一直贯穿了当代文学的几次大的文学思潮,成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母题。李浩作为“70后作家”队伍中的一员,“文革”在他们的生命记忆中相当模糊,也有人曾据此宣称70后是“没有历史”的“无根”的一代,是患有历史失语症的一代。然而,李浩对“文革”叙事的情有独钟则有力地证明了这种认识的武断。然而。“文革”对于李浩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小说题材,不再是一个庞大的抽象的话题,而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感性内涵和无尽审美可能的艺术领地。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赋予了“文革”以审美的“另类”的形象。
李浩的小说大都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以一种直观的体验传达给读者,他擅于通过一个儿童、少年的视角来审视文革岁月,并以一种儿童化的生命体验展现“文革”留给人们的灰色记忆,这种记忆由于作者的第一人称叙事带给读者近距离的心理冲击,闪亮又晦涩。
“我的叙述从一个黄昏开始,一个秋天的黄昏……”
——《如归旅店的叙事》
“在一个很早很早的早晨,我的父亲丢失了……”
——《蹲在鸡舍里的父亲》
“我父亲是个结巴,如果他问你……”
——《英雄的挽歌》
儿童化叙事视角的选择使李浩的小说成功摆脱了意识形态化的可能,由一种历史化的叙述变成一种个人化的生命体验,从而使“文革”叙事这一并不新鲜的母题有了多种书写可能性与宽广的想象空间。李浩的主要目的不是借助小说来展现那段岁月的历史沧桑,而是着力于刻绘那段荒诞岁月带给人们的生命体验以及发掘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人性的隐秘。《旧时代》中可笑的消灭行动、父亲不经意间因为一次拉肚子而带来的烦恼以及“一把斧子引发的血案”,种种日常化的生活事件放在“文革”时代却引发出各种不同的问题,历史环境的特殊性使这些事件蒙上了特殊的色彩,而这种色彩经由一个儿童视角来展现则充满了诡异性和荒诞性,历史的崇高被解构,生活的真相被还原。《我们的合唱》则是从一个“社会主义红苗苗”的角度来叙述一个合唱比赛的故事,作为“红星合唱团”的成员,“我”亲身参与了那些充满了革命热情的活动,并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其中。《英雄的挽歌》中,“我”见证了父亲在“文革”大潮下悲哀的生活。在这些小说中,李浩都将叙事视角放在了一个儿童(或少年)身上,这使得李浩的叙事充满了一种童稚化的气息,原有的因历史积淀带来的厚重感一扫而空,代之以清亮的生活本色,如“我们一家人”这样的小人物在文革大潮中的命运起伏和生命体验终于在宏大叙事的历史帷幕下“破茧而出”。
与此同时,李浩的“文革叙事”中,始终矗立着一个父亲的形象。李浩的这类作品几乎都是围绕父亲展开的。作者力图通过对父亲形象的重塑来表达他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生活的思考。李浩的父亲形象暴躁、冷漠而又卑微,深深打上了灰色的印记。《英雄的挽歌》中整日游走在乡村社会生活边缘的懦弱的父亲;《蹲在鸡舍里的父亲》中因一次意外的物理伤害而精神失常整日与鸡为伴的父亲;《那支长枪》中充满了糜烂气息终日与自杀为伴的父亲。父亲,这一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中扮演着重要伦理角色的形象在李浩笔下发生了质的变化:传统父亲所具有的那种高大、慈祥的特征一一隐去,父亲的神圣性与崇高性完全被解构,而仅仅沦为时代浪潮下的一个灰色标记,这种标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特殊年代给“父亲”这一代人留下的灰色印记。长期以来,我们的文革叙事都罩在宏大叙事的历史帷幕之下,李浩对父亲形象的重塑无疑为我们出示了反思“文革”的另外一种路径与可能。
(二)对人性隐秘的发掘
李浩小说最擅长的核心主题是对人性隐秘的发掘。李浩往往通过不动声色的描述揭示出潜藏在人性深处的善与恶,以及人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惑,引发人们对生命和自身的反思。在这方面,《碎玻璃》、《告密者札记》与《闪亮的瓦片》堪称代表。
A《碎玻璃》
就故事本身来看,《碎玻璃》很容易被看成是一篇现实主义小说;但就小说的精神内蕴而言,它其实是一篇具有深刻隐喻指涉意味的寓言。在这则寓言中,徐明,这个敢于和学校最严厉的胡老师对抗,敢于公然指陈胡老师之不对的“捣蛋大王”,这个“犯上作乱”者,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异端”,对抗权威的异端。而在异端与权威两者的对抗中,在异端的来与去之间,周围人,作为同班同学的“我们”的反应是颇耐人寻味的。
“一个转学来的学生,说‘鸟语的学生竟然敢顶撞全校最严厉的胡老师,这在我们学校造成了不大不小的震动,这绝对是一个事件。”“胡老师总爱发火。她
一发火我们教室里的光线就会暗下去,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在暗下去的光线里坐得直直的,低着头,一丝不苟。”因此,我们都希望“有个人治治她”。我们渴望出现这么一个敢于和胡老师叫板的英雄,打破课堂上几乎冰冻的空气,让轻松自在回归我们的生活。可是,真有这么一个英雄出现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和英雄站在一起。当愤怒的胡老师宣布了一条命令:“我们要把那些不听话的同学孤立起来,直到他改掉坏毛病,永不再犯为止”时,虽然我们认为徐明很可怜,可是,慑于胡老师的权威,我们敢做的就是乖乖地听胡老师的话,不和徐明说话。放学了,敢于和胡老师“叫板”的英雄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教室里,没有任何一个同学来安慰他。鲁迅先生说,沉默,有时也就是帮凶。面对“异端者”徐明,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帮凶。
在砸玻璃侦破案中,所有人,和胡老师的想法一样,认为肯定是徐明所为,因而,当徐明没有在胡老师的威胁恐吓之下站起来承认时,我们都愤怒了。“说实话平日里我们最怕胡老师在面前出现了,可那天胡老师不出现我们又觉得缺少了些什么——是谁打的玻璃?你马上去向胡老师认错去!胡老师为了我们……她容易吗,你还有没有良心?”——我们集体性地失去了思辨的能力:我们不去想想玻璃之被打破的种种可能性,不假思索地认为肯定是徐明——既然胡老师认为是徐明所为。我们习惯了胡老师的“发火”,习惯了活在“空气变少,阳光变暗”的高压氛围里,一旦环境宽松下来,我们还不适应呢。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这么被胡老师的威压“体制化”的一群。我们习惯了被管制,习惯了做奴隶。不思考不质疑只服从的奴隶。——由此,李浩的叙写直承鲁迅先生与胡风先生对国民“奴性”的思考。当胡老师终于出现在教室里时,我们这些惯于做奴隶的人及时地表现自己的“体贴”:我们跟着班长孙娟,三三两两地站起来,说:胡老师您回去休息吧。——内心里憎恨着严厉如法西斯的胡老师,可当这“法西斯”来到时,我们却又争着逢迎。害怕做奴隶而不得吗?只求作稳奴隶的一群!——或许,小说写至此节,新时代新青年李浩心中升腾起的也许正是旧时代的先知鲁迅先生的这份千古感慨,
徐明,是作为一个异端形象在文本中来而又去的:一个城里的“外来者”,一个敢于对抗我们乡下的既定文化秩序(胡老师是其代表)的“异端”;而我们,则是被既定文化秩序规约、驯顺的“良民”。校长、胡老师对徐明的孤立、驱逐,即是权力阶层对“异端者”的迫害与驱逐,对自由独立的压制与打击。由此,小说结尾,即将离去的孤独的英雄徐明同学对着教室玻璃投出那块藏在书包里的砖头这一动作也就具有了深刻的隐喻意味:是唯一的异端向从校长到老师到学生这集体的愚昧、无知、野蛮的愤怒一击。或者,来自城里的徐明可以看作是现代、民主、自由、平等的象征;胡老师是旧式专制文化秩序的代表,而我们则是被这种专制文化钳制压抑的受害者与牺牲者。再或者,徐明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现代启蒙者,他要启蒙的是我们这些愚昧无知不懂独立不争自由不懂何为人本何为艺术的奴隶。不会思考不会质疑只会服从的奴隶。而徐明之被迫再度转学离去,证明了启蒙者努力的无效,正如夏瑜的牺牲仅仅成为愚昧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寓言化的书写,使一个司空见惯的校园故事翻新出奇富含深意,成就了李浩这则经典的“现实寓言”。
B《告密者札记》
“告密者”是一个充满了“前理解”的词语,作为一部小说标题肯定具有冒险的意味。搞不好,很可能会遭遇李安先生的遭遇——影片《色戒》上映后,被一些老先生斥为“为汉奸翻案”——李浩很可能被斥为“为告密者翻案”。然而,作家的功力往往体现于:于悬崖处创造风景。就告密者西吉斯蒙德,马库斯这个人物而言,李浩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人性的丰富与复杂;一是处于特定历史境遇中的人选择的艰难。
a人性的丰富与复杂
西吉斯蒙德,马库斯在事实上的确充当过告密者这一角色,但事情绝非这么简单明了,在告密者这一角色之外,他还有着多重角色:他是诗人,他的诗歌充满了对存在之残缺与破碎的疼痛体验与悲悼情怀(我们人究竟为何物?一幢痛苦的房子。——《腹泻或者无题》);他是小说家,他的以《封在果壳里的国王》为题的两篇小说以童话般的轻盈形式诠释了“面对浩渺宇宙人之渺小”的沉重的存在真相;他是贪婪的阅读者,瓦格纳、歌德、尼釆、叔本华、弗洛伊德、黑格尔、雨果他都感兴趣,《漂泊的荷兰人》、《浮士德》、《悲剧的诞生》、《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精神分析与无意识》、《美学》、《悲惨世界》与《九三年》《笑面人》他都有涉猎。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确充当过告密者,但我们不能忘了,他也充当过犹太人的秘密拯救者;并且关键的是,担当这两个从道德角度来说极其对立的角色都是出于他内心的真诚追求,而不是源于外在的“功名利禄”的诱惑。
李浩将告密者西吉斯蒙德,马库斯悬置在道德领域之外:作者没有给人物一个先在的道德评判,而是试图展现一个人物可能的真实形貌,外在的与内在的,表现出来的与隐而未见的。李浩悬置对“告密者”先在的道德评判,而执念于对人性之丰富与复杂的呈现,米兰,昆德拉说,“创造一个道德审判被悬置的想象领域,是一项巨大的伟绩:那里,唯有小说人物才能茁壮成长,要知道,一个个人物个性的构思孕育并不是按照某种作为善或恶的样板,或者作为客观规律的代表的先已存在的真理,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建立在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之上的一个个自治的个体。”
b处于特定历史境遇中的人选择的艰难
当初,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为何选择了告密?这是创造“告密者”这一人物的小说作者无法绕过的问题;而以何种方式去揭示这个谜,则关乎谜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揭示。这里,我们看到,李浩同样悬置了先在的道德判断,而试图通过多种方式(主人公的身世,父母亲的影响;主人公的小说、诗歌、阅读等等)去探寻曾经充当过告密者的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心灵运行轨迹,去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米兰,昆德拉说。人是在迷雾中前进的。“他们既不知道历史的意义和它的未来进程,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客观意义(以种种所作所为,他们“无意识地”参加到事件中,同时又“不明白它们的意义”),他们在生活中前进就像前进在迷雾中。
西吉斯蒙德·马库斯对“告密者”这一角色的选择。正是“迷雾中”的一次行走;然而,当流血事件发生时,当犹太人被杀害的尸首悬于街头示众之时,西吉斯蒙德,马库斯认识到这一“雾中行走”方向之错误。人是在迷雾中前进的,当西吉斯蒙德,马库斯回过头去看自己的告密行为时,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心痛;于是,掉转方向,加入秘密组织。成为犹太人的拯救者,就成为曾经的“告密者”逻辑顺畅的选择。
“我设想,在爱民族和爱国家之间必须单向选择的时候,他要倾向于哪儿?这里面会不会受其他因素
影响而发生改变?在社会理想和艺术理想之间必须单向选择的时候,他会倾向于哪儿?……在充当告密者的时候,我相信西吉斯蒙德,马库斯是怀有一种牺牲的崇高感的,他相信自己行为的“正确”,而当杀害具体出现时他又开始对这种正确产生怀疑。他从另外的方向对自己进行着救赎,从而加入了法国的秘密组织,变成犹太人的拯救者,……
“人是在迷雾中前进的。但当他回过头来评判往昔之人时,他在他们的道路上看不到一丝浓雾。他所处的现今也即他们的遥远的未来,站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道路在他看来一片光明。一览无余。回头看,人看到了道路,他看到前进中的人们,他看到他们的错误,但迷雾不再有了。然而,所有那些人,海德格尔、马雅可夫斯基、阿拉贡、埃兹拉,庞德、高尔基、格特夫里德,贝恩、圣一琼,佩斯、季奥诺,他们都在迷雾中行走,我们不妨问一下:谁最盲目?是写了歌颂列宁的诗歌去不知列宁主义走向何处的马雅可夫斯基?还是我们这些倒退几十年去评判他却没有看到迷雾包围着他的人?
马雅可夫斯基的盲目是人类永恒生存状态的一部分。
不看到马雅可夫斯基前进道路上的迷雾,就是忘了人是什么,忘记了我们自己是什么。”
就此而言,李浩的这次写作探险无疑是成功的,他用一个虚拟的告密者形象为我们揭示了人类存在状态的尴尬性与暧昧性。作者在“悬崖”处为我们开辟了一片奇异的风景。
C《闪亮的瓦片》
《闪亮的瓦片》中从“我”的哥哥李恒手中飞出的带有玩笑式的瓦片击中了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恶之机关,此后我哥哥的一系列不幸遭遇接踵而来,潘多拉魔盒打开,恶之花便开满了整个天空。我哥哥李恒的瓦片毁了霄红的一生,霄红也用她歇斯底里的报复毁了我哥哥的一生,我的哥哥李恒在遭遇报复之后也开始了更为疯狂的报复“那天,是我哥哥李恒变成另外一个李恒的开始,是他走向罪恶、残暴和堕落的开始”。多米诺骨牌轰然倒下的瞬间,生命随即开始向着黑暗的深渊坠落。在这个因一个瓦片而起的充满了偶然性的事件之中,李浩向我们展示了仇恨的种子如何一步步茁壮成长然后又繁衍不息,在这一系列的不停报复中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偏离了正常轨道,向着毁灭的极端飞驰而去,这是一幕幕人性的悲剧,生命的偶然性决定了生命的必然性,李恒在这篇小说中或许是想告诉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深处都隐藏着一个潘多拉魔盒,我们都应该小心保存,不要触碰。
二、繁复而多元文体世界的创造
李浩不仅把小说当作了自己思想的实验场,在小说里对人性尽情解剖,对世界滔滔不绝,而且更把小说当作了文体的实验场。李浩的文体胃口很大,传统的文学体式、表现手法与现代小说技巧在他的小说中彼此融合,多元共生,营构了一个多彩多姿、热闹非凡的文体世界。
A寓言体
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文学体裁,寓言在古今中外的文学长河中都扮演着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寓言以其言简意丰的特征在众多的文学的森林中体现出其独异的风采。而寓言体小说,与寓言故事的一个相同特征是:小说的意蕴往往越出文本本身,体现出丰富的内涵。李浩想必是深谙其间妙处的,所以,在其创作中,这方面的探索为数不少,《等待莫根斯坦恩的遗产》、《三个国王和各自的疆土》、《一只叫做芭比的狗》三部作品可算是成功的案例。
《等待莫根斯坦恩的遗产》是一个寓言性质比较浓厚的文本。它很容易让你想起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及高行健的《车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社会历史语境下,“莫根斯坦恩的遗产”这个东西,与其说是真实存在的一笔遗产,不如说是一个象征的存在:希望、光明,诸如此类。而小镇人们对传说中的这份遗产的等待,也就具有了深刻的隐喻意味:对希望光明等等美好东西的期待。但耐人寻味的,不仅仅是对这份遗产的等待,更有在这等待中小镇人们的生活姿态:一方面,他们(通过政府的操作)以这笔遗产的名义,从银行中借来大笔的钱款,进行各种建设,提前享受“美好”生活(某种意义上就是提前挥霍这笔还未到手的遗产),另外还有一些建设正在计划中,只等莫根斯坦恩遗产一到就开始实施;另一方面,小镇的人们并没有积极地工作以恢复战争带给小镇的创伤、损失,而是聚在一块闲聊、打牌。小说开放式的结尾使关于“等待”的思考成为永不结束的人生命题:“愿你们能得到上帝的赐福!希望这笔驮在蜗牛背上的遗产早点到来。”/“哈。你也这么说!现在,我们都叫它驮在蜗牛背上的遗产!还是等下去吧,你说呢?”——等还是不等,对于小镇人们来说,这是一个问题;正如对于哈姆雷特来说,“生存还是死去”是一个问题,
《三个国王和各自的疆土》叙写了三个国王的人生选择与遭际。国王A为无尽的噩梦所扰,终于离开皇宫,上山当了和尚;出家之后的他江山不要美人不惜亲人不怜;但死时寺庙方丈给的评价却是:至死他也未能开悟,他不是我们佛家的人。国王B好战黩武,他的一生都在用来扩充他的疆土。“征战、掠夺、征服是他一生的兴趣所在,对此他投入了超过所有帝王的热情的精力。”国王B在征战途中患上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双腿溃烂,后来虽基本痊愈,脚趾处却无法根治,发出恶臭;肆意践踏手下败将的人格与尊严。让他们舔舐自己发出恶臭的烂脚;身为显赫的国王,却不为百姓所识;一次穿越沙漠的失败征战使国王B认识到面对浩渺宇宙人的渺小,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好战嗜杀的本性;当国王B结束三年的宫外征战生活,回到宫城,他的王位已被他的儿子占据。不再是国王的B改掉了长年以来总穿皮靴的习惯,改穿布鞋。他的烂脚奇迹般地不治而愈。国王C是国王B的阶下囚。对国王C来说,人生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他的身体日渐成长,他们的王国却日渐缩小,终于在某一天失去了他的王国,失去了他的王后,留给他的只有诗歌和自己的身体,最后,身体连同诗歌一齐丧失在国王B的手中。
三个国王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人,而他们的三种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三种人生可能性。小说探讨的,其实是生命追求与人生选择的问题。“疆土”,可以理解为人生目标或者说是人生追求。杀伐决断的权力;倾国倾城的美色;战功赫赫的声名;或是仅仅作为一个平凡生命闲看落花流水的悠游自在。——在这各色“疆土”之中,你想要哪一块,或是哪几块?生命短暂,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在可能的多个角色中,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我?哪一个才是我真正想成为的?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由此。小说某种程度上接通了西方哲学中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永恒追问。正是寓言体的运用,使看似简单的故事生发出丰富的思想意蕴。
《一只叫芭比的狗》可以说是一篇展示人性隐秘的寓言,小说借助于对一只狗的书写展示了人性深处复杂的善恶,通过人与狗这两类所谓的高级与低级动物的爱与情感的对比揭示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与阴暗性。从最初芭比成为我们家的一员,到最后芭比被我们全家抛弃,仅仅是因为芭比已经不再有最初漂亮的
“容貌”,可见我们最初的爱是建立在一个漂亮的外壳基础之上的,当这种外壳失去,我们的爱也荡然无存,尽管在芭比失踪期间,我们一家也都表示出相当的怀念,然而芭比回来之后的遭遇击碎了所有在此之前纸一样单薄的虚伪怀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芭比在历经劫难之后依然对我们一家充满留恋,“它大约是依靠嗅觉和记忆回来的”,芭比艰难地回到了我们中间,可那里已经找不到它想要的温暖。在对待芭比的恋爱问题上,我们一家也充满了残忍,如果说哥哥是一个“刽子手”,那么我们全家都是帮凶,我们一家在哥哥杀狗这件事情上的纵容使芭比最终离开。“芭比凄凄惨惨地叫着,窜出了院子。院子里剩下我哥哥和那只被打碎了眼睛的黑狗。夕阳照得院子里一片暗红。”芭比在目睹同伴的一次次死亡之后终于离开。而我们一次次目睹死亡却始终无动于衷,比照之下,人性之恶如落潮之后海滩上遗留的垃圾一样昭然。芭比对待“情感”的善良与对待主人的忠诚凸显了人类情感的“黑洞”,我们自认“高级”却在不经意间丢失了生命最初的纯真与质朴。
B讽喻体
幽默讽喻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讽刺性作品的突出特点是独特的视角与新颖的立场,在作品中作家往往没有为我们贡献新的哲学,然而他却用一种新的形式把大家熟视却无睹的一些生活内容展现出来,从而引起大家的思考和共鸣,在李浩的小说创作中,讽刺性的文学作品也时有出现。这方面,《飞过上空的天使》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在这篇小说中形形色色荒唐可笑的社会世相好比是“多米诺骨牌”,而“天使”是推倒这些骨牌的那只手;天使飞过,多米诺骨牌效应随之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形形色色的社会世相都在这个效应的推动之下粉墨登场,表演一番,很有些群魔乱舞的味道。在这里,被讽喻的社会世相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一个新闻记者的崛起,靠的不是超凡出众的才能,而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是机遇或者命运;新闻媒体之间的无聊笔战;城市交通拥挤问题;遇有问题时相关各部门的“踢皮球”(天使飞过使流言四起,市民三天三夜燃放鞭炮,导致市中心的民心河堵塞,环卫局、环监局、居委会对疏通河道的相互推诿);国民喜欢制造谣言、传播谣言的恶习;所谓的“科学”之争(“天使”的本质是什么?海市蜃楼?外星人?);信仰的缺失(“为什么那么多人认定它是天使而不是飞天?是人们对飞天的疏离和淡漠!物欲横流的今天人们疏远了它疏远了精神的家园!”);将迷信当“信仰”,当民族特色,利用死人赚取活人的钱(“至少,它是本土化的,我们应当尊重本民族传统,维护民族传统。一个不尊重自我传统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物质产品滥用商标;文化的被滥用与商品化(“A城天使节”的设置及其一系列荒唐的活动);不懂民族经典,却敢在公众场合信口开河的伪学者……所有这些“多米诺骨牌”,都因为“天使飞过”这只手的轻轻一推而呼啦啦倒将下来,消失了它们“宝相庄严”的面孔,呈现出荒唐荒谬荒诞的可笑可恨与可憎。小说结尾,作者终于抖开了神秘“天使”的包袱:上空飞过的不是天使,不是飞天,不是外星人。更非什么海市蜃楼,它不过是我的朋友的一个发明罢了。而有意味的是,在各色社会世相粉墨登场轮番表演“群魔乱舞”一番之后,我的这个发明家朋友疯掉了!——这是小说最后的也是总体的一个绝妙讽刺:发明家眩晕于各色社会世相的荒唐荒谬荒诞,终因经受不住各种刺激的折磨而神经崩溃!
试想,如果不借助“天使”这只手,“多米诺骨牌”如何来推倒,“多米诺骨牌效应”将如何产生,对社会各色荒唐荒谬世相的绝妙讽刺又如何水到渠成浑然天成地达到?(作为读者的我们都知道,A城的这些“多米诺骨牌”决非“A城”才有的。“A城”其实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或是一个代表。)“天使飞过”,让我们见识了李浩的聪慧与巧妙。
C札记体
《告密者札记》是其代表。我们看到,就札记体这一小说样式来说,《告密者札记》有着多方面的尝试,小说采用了多种写作手法,呈现出“跨文体”的味道:其中有元小说因素(作者直接向读者说出自己的构思与思考)的引入,有小说主人公创作的引入,有问卷调查(第6节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同读者商讨,询问读者希望作者如何写,以提供一个真实的、多侧面的、有内心的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引入,有书单(主人公阅读情况)的引入。而所有这些手法的运用,都是为了勾画出“一个真实的、多侧面的、有内心的西吉斯蒙德,马库斯”。客观来说,李浩的努力基本实现了自己的预定目标。札记体这似乎有些“散淡”的文体,这种故事情节不是很强的文体,其实正切合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去形塑小说主人公。小说中,告密者西吉斯蒙德,马库斯是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人:犹太人;德国公民;秘密党员;屠杀犹太人的帮凶;犹太人的秘密拯救者。告密者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绝非一个单纯的告密者,不是一个单面的、单向度的人,而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组合体,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告密者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也许就是我们自己。“懦弱和激情似乎是矛盾的,爱和恨似乎是矛盾的,理想和背叛似乎是矛盾的,悲悯和毒恶似乎是矛盾的……然而种种矛盾也许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只是轻重有差,只是在非特定的环境下并不显现而已。”在此意义上,李浩写出了人性的丰富与复杂。某种角度来说也就是世界的丰富与复杂。
三、创造的幸福与迷失
与“简单化的白蚁”作斗争,创造宽阔的、意蕴丰富的小说是李浩一向的追求。“宽阔”是李浩小说创作的灯塔,在这灯塔的指引下,李浩持之以恒地走在探寻的道路上:对人、人性、人之存在的种种可能的探索。我们欣喜地看到,不管是在小说内蕴还是小说形式方面,李浩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儿童化视角文革叙事使其成功避开了宏大历史叙事的路障,还原出一段更为纯粹的文革岁月与更为真实的文革体验;对传统父亲形象的颠覆与再造则完成了对历史的另一种反思;对人性隐秘的深度挖掘是作家对生活及人性哲学化思考的成果,这些成果以多样化的外在形式和手段得到呈示。这种对“思考人类存在的一切”的“思维小说”的追求,使李浩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片独特奇异的空间:较之一般的“描绘性小说”更为宽广、阔大的话语空间与审美空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李浩对于小说宽阔度的追求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一,李浩的“文革叙事”系列作品存在资源过度重复的情况,如《那支长枪》和《英雄的挽歌》中对于父亲被游街的情况的叙述如出一辙,雷同化的叙述大大降低了小说的美感。
其二,李浩小说对于技术和文体形式的过分关注使小说呈现出浓重的匠气,从而拉大了他的小说与生活的距离。缺乏一份生活的质感。“文革叙事”中父亲的形象始终呈现灰色,几乎让人触摸不到一点生活的气息和生命的温度,被严重隔离在了形而上的意义层面上,其他题材的小说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告密者》中对于各种文体的使用也存在明显人为雕琢的痕迹,尽管整篇小说的叙事流畅完整,但是面对细节推敲仍显得有些单薄。
其三,李浩的小说有过于强烈的“思想”欲望与形而上冲动。李浩的小说追求深刻,但某些主题开掘用力过度,表面上有深度,但主题先行、理念化或观念化的偏执却使小说艺术的原生性流失、牺牲颇多。在李浩这里,对于现代哲学的迷恋,似乎导致的是“思想大于形象”这一顽疾的复发。对于小说来说,这样的代价显然太大了。
当然,古往今来从来就没有一种文学是完美无缺的,局限有时也正是一种美。对李浩的苛责无非想表达的正是对他的一种更高的期待。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