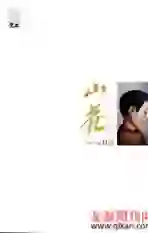种植野萱花的昨日之举(组诗)
2009-03-27韩高琦
韩高琦
那渐至黯淡的微弱之美
——引自拙诗《呼喊》
度假之夏
那年夏天的舌苔亮出一列发绿的南方火车,
它将我粗暴地卷进苏州:
外戚祖宗遗下的一栋老房子。
我以度假之名考证一桩史实。
水巷依旧,庭院幽深,
吴侬软语掩饰不了老房子的阶级结构。
我必须搞清,以免踏错门槛。
如果历史经常在修改:产权如何得以保障?
占着隔壁房间的那位主人,
显然是外姓,早先他从孤儿院出来,
如今30年纪,还打着赤膊与光棍。
一只穿绿袍的苍蝇围着他的秃头
念咒语,乌云在周边翻涌着响应。
秃头先生把收音机放在窗台,
把害着黄胆肝炎的身子
埋进竹编躺椅,松弛,再松弛,
他需要休息。
日晷的手臂正好搁在正午的焦点。
高压线的交叉投影垂直打在天井里,
收音机播放着评弹(具有明显的助睡效果)。
庭院里的一丛芭蕉,栖着一只彩蝶,
翕合的翼翅,
像一扇朱漆大门似开非开着。
——秃头的睡姿已经舒展,模糊,
仿佛浸在茶杯里的胖大海……
哦,内心的敌意缓缓消释。我转过身
深入柱头开裂的老房子——
外戚祖宗传承下来的疼痛一览无余。
壁龛里的一副玳瑁眼镜,多少有点稀奇。
透过蛛网,
透过这深渊般回声的震荡,
把一丝人文关怀的遗风保留了下来。
我们为什么活着?并且易碎?
谁又为我们传递活着的信念?
——彼此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一幕大戏。
深入老房子,我无疑像一条书虫,
寄生在本地最难读懂的一章史志里。
——纸页翻动,如烟的往事像曲折的回廊
将把我引向何方?
错纵复杂的伦理如何剖开原始密林的文句?
一条书虫,复活着旧式知识分子的精神造型。
浑然不觉中一记响雷破空而来,
太突然的钻石君临,
把秃头梦游的影子击碎在窗外——
我分明捕捉到了童年的一次呼喊。
一场天使的合唱从九重院落外的运河疾扫而来,
不一会,无视阶级结构的老房子
开始雨雾飞花:琴弦根根断裂!
一条鲥鱼挣扎着游向鳞片脱落的屋脊……
——那年夏季,我的阅读语言变得多余,
并且影响至今。
随想录
记忆浮动的十六铺码头,
息影着军舰鸟的翅膀,它从嗉囔里
吐出第一批上岸的人群:他们各怀鬼胎。
那时毒日的罂粟花开在申城上空的肺部。
像一把打开的折刀,在孩子手中闪动,
不可言说的邪念以高温方式
完成着对一座城市成长的笼罩。
而今天,一位拾级而上的导师,
晃动硕大的头颅,从日出走向日落,
简单的旅程将黄浦江的流水帐一笔勾销!
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我坐在卫星城的
一间办公楼里,揣摩一桩心事。
我与孤独交谈,直至水杯见底。
孤独是桌底下的抽屉:放着私人日记。
或者更像是一把钝刀。
——愈磨,心头就愈明亮!
现在天气晴朗,
西窗斜射进一束束葡萄藤光线,
印证遥远的旨意:难道我是不二的选择?
农业的姓氏,
城市化的生活:这蛇腰的两端左右逢源。
谁是始作俑者?30余年尘世的会战,
渐渐疲倦下来,
莫非人性中善的部分
已被吸干、蒸发,化为可怕的酸雨?
——从大上海的记忆底层。
——从竞相攀比的高楼遐想里。
向西,向西,毒日的罂粟花,
一路上焚烧蚁穴、冤魂,万物吹浪如烟。
而我又以何种方式走向归宿?
牺牲者的惨烈与彻底,
重塑警钟敲响的所指——
我能眺望到的浦江对岸金融区的巴别塔,
它的意图让天空发出隐雷的微笑。
昨日之举
点灯:种植野萱花的昨日之举。
谁操起一把药锄,带上柴门?
一位面色红润的老者?
他长寿的秘诀如何公开?——
他要点灯,照亮——
隐私中一条酣睡的虫蛆,
那与人体朽木同龄的白蚁?
点灯!让那些自我折磨的人
认清自己僵化的姿态!清晨五点,
一块顽石打露水中醒来,
醒在梦幻之豹
懒腰的一侧。
面色红润的老者,张开仙鹤的双翅,
仿佛就要羽化而登仙——
面色红润的老者,善打陈式太极拳。
他提炼,他吐纳,
70余年尘世的阶梯,让他
回首,俯瞰——
埋着坛子的旷野,退远的
有序排列的村舍,犹如一盘展开的残局。
老人不免发出呵呵的笑声……
面色红润的老者,他要登上峰顶,
让体内的红汞上升至夏天的冰点?
是他操起药锄,种植野萱花,
把灯点到隐私深处——
灯中坐着5睥前的一位少女。
(那种心跳!砰然碎裂的瓷器!)
可是。如今她又在哪里成就一位祖母的慈祥
——点灯。蝎子歌吟。
——点灯。漫山的乱石在操琴。
——漫山的乱石围着峰顶潮涌,
——点灯!种植野萱花的昨日之举。
——谁操起药锄,带上柴门?
——位面色红润的老者?
——他长寿的秘诀如何向世人公开?
汉语的巴黎时装
我不可能是那位被黑马选中的骑手,
不像他,从彼得堡到斯德歌尔摩,
流浪的一生写尽辉煌与坎坷。只剩下
一条灯芯绒长裤,
名词砂砾中几颗怀病的钻石,
黄昏的星空之语,以及
动词的篝火选举。
这位对形容词抱有偏见的理论怪人,
市场营销者。
在我的晚餐中少了他的一份牛排。
我坐在临街的窗口,饮下一杯红酒——
体内霎时泛起一阵鸟叫的春风!
城乡结合部一带应声融化,
它笛孔里的草色,吹绿健康之神的笑容!
——向生命谢罪!
——向起立的大地致敬!
然后盟誓:我将抒写高古卓绝的中国诗歌。
作为汉语传统的继承者,
又是否定者,
我要把押韵在虎豹皮毛上的绚烂杜诗
从七律的栅木囚笼中释放出来——
要给象形文字,
这古典的东方细腰,
穿上新世纪的巴黎时装!
我要给当下作践的无知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坐在临街的窗口,我踌躇满志,
向内抱紧的凝视——
我的另一份财产和骄傲:一辆萨博轿车
在过去时态的提速中,
两翼生风的形容词唰唰而过——
一下子把道路磨亮!
当它穿越城乡结合部的证券交易所,
——我的疑惑迎刃而解!
当它穿越城乡结合部的证券交易所。
就像一把软刀,
肢解了癌块上的群氓。
多么有力的提示:汉诗的魅力,
这古典的东方细腰穿上
新世纪的巴黎时装,最美
也是最尊严的一种欣赏,
首先将我征服,然后还是将我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