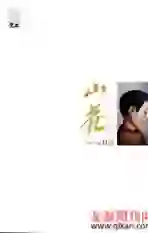圣火车站(外六首)
2009-03-27胡续冬
胡续冬
汗流浃背的土行孙,行李是一个省。
哪吒们老了,拉杆箱下可还有风火轮?
发财的跑路的吃方便面和火腿肠的肉身
都来投胎,穿制服的女娲抟气味造人。
一个字
有一天,我突然想写点什么。
我不停地点IE右上角的叉叉
像崇祯十七年攻入成都的张献忠。
以鼠标为刀,砍死了全部的
含有“强奸”、“乱伦”等关键词的
社会新闻。异常粗暴地,
我关闭了所有的下载软件:
BT、迅雷、电驴、FTP,不管那里面
有多少暉杯正在1k接1k地隆起。
我一把捏住了一首歌的喉咙,
把它摁在播放器里活活掐死。
至于msn,这倒霉的玩意儿,
噙着所有在线好友的泪水,
被我像麻风病人一样轰出了电脑。
是时候了。我打开了一个
白茫茫的word,干净得像是
天使在地狱里的履历。我激动地敲下了
第一个字,指尖还未离开键盘,却发现
那个字正一笔一画地从屏幕里
往外爬,已经爬出来的笔画
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脑袋,分明是
一只壁虎!我慌忙用手捂住word,
但还是来不及。接下来的笔画
已成为细小而有力的壁虎身躯,
带吸盘的小爪子勇猛地撑开了
我手指间的缝隙,扭动着,
试图钻出液晶。妻子赶紧帮我
扣上了笔记本,但,仅仅,
只夹住了最后一个变成了尾巴的笔画。
断了尾巴的壁虎迅速逃离了
我的书桌,我的家,不知所终。
而我,竟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到底敲下了怎样一个字。
高尔夫球场
从我住的酒店望下去,
有一片绿得发嗲的高尔夫球场,
像一个整容后的大龄二奶,
对四周威而刚的高楼吐出
要死要活的绿气:“来呀!来呀!”
于是来了一群花衣花裤花肝花肺的
资产阶级,每人拎一根
细长的资产阶级假鸡鸡,向一砣
名叫果岭的绿屁股乱挥一气。
空气咸湿得可以随时伸出一根手指,
从半空中抠出一场黏乎乎的雨。
资产阶级们玩累了球球、洞洞
和明晃晃的假鸡鸡。坐着电瓶车
逐乌云背后的财富而去。
凤凰树、鸡蛋花、木麻黄,
都被资产阶级夹在软绵绵的裆里
带回去装点咸湿的证券市场。
高尔夫球场在资产阶级的乌云下
绿得晕头转向,绿得让
果岭上的洞洞止不住地发痒。
像是一种安慰,几只
白色的大鸟降落到空荡荡的球场上,
翅膀收起的一刹那,我突然看到
一种来自撒马尔罕的凄凉。
掏耳朵
第一次给你掏耳朵的时候,
我战战兢兢地,从里面掏出了
一个鸟窝。鸟窝里的鸟都说着
我说过的废话,我羞于看见它们
唧唧歪歪地从你眼前飞过。
第二次,我掏得更深,先掏到
棉被一样厚的乌云一朵,
我沉住气,沿着云端再往里掏,
就掏出了整整一上午都躲在乌云里
下载毛片的太阳老哥。这该死的家伙
看的毛片和我看的一样猥琐,
它升到天上。向你认了个温暖的错。
你嫌金属耳勺太硌,所以第三次
我就换了一把牛角的,可以对付
更多的妖魔。天哪!这一次
我居然从你耳朵里掏出了
一岁大小的我。好像还没掏完。
一岁的我小手紧紧拉着你耳朵深处
两岁的我,两岁的我拉着更深处
三岁的我,我越掏越慌,最后
掏出了三十多个吵吵闹闹的我。
你让这三十多个我和我站在一起
排排队、吃果果,相互交流
对你的研究成果,然后又让他们手拉手
回到了你的耳蜗。我顿时理解了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掏耳朵。
阿克黄
你为我叼来魔鬼的呼噜,
我喂你吃窗外的满天大雾。
你蹲在水碗边上等候渔夫,
我给你读了两遍《硕鼠》。
你抓我,想从我身上抓出
各式各样的隐形生物。
我摇着你的脑袋,神色严肃,
拷问你到底把手表藏在了何处。
你一高兴就忘了礼数,
闯进卫生间观看人类的屁股。
我一生气就记不得你的种属,
曾经叫过你变态、狗屎和猪。
惭愧啊!我和老婆互相照顾,
却让你在手术刀下迷失了公母。
我以为你咔嚓之后只喜欢哭,
只喜欢抱着桌子腿跳钢管舞,
没想到你依然矫健如故,
从书架上掀下来一堆歧视太监的书。
你甚至还操心起太空军务,
在电脑上踩下导弹打卫星的命令符。
我教育你要爱和平、走正路,
你躲在沙发底下,喵喵呜呜。
为了请你出来散心我三顾猫庐,
结果,反被你关进了狡黠的小黑屋。
雨
旅途中,总有
不知生辰八字的细雨相随。
在机场的出口,雨就已经
混进了人群,踮起
窸窸窣窣的脚尖,盼你。
火车上,雨,又是雨
拿灰蒙蒙的小指甲
刮着车窗喊你,你就是不醒。
要等到一个空落落的傍晚
你才真正和它相遇:
雨伸出它小猫一样的舌头,
一块砖一片瓦地,为你把
整条街道舔湿,让你在空气中
闻到了小学一年级。
你把剩下的雨
从一颗冬青树上抱下来,
让它躺在你的旅店里。
你用毛巾擦去它身上
冷飕飕的风,却看见
这陌生的江南细雨
竟有一块和你一样的胎记。
里弄
内裤紧挨着腊肉、咸鱼
挂满了巷道两侧的梧桐树。
树下,菜刀男浑身是胆
在东北馆子的案板上剁碎了
四分之三个南宋。
热乎劲儿这就传开了,几条
缩在冬天的袖子里吃面的好汉,
竟被热气蒸得掏出了小灵通,
按下一行亲娘,发送成功。
右半条街有笑眯眯的屋檐,
鸭舌帽老头嚼着酱鸭舌
听他父亲从土墙缝里捎话:
台儿庄一战,死伤惨重。
可巧,小楼背后
是乳臭未干的高楼,脖子上
挂一条广告围嘴,上书SONY。哦,
SONY,SONY,谁的嘴在唆你鸡鸡?
粉灯亮处,老房子总能
温暖老生意。但更多的老生意
须得在街头放肆,比如:
大喊三百声年糕,而后把扁担
挑进吾等闯入者缓慢的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