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们讲的满洲故实
2009-03-26彰无忌
彰无忌

1948年沈阳解放,父亲被任命东北轻工业管理局计划科科长,成为“奉天满清宗室”中在新政权为“吏”的第一人。当时我家住在闹市十一纬路一幢3层楼的二楼,亲戚们闻讯投奔。满族尚往来,重礼节,极好面子,父亲将院内一溜4间车库,盘炕立灶,供老人们享用。“我家的奶奶数不清,有事没事都登门。关东烟子管个够,絮絮叨叨说不停。”大奶奶、老奶奶是我去世奶奶的姊妹,跟我们在一起。经常串门子的有大北关的依奶奶,小河沿的富奶奶,铁西的卢奶奶……我玩儿累了,就到后院找吃的。那时家境,已经没有几碟几碗了。只记得盛夏时节煮得开了花的红高粱米,拔上凉水,往碗里一捞;焦黄面面的地豆、蒸得稀烂的紫皮茄子,拌上大酱,通透码在盘里。四秩归齐摆在一张剥了漆的八仙桌上,还得说声“奶奶们请用膳”,流露出过去摆谱的遗风。吃饱了,麻利给奶奶们的烟袋锅里装烟,双手一一奉上,当然还要哈着腰一一点上。奶奶们盘腿坐在炕沿,猛吸一口,微闭着眼睛,屋里便有了片刻的沉静。这场面见多了,我就知道什么叫“运气”,因为接下来就打开了“话匣子”,而且不止一台两台。随着淡蓝色袅袅细烟在屋里缭绕弥漫,“不出门,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奶奶们,谈锋之健,忆述之清,话题之广,情绪之浓,端的是“博大精深”,给幼年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奶奶们得意时眯着双眼,将烟袋微翘着托在嘴边的神态;愤懑时二目圆睁、用烟袋咔咔咔地厾击木制炕沿的表情,虽然过去快60年了,还能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宛若昨日。
先人传说
卢奶奶祖籍吉林,深深的、弯弯的眼角,隐约着自豪的笑意——咱们的先人是仙女所生。纵横千里的长白山也叫白头山,终日积雪一片银白,满族称为布库里山。山顶有天池,像大荷叶样汪汪一碧,松花江、图门江、鸭绿江带着她的甜蜜流向四方。一年夏天,太阳光如火箭般四射,酷烈,窒塞。天上的神仙也受不了,3位仙女见长白山顶树色郁青,凉风席席,一池清澈,便飘摇而至,沐于湖中。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古伦。她们摆脱天条,在水中畅游,灵感都融化在水中。佛古伦甩一甩瀑布般青丝,往岸边走来,身上晶莹玉珠在阳光下闪烁。突然一只神鹊从山尖盘旋而下。佛古伦指着神鹊对姐姐说:“它看我们来了!”神鹊直盯着她,紧抖两下翅膀,落到佛古伦摆在青草地的长裙上,将衔在口中的一枚朱果放下,冲着佛古伦“喳、喳、喳”叫了3声,便扬天而去。佛古伦捡起朱果,见色甚鲜艳,不忍释手,遂衔于口中,拿起衣服刚一伸袖,朱果滑入腹中,一股热流,冉冉上涌。二姐见佛古伦面颊赤红,灿若朝霞,以为她受惊吓,忙召呼大姐一起返回天庭。傍晚时分,佛古伦腹痛难忍,将吞下朱果之事告诉大姐。大姐急道:“你违犯天律,受此惩罚。天上一日,地下一年,你已成正果,快去快回吧!”佛古伦返回天池边,生下一男,已是第二年的春季。佛古伦用桦树皮扎一小舟,脱下自己的衣服将婴儿包上,说道:“儿呀,你叫布库里雍顺,天生汝,令汝定乱安国,上天保佑你,去吧!”双手一送,小舟顺松花江而下。

2006年7月,我随河北省政协一位副主席赴东北考察,驱车登长白山顶,但见天池深碧莫测。清朝礼亲王永恩题碑“天女浴躬池”侧立其西南,有诗云:“树色郁青苍,兴王肇基始。”这么圣洁的天庭,别说满族,哪个民族诞生在这里都不委屈。从长白山下来,到辽宁省新宾县赫图阿拉,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先墓,也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一部分。大殿上陈列着满族史,开篇第一章为一幅水墨画,画中湖水荡漾,三长发女子沐浴其中,岸边柳枝垂晃,远山苍松郁郁,一仙鹊,尾朝上,衔一果,振翅下滑。画侧用满、汉、蒙文字标明“三仙女浴布勒瑚里泊。清朝皇帝钦定长白山天池是始祖诞生地并大事渲染,为广大满族耳熟能详。满洲始祖为仙女无孕所生,清朝历代官修史书均有记载。这实际反映了人类早期的图腾崇拜和母系社会状况以及统治者“皇权天授”的思想。
明崇祯八年(1635)十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废除女真旧称,将所属48家定名为满洲,这一天称为“颁金节”,汉译“生气勃勃的节日”。满族从此定名。其实女真最早生活在松花江下游鄂多理,即现在黑龙江省依兰县马大屯,住着达斡尔部、古斯通、斡朵怜这3个部落。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男子骁勇善射,女子育子持家。严冬围猎,冻饿兽侵,由其族斗,男丁暴损,故孩子们只知道舅舅,社会处于母系氏族状态。有时男子远行归来,驮着狍子兴冲冲地踏着薄冰,却见自家茅屋门口挂着别人的狐狸皮帽子,冻着不是自己打来的鹿肉,只好垂头丧气地向别人家走去。仙女所生的传说正是产生于这个时代。
这样的传说,在世界各民族中并不鲜见。《圣经》记载,耶路撒冷犹太贞女玛利亚,发愿奉献于天主。天主派遣天使向她预报,她要怀孕生天子,在睡梦中华光如流,祥云环绕孕育了耶稣。这华光与满族传说的朱果,表明其圣洁高尚。
老奶奶的口诵,不能等同历史,更何况祖先精心改造的神话淆乱了其种族迁徙足迹。由于清皇室钦定,无人敢撰“仙女”之外的事实。而朝鲜李氏王朝不受此制约,官修《龙冰御天歌》宫廷档案中,披露了布库里雍顺族部的形成。大元帝国曾在松花江下游地区“设官牧民”,称为斡尕里万户,胡里改万户,托温万户。万户为官名,满族祖先三大姓。这3个部落不仅受到毗邻外族如鞑靼部落和明朝、朝鲜的侵略,部落之间也互相掠杀。直到元末明初的1350—1385年,斡尕里部蒙哥家诞生了蒙哥帖木儿。
——小孩子时的帖木儿总爱拿一些鱼干、鹿肉或饽饽,分给大家。有一天他和几个小伙伴到松花江畔芦林里掏野鸭蛋,见几条平底木排贴在江面,上面几个鞑子围着小火堆喝酒。一个大胡子指手画脚地乱嚷嚷。
这几条木排来自对岸鞑靼部落,利用夜幕实施偷盗。几个孩子忍着蚊叮虫咬,望着帖木儿,等着他拿主意。3年前鞑靼人过来抢走40多头牛、20多头骆驼和玉山儿、二熊的两个姐姐。怎么办?帖木儿想了想,估计大伙强盗已经去一会儿了,部落那边没有动静,他们偷盗得逞了。对,断其后!

卢奶奶像自言自语,烟袋磕磕炕沿。我赶紧装烟、点火。
——帖木儿见木排上几个鞑子又四仰八叉打开呼噜了,便悄声命二熊回去报信,自己潜入水中游到木排边,慢慢地拔下锚砣,并连的木排顺江缓缓而下。一会儿听到人畜噪杂声,月光下,十几个鞑子牵着牛和骆驼,赶着羊群,扛着背着大包大包,向江边拥来。
来到江边,木排不见了。这伙人全都傻了眼,四下里嚷嚷着叫人找船。这时天快亮了。
突然,林子后边亮起火光,呐喊声响成一片。斡尕里部落的人赶来了。鞑子们立刻乱作一团,丢下偷抢来的东西,四散逃命。
部落首领问明情况,几个男人举起帖木儿,大声喊着:“巴图鲁!巴图鲁!”(勇士之意)被吵醒的几只鹭鸶箭一样向初升的太阳飞去。
蒙哥帖木儿长大了,成了部落的主心骨儿,三姓人都听他的。他从各部落抽一些男丁守护村落,哪家遇到困难,大事小情,帖木儿都主动相救相帮,慢慢被推为三姓的酋长。
松花江南岸,升起的炊烟成了定无居所的北岸鞑靼人的饵料。鞑靼酋长纠集6个部落袭击三姓村,在缺食少衣的春天蹚过河。 酋长叫着:“克露姓(牛崽子)那里有鹿肉!有热炕!有女人!”于是鞑靼人呐喊着,疯子一样向三姓村冲去。
蒙哥帖木儿听了从山岗上跑回来的村民的报告,眉头皱了两皱就拿定主意:来者不善,敌众我寡,只能躲避,也就是逃。逃可不是乱逃,他命各户带上要紧东西,到狼窝沟,都快把狗放出去。”木帖儿那只叫“大鹰”的白狗,像一块飘舞的白布片,率领狗群向村外冲去,迎头与鞑靼人撞在一起,搅在一起。那是一场人、马、狗的大战,都把各自的本能发挥到极致。人砍狗,马踢狗,狗咬人、扑马,马又踏人。帖木儿和三姓人站在狼窝山梁上望去,只见一团黄尘一片血,人喊、狗吠、马嘶阵阵不断传来。逐渐,一团尘血分为两团,人马向北退去,十来只狗向狼窝沟跑来。“大鹰”到帖木儿脚下,一歪倒下,脖子上往外冒血,左前腿仅连着筋,尾巴少了一截;跟着上来的几只狗,也都受了重伤,跌跌撞撞地跑到主人跟前,呜呜地叫着。帖木儿把“大鹰”抱起来,敷上刀伤药,“大鹰”挣扎着叫了一声,头慢慢垂下,再也没抬起来。那场恶仗,50多条狗为保护三姓村牺牲了,从此满洲人视狗为友,永不食狗肉。

蒙哥帖木儿率三姓女真人,溯牡丹江而上,几经辗转,移居图门江下游斡木河(含朝鲜会宁)一带,从事农耕、狩猎、放牧。
朝鲜王李成桂,称帝前长期居住在朝鲜东北境会宁、镜城一带,与邻近的女真酋长联系密切,记载了“野人”(女真人)帖木儿的若干情况。笔者推断蒙哥帖木儿应是传说中仙女所生的布库里雍顺的化身。
满族姓氏
炕上5个奶奶,4个姓氏。我的大奶奶和老奶奶汉姓关,满姓为瓜尔佳觉罗氏;富奶奶汉姓富,满姓为富察觉罗氏;卢奶奶汉姓卢,满姓钮祜禄觉罗氏;依奶奶汉姓依,满姓伊尔根觉罗氏。觉罗本女真旧姓,1213年《金史》中称松花江一带生活在山坳中野人为夹谷氏,而延续下来。为有所区别,在“觉罗”前有加居地,如西林、呼伦、穆溪、叶赫等。有加上辈名字之首的,如廊、托罗、马佳等;有加图腾的,如多尔衮(词义为獾)、固尔玛浑(兔子)、杜度(斑雀)等;有加物称的,如蒙哥帖木儿(意为银铁)等。这些特定的符号,使女真族健康繁衍。
在清朝“钦定”三仙女传说里的始祖被冠以爱新觉罗姓氏,“我国家肇兴东土,受姓自天”。其实爱新觉罗是努尔哈赤整合女真各部落之后,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定的“国姓”。“爱新”满语意思是“金子”、“第一”、“最棒”,“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
“你就是一个小爱新觉罗。”大奶奶点点我的鼻尖说。
“这么好的姓,有人还不愿意姓。真是!”富奶奶叹口气。
爱新觉罗家族从康熙皇帝才按字排辈,从“胤”字开始,各代续排,共编列14个字辈: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仿行汉族传统,把族人名字框定在经纬网络中,支辈分明,从姓名中便可看出是否属于同宗。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满族有识之士“习汉书,入汉俗,循礼法”。但也有人盲目效仿成无聊之辈。
嘉庆年间平郡王后人,爱新觉罗·图克坦小时候受惊吓,有点结巴,入家塾时先生问他:“你姓什么?”
“爱……爱……爱……”
“爱什么,问你姓什么?”
从那以后他觉得姓爱新觉罗太麻烦,不如用汉姓,读了《百家姓》后认为赵姓居百家姓之首,爱新觉罗既然至高无上,不如也姓赵,叫“赵大”多响亮!于是很得意地告诉先生,告诉同窗。
嘉庆皇帝闻听,龙颜大怒,谕旨称:“……其名图克坦,甚属尊贵,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似此者,宗人府王公等理应留心查禁,今竟不禁止。王公所司何事?恐其尚有似此等者,著交宗人府王公等查明,俱行更改,将此严禁。”
虽有谕首,但收效不大。清末民初以来,爱新觉罗氏嗣裔分衍,简单方便的汉姓由少而多,主要有金、肇、赵、罗、艾、德、洪、依、海、彰等。
1911年辛亥革命后,满族人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而伴随着“驱逐鞑虏”的口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排满、反满甚至杀满的社会行为。笔者就听有关专家学者讲述过发生在首义之地武昌的史实:革命军在桥头设卡,对每一个过往行人出示一纸条,上写“六百六十六”,命念之。本地人发音“篓伯篓斯篓”,得以放行;而原驻防武昌的八旗及其家属都说北京话,自然是京腔“六百六十六”,便被抓去砍头。当然这种行为很快被革命军政权制止,黎元洪答应出任革命军政权领导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许滥杀旗人”。但全国类似“六百六十六”的事情对满族人造成的恐慌,可想而知。于是改满姓为汉姓,多为取原满姓之一字(有的变字不变音),如爱新觉罗之艾、罗;钮祜禄之钮、卢;伊尔根觉罗之伊、依;富察之富、傅;叶赫那拉之叶、赫、那。还有谐音的,如瓜尔佳之关(瓜)等。有的取其原满姓之意或比照汉姓之意,如爱新觉罗之金(满姓之意)、赵(比照汉姓之意);瓜尔佳之关(满姓之意关隘)等。
努尔哈赤时代,授予爱新觉罗姓,有6祖以及他们22个儿子所组成的家庭。6祖即努尔哈赤的爷爷和他的亲弟兄。由于他们的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才有国家的缔建和发展,随着一套封建朝政纲常渐趋完备,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亲疏之序、尊卑之别也愈加明显。
1634年(天聪八年)继承皇位的皇太极于奉天永福宫,听户部贝勒德格雷汇报家族徭役豁免情况,一边听一边摇头。满族徭役(义务工)是天条,出马,出人,打仗,筑城等全靠徭役,谁人也不免。但随着战事扩大,负担越来越重。
皇太极就此询问军师范文程:“先生,爱新觉罗家族乃太祖所制,然所辖众而远,何以治?”
“太祖言不可变,族群不可越众而行,天下尚不平,应分而治之。皇上以孝为本,六祖与皇亲应有所别,依臣之见设宗室为尊。”范文程答道。
“好,先生请代劳。”
从此爱新觉罗分为两大支,皇太极及其父努尔哈赤、爷爷塔克世的子孙为“宗室”,系黄带为标志;其余6祖子孙仍称“觉罗”,系红带为标志。爱新姓一分为二,宗室爱新,觉罗爱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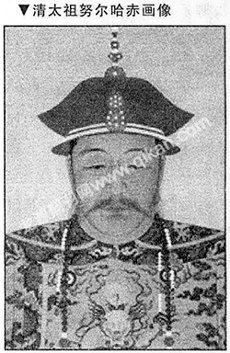
满族八旗
我揉着眼睛,哭咧咧地跑回后院:“额祖母,他们让我爬在地上,给他们当马,说我是‘骑人!”
“真是翻天了!这皇上才没几天,你是响当当的旗人,什么骑人!”众奶一词,尤其富奶奶声高,她那当家的曾为旗主。
1589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建立八旗军制。女真氏族部落时代就有八旗军制的雏形,大型狩猎时面对熊、狼、虎以及群鹿,单弓匹马不仅所获甚微,而且易受动物的伤害,有时与异部发生冲突,势单力薄就要吃亏。帖木儿规定:“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出猎开围之际,举箭一支,10人中立1总领,属9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敌”。总领称牛录额真,“牛录”汉意箭,“额真”汉意主。部族战争时常命“哈齐箭主守东门”,“呼舒箭主攻城”,于是各箭主便率自己平时狩猎弟兄们冲上去。
努尔哈赤把管辖下的女真人统一组织起来,每300丁编为1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代子2人,章京4人;300人又分4个达旦,1个章京领1个达旦。按现代编制,牛录为连长,代子副连长,章京排长。这是女真社会的基层组织,平时耕猎为民,战时则披甲征战。战马的饲养,打仗的军器,行军的干粮,皆个人顾个人,谁都准备家里最好的马,最利的兵刃,最禁饿的干粮,角螺一响,轻骑驰突,所向披靡。编制往上5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参领)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真统)1人,梅勒额真(副都统)2人。“固山”意为旗,每个固山各有特定颜色的旗。推算一固山大约8000人,最初为4旗,黄、红、蓝、白。随着队伍扩大,1615年又增设镶黄、镶蓝、镶白、镶红4旗,合为“八旗”,从此结束了女真部落无统关系的涣散的落后局面。“一国之众,八旗分隶”,全体女真人,按照牛录、甲喇、固山的层序组织起来,严格管理,统一指挥。
努尔哈赤称金国汗,也是八旗的最高领有者,他将八旗作为家族的私产,绝对领导。编4旗时,努尔哈赤自掌黄旗,由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分领蓝、白、红旗。增至八旗,努尔哈赤自领两黄旗,代善领两红旗,皇太极领正白旗,莽古尔泰领正蓝旗,褚英长子领镶白旗,舒尔哈齐次子阿敏领镶蓝旗,军事大权完全掌握在宗室手中。《八旗制度考实》记:“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旗下人为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主之分。……得些人来,必分八家共养之,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共用:战斗力役,抽甲派兵,举凡与国家有关的公共开支,由八家均出。”
牛录额真也组织生产。八旗制下的部众 “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战时征驰,平时生产,额真按需要,由章京率引牧放马匹,耕种田地,修屋盖房,打造器具等。随着战争的频繁,兵士不再弃戈务农。规定牛录下的民户“三丁抽一”,即每户如有3名男子,抽1人去作战,另2人称余丁替补,在家从事生产劳动,完成3人或3户的生活需要,“人自为兵,人自为饷,无养兵之费,故用无不给”。八旗还是掳掠财富的基本分配单位,每战后将战利品堆放8处,按八旗分配人人有份,族人自下而上渴望打仗。行军时,八固山并列,彩旗飘扬队伍齐整,若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节次不乱。军士禁止喧哗,步伐禁止杂乱。作战时披重铠甲、执利刃者为前锋,披短甲、善射者自后冲击。八旗军以骑兵为主,虽然运用皮弦木箭、短剑钩枪,射程近但以铁骑角胜,以填药的速度瞬间即至。旗规:“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敢进者为功,退缩者为罪。”一仗下来,立功者授予“巴图鲁”称号,佩红带赐宝马,挑姬选妾;胆怯者女人房子都是别人的了。因此八旗军有进无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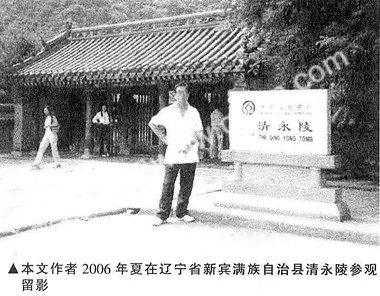
进关八旗军势如破竹,兵至良乡、昌平,牛、羊、猪、粮、人丁、妇女等源源不断抢掠回旗,运不走带不回谁抢归谁。渐渐地八旗开始互不相让,察哈尔壮丁掠回,汗王拨入两黄旗1256丁,两红旗758丁,正白旗573丁,两蓝旗612丁,平衡被打破,势力不均。1672年朝鲜国王李成桂尊明神宗旨意,助兵部尚书杨镐,领兵两万夹击满洲,大败而归,成了满洲后患。太宗皇太极即位后,令二贝勒阿敏为征韩大元帅。八旗军分建制列队义州平原,五颜六色旌旗招展,战马嘶鸣,八旗兵的脸都成了褐色,鞍架、马镫、笼头的金属部分,烫得连手也不敢去碰。义州府尹李莞领着藤排兵,一手架着用柳条编盾,一手拿着大刀,“女真野人,我等受天朝太祖册封,袁总兵必然发兵相救,尔等知趣速速退下。”府尹壮胆喊着,只听一声螺号声,在马上已经不耐烦的满兵风云而至。立刻,几百朝鲜军士身首各异。
“镶蓝入城,余者前进”。传令官挥动帅旗。镶蓝旗军冲入城中,任情杀戮,到处抢劫。随后攻破定州,兵临汉城,朝鲜国王逃到四面环水的江华岛,并遣族弟李觉携马匹、豹皮、棉绸等重礼议和。阿敏见朝鲜使臣,将礼收下道:“若要议和,总须待我入都。”同行旗主看出阿敏谋一旗之利,济尔哈朗密派甲喇额真报之太宗皇太极。阿敏下令攻城,喊杀声震天动地,鼓声如雷,两蓝军使劲儿。阿敏又令攻平山、开平,他想朝鲜都内,总还要繁华一点,趁此攻入,抢一个饱,一面打着一面将掳掠的子女、玉帛、金银、财宝运回满洲。集议日贝勒们争辩,红旗贝勒要挟道:“你若要去,只管去吧!我要率我的两红旗退回去。” 阿敏不示弱:“朝鲜岛兵,有我蓝旗就够了,要走你尽管走。”
“大同江没我红旗,你岂能过去?”
“回去有你的好,我能不分给你吗?”
“朝鲜已承认贡献,理应许和,何苦久战劳兵?宁远大军还等着我们呢。”济尔哈朗微笑道。
“你许和,我不许和。”
忽帐下来报:“圣旨到,请大帅接迎。”阿敏急令军士排好香案,率大小官员出帐跪迎。差官下马读诏,内称:“朝鲜有意求和,应即与订盟约,克日班师,毋得骚扰。”阿敏无奈,起接圣旨。召见李觉,朝鲜谢罚订约,累世进贡,世为藩属。阿敏又暗暗嘱咐亲信军队,四出抢夺,满载而归。从此贝勒各自为政,军权涣散以至于贻误战机。贝勒们只关心本旗利益,尤其在入关后,悉行圈地,东起山海关,西达太行山,八旗各显其能,冲突不断,甚至兵戎相见。八旗原本的威力,自己给消蚀了。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逝于明天启六年(1626),享年68岁。被誉为满洲第一巴图鲁,为清朝奠定基础;清入关后追认清太祖高皇帝,葬于盛京(沈阳)东石嘴山,称福陵。
努尔哈赤这一家族,称女真,称爱新觉罗,实际上一直是大明的子民,世代受封,年年得禄。六世祖蒙哥帖木儿受永乐帝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即现在牡丹江以南、朝鲜以西、吉林市开原市以东、新宾市以北一带。当地胡里改部酋长阿哈见从内斡木河迁来的吾都里部女真酋长帖木儿待人忠厚,勇力过人,向明朝举荐为指挥使,相当朝廷三品。五世祖华山受封为右都督,掌建州左卫印,很有实权。四世祖妥罗官至一品都督,执掌建州左卫,先后5次入朝受封赏。祖父觉昌安、父亲塔世克不仅继承都督之位,同时与辽东总兵李成梁互为兄弟。觉昌安、塔世克被苏克素女真酋长尼堪外兰杀害后,明万历皇帝敕书30道,马30匹,令努尔哈赤继建州一品都督,岁予银800两,蟒缎15匹,通好。
一个都督领兵推翻旧朝建新朝,历史有之。公元617年太原留守袭封唐国公李渊,趁瓦岗寨程咬金、李密等重挫宇文化及所率隋军,于扬州诛杀隋炀帝,借立帝之孙杨侑为帝,兵发长安,次年逼杨侑让位,建立唐朝李家。努尔哈赤及他的子孙,趁李自成、张献忠率农民军打败明总兵左良玉百万大军,自立顺王、楚王,攻下京城,崇祯帝以发覆面,自缢煤山寿皇亭之机,兵发北京建立清朝爱新觉罗家天下。
——努尔哈赤一生下来就比同龄孩子爱哭。其祖父老都督觉昌安听到是个小子,激动得泪流满面。走上前去提溜起婴儿的双腿,忽见右脚小脚心有7个红痦,状若北斗。觉昌安欣喜万分,早年听说书先生说:“红痦脚心生,必定坐龙廷。”
“老人家敕个姓名吧!”孩子的父亲塔克世说话了。
“嗯……就叫努尔哈赤吧!”觉昌安抬头见墙上挂着被柳条撑起的野猪皮。
“好,叫野猪皮好养活。”
满族第一个皇帝努尔哈赤,其义汉译为野猪皮。
儿时的努尔哈赤整日使刀弄棒,自称大王,率孩儿们到处奔跑。努尔哈赤10岁时,生母故,他作为长子挑起生活重担。建州仅有一些生野资源,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等全靠集市贸易。努尔哈赤就跟长辈到镇北关(今开原市)、抚顺关赶马市,带着人参、松子、榛子、蘑菇、东珠、貂皮、马皮,买回耕牛、食盐、铧子、布匹、铁锅、针线等。多年的通关、论价、交际,使他了解汉族经济情况,熟悉明朝政治动向。集市成了努尔哈赤的大学校。
1574年,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扩充地盘,抢掠军辎,伏擒明军。朝廷令辽东总兵李成梁镇压,王杲兵败逃亡。李成梁认为,左卫指挥使塔克世也不可靠,欲征之。努尔哈赤请命携礼前往李成梁军寨。
“总兵大人为何欲攻打左卫建州?”
“你们与‘右卫同宗同族,必异于朝廷。”
“大帅,您见太子河右岸徒而险,左岸缓而坦。右左截然不同,族也如此!”
李成梁觉得眼前着这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挺着人喜欢。努尔哈赤又低声说:“大帅,这次阿玛让我给您带来10斤上好山参,100颗东珠,40张紫貂皮、4张熊皮。还有两名高丽姑娘,只要大帅不进兵,随后就送上。您若进军,即使获胜,也要损失;抢掠一些东西,但绝赶上不我献给大帅的。”
李成梁想了想:“好,我服你了,可以不犯左建,但有一条,你得留在我帐上,当个书童,伺候我。”
努尔哈赤在李成梁总兵帐下一待就是5年,军中规程、排兵布阵、给养配置等烂熟于心,有时翻阅兵书,又学了不少本领,为日后统兵打下良好基础。
1583年,努尔哈赤授都督剌书,封为明朝一品龙虎将军,整军建防,主旗强民。并先后8次到北京朝贡,从谦卑到敬畏,到意得。万历二十六年(1598),40岁的努尔哈赤第四次去北京“朝贡”,带一张六龄东北虎皮、九支八叶长白山野参,虎皮是上年入京答应万历皇帝的,为这张皮死了6个弟兄。京城棋盘街闪耀着宝石似的光辉,紫禁城红墙碧瓦,朱栏玉砌,高大的明黄色的琉璃瓦屋脊像浮动的龙。万历皇帝坐在金碧辉煌的龙椅上,大殿里堆满了盆花。
“建州龙虎将军努尔哈赤为感谢皇上天恩庇护,特敬献贡品,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可曾有虎皮?”
“回皇上,六龄东北虎,狮子王头。”
“你一路辛苦了,先赐你御酒,过几天,朕还要赏你。来呀,将虎皮速送恭妃娘娘。”
努尔哈赤抬头,见龙床上的万历皇帝容貌苍老,黄胡须,小眼睛,左鬓角有拇指大一块鲜红的痣。他觉得很遗憾,暗暗地想:我与这个万历年岁相仿,他能当我为何不能?
“老汗王从京回来,从不忘祖,万历爷赐的都分给族人,到现在家里还供着御赐的蟒缎。”
“还有玉佩。”
“还有金佛。”
奶奶们七嘴八舌说起来。
责任编辑 齐玉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