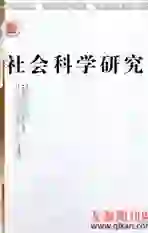古诗词“今译”作为“翻译”的质疑
2009-03-10高玉
高 玉
〔摘要〕 迄今为止,古诗词的“今译”没有一首能代替原诗,这与技术无关,根本原因在于古诗词不能“翻译”。古诗词就是它自己,就是古汉语的,翻译成任何一种语言都会从根本上改变了它。古诗词之所以不能“今译”,首先是由语言体系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其次是由文学的特点以及古诗词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古诗词中的格式、意境、多义性等都是不能“今译”的。
〔关键词〕 古诗词;今译;翻译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1-0177-07
现在见到的最早把古诗翻译成新诗的是郭沫若,早在新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确立不久,在新文学还是属于“婴儿”的时期,他就开始“今译”诗经。到1922年时,他“今译”了《诗经•国风》中的40首诗,取名《卷耳集》,并于第二年出版。但是,古诗“今译”从一开始就有争议,比如当时的梁绳炜和周士钊就对郭沫若的《卷耳集》提出了批评,认为“古书今译是走不通的路,古诗是不能译和不必译的东西”〔1〕。很多学者都是持这种观点,也一定程度上有所表述,但笔者并未见到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本文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重新论证这个问题。
(一)
为什么要“今译”?“今译”的作用和性质是什么?这是我们首先要追问的。
古诗词“今译”实际上是为了缓解或消除文学上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首先是语言上的,其次是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学观念和文学风尚上的。由于时间的变化,物事以及文化的变化,特别是古代汉语作为一种语言体系成为历史语言之后,隶属于古代汉语体系的中国古代文学对于生活在现代汉语中的人来说,已经有了理解上的障碍,特别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种语言上的障碍已经构成了影响古代文学普及、接受和欣赏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语言体系的变化,特别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文学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以及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现代人对古代文学在“文学性”方面也感到很生疏。“今译”首先就是解决语言上的障碍问题,其次是解决文学上的陌生感问题。
但我认为,古诗词是不能“今译”的。在西方,一个很普遍的观点是,诗歌是不能翻译的,我认为这个观点对于古诗“今译”同样适用。根据茅盾关于文学“翻译”的定义,把古诗词翻译成现代汉语,不可能“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也不可能“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2〕。任何“今译”都是一种强制性的解读,都会改变它,都会在意义和文学性上有所增加或减少。古诗词就是它自己,就是古汉语的,翻译成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保持其原来的意义内容。
从郭沫若翻译《诗经》到现在,已经有8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80多年的时间里,有无数的“今译”,《诗经》、楚辞、汉魏乐府诗、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今译”尤其多,笔者所见,《诗经》的“今译”就有40多种。译者中,诗人、学者均有,且不乏名家,诸如李长之、张光年、余冠英、姜亮夫、陆侃如、金开诚、陈子展、文怀沙、陶文鹏、弘征、杨光治等。但是,我们可以说,在这些“今译”中,没有一首译诗能够达到等同或替代原诗的程度,没有一首译诗能够达到上述茅盾对文学翻译的要求。这不是翻译的技术问题,而是“今译”的理论问题。
对于《诗经》,郭沫若为什么只“今译”了其中40首,他解释道:“《国风》中除了这几十首诗外,还尽有好诗;有些不能译,有些译不好的缘故,所以我便多所割爱了。”〔3〕但实际上,岂止是有些诗不能译,所有的诗都“不能译”,所有的诗都“译不好”。郭沫若的这句话有一个弦外之音,似乎这40首就译好了。但事实如何呢?我们且看一首,比如《蒹葭》,郭沫若是这样“今译”的:
我昨晚一夜没有睡觉,/清早往河边上去散步。/水边的芦草依然青青地,/
已经凝成霜了,草上的白露。//我的爱人呀,啊,/你明明是住在河那边!//
我想从上渡头去赶她,/路难走,又太远了。/我想从下渡头去赶她,/
她又好像站在河当中了——//啊!我的爱人呀,/
你毕竟只是个幻影吗?〔4〕
读完译诗,对于熟悉且能够欣赏原诗[注:原诗首章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的人来说,这简直有点像“后现代”,有点像西方文体理论中的“戏拟”。所谓“我昨晚一夜没有睡觉,清早往河边上去散步”,所谓“渡头”,所谓“幻影”,都是译者附加上去的。
也许是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我认为,《蒹葭》的艺术就在于它特殊的表达、它的意境以及给人语感和想象上的审美快乐。“在水一方”就是“在水一方”,它的艺术韵味就是从它本身生发的,而“你明明是住在河那边”就不可能生发出这种意蕴。欣赏古诗词就是在它的字、句中以及字句的组合中品味意境,始终不能脱离原诗语句,如果我们老是用现代汉语来思考,那就难得体味其中的真味。总是把外语换成汉语来思考,外语就学不好,总是用现代的语言和思想来理解古诗词,就不能真正进入古诗词,不能真正欣赏它。
对于郭沫若《诗经》的“今译”,也许我们可以说是初期的古诗词“今译”不成熟,还与他的“今译”不正宗有关系,因为他曾说,“我对于各诗的解释是很大胆的。所有一切古代的传统的解释,除略供参考之外,我是纯依我一人的直观,直接在各诗中去追求它的生命。”“我译述的方法,不是纯粹逐字逐句的直译。我译得非常自由,我也不相信译诗定要限于直译。”〔5〕这和后来的“今译”观有一定的距离。30年之后的郭沫若明显成熟了,“今译”也正统多了,但是否就避免了问题呢?我们且看他“今译”的《离骚》:
我本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号叫伯庸的是我已故的父亲。/太岁在寅的那一年的正月,/庚寅的那一天便是我的生辰。//先父看见了我有这样的生日,/他便替我取下了相应的美名。/替我取下的大名是叫着正则,/替我取下的别号是叫着灵均。〔6〕
在《离骚》中,这四句诗因为是叙述作者自己的身世、生辰、姓名,所以相对具有客观性和实在性,应该说是最容易“今译”的。但对照原诗与郭沫若的译诗,我们仍然感到译诗未必契合了原诗。“古帝”是秦以后的概念,是相对“皇帝”而言的。“古帝”是今人对“皇帝”之前的“帝”的尊称。屈原时代,还没有“皇帝”的概念,因而也没有“古帝”的概念,所以,把“帝”翻译为“皇帝”是不准确的,翻译成“古帝”,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帝”就是“帝”。“嘉名”简单地就是“好名”,未必是“美名”,正如今天我们说某人的名字“很好”,但未必意味着此人的名字就“很美”一样。屈原时代,已经有了“美”的概念,而且很通行,用“嘉”而不用“美”,屈原是有他自己分寸的。作为“皇考”的伯庸未必是父亲[注:黄灵庚说:“皇考,古来聚讼纷纭,未有确论。”刘向、洪兴祖都认为是先祖或远祖。见黄灵庚《离骚校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24页。本文有关《离骚》词句上的释训来源,多参考此书。]。今天我们读这句诗时,感到屈原流露出的是一种高贵和自矜的口气,而“今译”则很难体现出来。译诗第四句用同样的句式,让人感到单调、重复和累赘。更根本的是,楚辞最重要的特征就在它的语气词“兮”字,“今译”没有了这个词,整个诗的节奏、韵律以及相应的语言上的韵味都没有了,就不再是“楚辞”了。
事实上,楚辞的韵读也是非常讲究的,在王力先生《楚辞韵读》中,这几行诗的韵读是这样的: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jiong)。/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heung)。(东冬合韵)/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mieng)。/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kiuen)。(耕真合韵)〔7〕
整个《离骚》是两句一节,每节都符合古韵。每一句中间都用语气词“兮”进行停顿,使诗句在语气上有所舒缓,同时又避免了全诗押韵所造成的语感上的单调。但“今译”之后,这种节奏、韵律和语感上的讲究以及艺术性全没有了,相应地,在书写上,诗句被拆开,诗节也体现不出来。楚辞的特殊的艺术形式都没有了,哪里还能叫楚辞呢?
这不是郭沫若的过错,这是所有古诗“今译”固有的问题。具体于《离骚》,我们还可以看看其他的“今译”,比如张光年的“今译”:
我是颛顼皇帝的后代,/先父是忠贞的伯庸。/我诞生在寅年寅月的庚寅日,/
当时北斗星指向东方的天空。//为了我光荣的生日,/先父赞赏我为我命名:/我的名,代表苍天的公正;/我的字,显示大地的丰盈。〔8〕
作者在“今译”的理念上很复杂,一方面强调“直译”:“经过多次的考虑,我仍然选择了一行对一行的近乎直译的步法。”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我有我自己大胆的解释和处理”,“我的译文随时随地都想迁就那个在我的理解所能够触到的范围之内的作者当时的创作意欲”。〔9〕但这不过是一种主观愿望罢了。从“译诗”来看,事实上也是充满了主观性,与原诗不仅是在形式上差距甚远,内容上也有很大的差距。“高阳”是“颛顼”有天下时的称号,二者可以说是同一对象,但之间具有细微的情感上的差别,“颛顼”比较中性,而“高阳”则具有感情色彩,这正如叫爸爸和叫爸爸的名字,其色彩意味不同一样。“忠贞”则是凭空加上去的。“当时北斗星指向东方的天空”,这有天文学上的根据,但这是后人的演绎和推算,原诗中根本就没有这种内容,也没有这种意味。读这种译文,我们很容易就想到“贵人出,有祥瑞”的中国传统文化逻辑,因而具有封建主义的庸俗气。此外,“光荣”何来?“赞赏”何来?“取名”和“命名”这在今天是两回事,“取名”用于人,“命名”用于“事”与“物”,现代汉语的日常习惯中,如果我们说“鲁迅的父亲给鲁迅命名为周树人”,这可以说是不通的。最有意思的是,屈原的“名”和“字”经过这样一“今译”之后,没有了。这与其说是“翻译”,还不如说是创作。作为个人化的解读它绝对是可以的,但作为“文学翻译”,则严重地违背了文本,它连最基本的“保持内容不变”这一要求都没有达到,更不要说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了。
相比较而言,作为学者的姜亮夫则严肃多了,他是这样“今译”的:
咱家是始祖高阳氏的后代子孙,/伯庸是我父亲。/属寅的那年当着正月的时候呵,/我在庚寅的那天降生。//先父研究审度了我初生的气度,/始赐给我一个美名。/名我叫正则,/后来我成人了,又为我起了一个字——灵均。〔10〕
但它同样值得追问,除了上述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些新的疑问,比如,把“帝”译为“始祖”,是否合适,值得商榷,“始祖”是后人对颛顼的尊称,包含很浓的情感色彩,站在今人的角度,我们可以把颛顼称作“始祖”,但屈原未必可以这样称呼,也未必愿意这样称呼。把“初度”译为“初生的气度”,看起来倒蛮像,但未必不是臆测,事实上,姜先生后来订正了这一想法,在《重订屈原赋校注》中,他这样说:“初度王逸注:‘观我始生年时,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云云、此说至确。余旧说从戴震以为初生之器宇,空疏不与上下文义相会,非也。”〔11〕而最后的一句则完全是根据中国文化的一般特征进行的揣度,也许“字”的确是屈原成人之后“又”起的,但从原诗本身我们看不出来。
《离骚》的开头两节四句,内容相对客观,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和阐释,意思和文脉也大致清楚。从翻译的角度来说,这是相对可译的。但为什么三位名家的“今译”都有很多疑问,经不起追问?不论是对于新诗还是对古诗,郭沫若的感觉和内修都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作为解读,郭沫若的“今译”具有独特的价值,并且在新诗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但作为“翻译”,它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诗歌翻译属于“不可为”,“不可为而为之”,自然是失败。姜亮夫先生也深切地感受到古诗“今译”的“不讨好”,他译完《屈原赋》之后感叹道:“翻译实在是件极难的事,尤其是译诗歌。”“为了一字一句的翻译,往往成天去搜寻合乎普通语句的标准词汇,至于韵我也想找到人人能读得准的那些。这时遇到的困难真是千千万万,不可言语。这说明,三代到现在,语言的结构习惯与兴废变化是很大的。翻译古籍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12〕①对于“今译”,姜亮夫先生是潜心地研究过的,对于楚辞今译,他也是非常严肃的,花了很多时间和功夫,比如文体、语法、词汇、韵律等,他都有自己的思考。他的楚辞校注非常有影响,但“今译”并不成功,这与学问无关。“今译”的困难“千千万万”,这些困难不可能解决。
(二)
古诗词之所以不能“今译”,首先是由语言体系之间的差异造成的。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虽然都是汉语,但它们实际上是两套不同的语言体系,在“表达观念”②上主要体现为两套词汇。现代汉语是以白话口语为主体建构起来的,在词汇上它大量继承古汉语词语,但更多的是大量吸收外来词语,所以在“表达观念”上现代汉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现代汉语在“表达观念”上深受西方语言的影响。词的意义并不完全取决于词义的约定俗成,同时深刻地受制于与其他词语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古代汉语不仅是一个语言系统,也可以说是一种语境,作为一种语境,它有形和无形地制约着中国古人的思想方式和观念表达,就是后现代语言观所说的“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比如古代汉语缺乏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话语,所以中国古代自然就缺乏这种思想。即使词语相同,但由于所属的语言体系不同,其意义也有差别,比如“道”、“理”,它们既是古代汉语在思想层面上的关键词,也是现代汉语在思想层面上的关键词,但其内涵明显不一样。对于“道”,古人谈到它时从来不解释,也不限定,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它的词义却经常遭到追问,所以现代人总是这样言说它:什么是“道”?
语言体系的不同以及意义与语境之间的紧密关系决定了词义之间不具有对等性,观念表达上不具有对等性,这种不对等性就决定了具体对于古诗词“今译”来说,翻译不可能做到“等值”或“等效”。翻译界一般把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称为“语际翻译”,把相同语言之间的翻译称为“语内翻译”,前者如英汉互译,后者如把古典英语译成现代英语。我们也可以在约定的意义上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翻译叫做“语内翻译”,但实际上它和真正的“语内翻译”有本质的差别,我认为古今汉语之间的翻译更接近“语际翻译”,因为“语内翻译”是同一语言体系内部的翻译,而“今译”则是两种汉语体系之间的转换,它和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文学上,译作和原作是两种不同的文本,这是公认的事实。原作只有一个,译作却没有数量限制。译作从原作而来,却永远不能替代原作。但文学翻译仍然在世界通行,得到普遍的认同,这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是文化和文学交流的需要。能够读原作并且能够在原语言上欣赏原作,这当然再好不过了,但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都只能是少数人才可以做到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能借助翻译。翻译不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会造成对原作有所损失,有所增益,从而翻译文本和原作在文学价值上有差距,也就是说,所有的翻译都是“权宜之计”,但目前全世界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语言上的隔阂问题之前,或者说语言交流还存在着障碍的情况下,翻译是最好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当然,翻译也具有创造性,是二度创作,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创作来阅读和欣赏,这是翻译被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接受跨文化的文学翻译。
“今译”当然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具有解释的意味,就是郭沫若所说的“今译”笼统地包含了“考证、研究、标点、索引”等,在这一意义上,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看作是“注”、“解”、“疏”在现代的合理延伸,可以为我们理解和欣赏古典诗词提供一种参考,但这种参考价值非常有限。二是等同于“文学转换”,即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和把汉语诗歌译成外语或把外语诗歌译成汉语具有同样的性质。当今的“今译”多表现出这样一种“翻译”的意向,也是以“翻译”形式存在和通行的。在这一意义上“今译”就是“相当于”、“换一种说法”、“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等,就是“语言转换”,就是《现代汉语词典》所定义的“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也就是翻译家所说的“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即等值)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话语的过程”〔13〕。本文所探讨的就是这种“今译”,否定的也是这种“今译”。在“翻译”的意义上,我认为“今译”是不适宜的,它并没有解决(事实上也不需要解决)由于语言的变化所造成的母语文学陌生感的问题。它伤害了古典诗词,有损于古诗词的文学性和形象,招致一些误解。
当今的文学读者古汉语水平的确大大下降了,和古人有天壤之别,与现代时期相比也有巨大的差距,但还没有到需要翻译才能读懂古诗词的地步,当代教育体制下的中学文言文教育,对于阅读古诗词还是够用的。所以,与外国文学“翻译”不同,古诗词“今译”不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不具备跨文化性,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今译”的合法性从来没有得到理论上的论证,某种意义上说,“今译”也从来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在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界,“今译”从来就不入学者的视界。有外国文学翻译大师,但从来没有古诗词“今译”大师,即使郭沫若这样的文学大师、学术大师,他的“今译”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他也不能提高“今译”的地位。所以我认为“今译”是错误“翻译”理念下的错误产物,是一种充满了误解的文学现象。我们承认“今译”的创作价值,但不承认它有“翻译”的价值,“今译”具有二度创造性,可以当作一般创作来阅读,但在实际上这种二度创作是没有市场的,它有点像仿制品或者假货,我们读不懂原语外国文学,翻译作品还聊可充数,但在中国,古典诗词唾手可得,没有文字上的障碍,通过一定手段就能够读懂,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读“今译”这种“伪劣产品”呢?
对于古典诗词的理解和欣赏来说,“今译”是一种辅助性的办法,但它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今注”。“今注”和“今译”经常被相提并论,但二者既有联系又有本质上的区别,当“今译”作为翻译时,二者有不同的意味,也表现出不同的理念,“今注”主要是相关文史知识介绍,其目的是引导读者阅读和欣赏,虽然也有“该注的不注不该注的注”这样的“伪劣注”,但优秀的“今注”多是读者懂的就不注,读者不懂的就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形式上非常自由。但“今译”则受形式限制,不能译的也要硬译,不需要译的也要硬译,具有强加的意味,其结果是让人反感。
古诗词之所以不能“今译”,其次是由文学的特点以及古诗词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文学作品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不具有物质性。语言对物质性的东西只是符号或工具,是附属性的,重新命名或者换一种语言符号不会改变它的客观性和实在性。文学中当然也有工具性的语言,也有物质性的事物,比如物质名词、地名、时间、方位、称谓、亲属关系等,这些内容都可以翻译,但文学总体上不是这样。文学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创造,它既具有内容上的客观性,同时又具有开放性,它的作用、价值和意义都是读者在与文本的对话中完成的,文本实际上给读者实现价值和创造价值提供了基础和平台,读者的想象和创造都是建立在文本的基础上,改变文本,这一切都会发生改变。
中国古典诗词尤其特殊。一定意义上,古诗词是古代汉语的产物,它在文体、节奏、韵律、词法、语法、格式等方面都与古汉语密切相关,古汉语是古诗词深厚的土壤,它的生长和繁荣都与这一土壤有关。古诗词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还有广泛的影响,还能得到中国人广泛的喜爱,与古汉语对我们来说还不十分陌生有关,毕竟现代汉语是在古代汉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语音、词汇、词义乃至语法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有一天,古汉语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那古诗词的接受就到了非常艰难的地步。不懂古汉语,是不能真正理解和欣赏中国古典诗词的。而把古诗词翻译成现代汉语,则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古诗词。改变语言方式,古诗词的一切,从内容到形式到它的艺术性到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想象空间,一切都改变了。
真正创造性的文学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于中国古典诗词来说,每一首诗就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由特殊的字、词、句构造而成,特殊的字、词、句不仅表达出一定的思想、情感,构建一定的文体形式和结构,组织出一定的音韵旋律,同时还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情绪氛围、意境。好的诗,不仅有诗内的东西,还有诗外的东西,既有可以言说的东西,也有不可以言说的东西。比如“空灵”,弥漫在语言的缝隙之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每首诗就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其中每个字、词都发挥着它独特的功能,而且这种功能的东西是不能进行“解剖学”分析的。诗的意义和艺术既表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形式上,“形式”也具有“意味”。绝对精妙的诗一字不移,绝对精妙的句子也是一字不移,“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至今还没有人找出一个可以替代它的“字”。现在的“今译”把整个语言“移”掉了,整个形式都变化了,形式的“意味”没有了,“旋律”没有了,诗外不可言说的“空灵”失去了依托,哪里还能有精妙可言呢?一句话:一译就俗。
文学的创造性就体现在它语言的独一无二性,也就是说,在语言形式上它是它自己,而不是别的。如果它可以轻易地进行语言置换,那么它独一无二性就值得怀疑了。古诗词的“文学性”就表现在它的表述之中,换一种语言就是换一种表述,新的表述应该仍然有“文学性”,但那是另外一种“文学性”,已经不属于原诗所有。
(三)
纵观当今的各种古诗词“今译”,我感觉到“今译”实际上是从三个方面损害原诗的:一是改变内容,二是增加内容,三是减少内容。比如白居易的《长相思》①,我比较随意地挑了两种“今译”。
徐荣街、朱宏恢今译:
汴水奔流,泗水奔流,/流呀,流到长江边上古老的渡口/南方的远山望去又多又小,/山山岭岭都凝聚着无限哀愁。//想念没个尽头,怨恨没个尽头,/爱人回来心头的烦恼才会罢休。/一轮明月照在高楼,/她含愁远望,倚在窗口。〔14〕
杨光治今译:
汴水不停地流,泗水不停地流,/流呵,流到这瓜州的古老渡口。/江南的点点山峦都凝聚着哀愁。//思念没有尽头,怨恨没有尽头,/直到爱人回来时烦恼才会罢休。/明月当空照,她独个儿倚高楼。〔15〕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白居易的诗一向以通俗易懂著称,应该说,这首词在意思上也没有什么难解的。但从译作来看,即使是在诗意上也仍然不能说契合了原词。词在中国古代是有严格格式规定的,包括句式、音韵等,所以中国古代词的写作又叫“填词”。但“今译”之后,除了在某些意思上有所保留之外,哪里还有词的样子呢?哪里还有词的味道呢?一点词的语感都没有了。
“流”,也可能是急速地流,也可能是缓慢地流,“奔流”就把“流”的意义缩小了。“汴水流,泗水流”,简洁而流畅,加上的“不停地”完全是废话,难道还停一下再流?“瓜州”是具体的地方,把“瓜州”译成“长江边上”就把范围扩大了。“瓜州”古代属吴国,所以叫“吴山”,叫“吴山”而不叫“南方的山”,属于用典,这是中国古典诗词惯用的写作技巧,具有文化和风尚的意味。这里“吴山”可能泛指南方的山,也可能具体指“瓜州”一带的山,把“吴山”译为“江南”的山或者“南方”的山,就把词义的模糊性去掉了。同样,“愁”、“思”、“恨”都是内涵非常丰富的词语,包容了许多与“愁”、“思”、“恨”相关的意思,具有模糊性,现在把它们译为“哀愁”、“思念”、“怨恨”,词义的微妙性就没有了,而微妙性和模糊性恰恰是古代诗词艺术韵味产生的重要来源。
“悠悠”就是“悠悠”,现代汉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无法描述它的状况,也无法对它进行情感范围的限定。在这首词中,“思悠悠,恨悠悠”,这是非常美的句子,对于它,我们只能想象,不能解释,一解释便没有了味道。“点点”比“又多又小”含义丰富和模糊,它既是修饰“吴山”的,又是修饰“愁”的,“点点愁”绝对不能分开。“远山”这里不通。
“月”在古代是一个很特殊的意象,它特别具有“思念”的意味,所以,“月明”在这里既是诗歌中的景象,又具有象征的作用,而这是没法翻译的,因为现代文学中已经不再这样使用“月”的意象。此外,“楼”未必是“高楼”,“倚楼”未必是倚在楼的“窗口”,未必是“独个儿”,而“含愁远望”更是凭空想象。
伏尔泰说:“凡妙语的注解者总是个蠢人。”〔16〕我想这特别适用于古诗词的“今译”。如果撇开原诗,单看“今译”,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今译”都不能说是好诗,放在古代文学中不是好诗,放在现代文学中也不是好诗。
古诗词中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很多都不能“今译”。
首先,格式不能“今译”。比如律诗、绝句、词、曲,它们都有非常严格的形式限定,诗句的长短、音韵都比较固定。“今译”因为换一种语言,必然会改变诗句的长短,改变诗句的音韵,从而改变诗的节奏和韵律。“今译”之后中国古典诗词就不再是律诗、绝句、词、曲等,而是新诗,自由诗,或者“新格律诗”。
其次,意境不能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特别追求“意境”,所谓“意境”,指的是作者所描写的景物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完全地融合在一起,“情”和“景”都表现到极致,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17〕。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①,在思想上,这首散曲表达的是传统的“游子思乡”的主题,但写作方式上非常独特,全诗四个画面,十种景物,无一不具有强烈的主观情思色调,即哀愁、凄凉、衰惫、凄婉、沉重,从而有效地表现了思乡的哀婉。十种景物就是十种意象,每一种意象都具有相同的色调,从而从总体上构成一种特殊的氛围。这种氛围与全曲的每一个字有关,但又不能在某一个字、词和句子中找到,它是一种组合。就形式和技巧来说,这首散曲除了一个“在”字以外,其他都是名词。语法关系、景物与景物之间的关联、动作都是隐含的,且具有模糊性,需要读者去填充,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它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我们且看一首“今译”:
深秋傍晚枯藤缠绕的老树栖息着乌鸦,/小桥下流水潺潺桥对岸出现一户人家,/
荒凉的古道上冒着凛冽西风骑着瘦马。/颠簸中寒冷的夕阳慢慢地向西山落下,/断肠的游子仍漫无目标地流浪在天涯。〔18〕
“今译”完全破坏了原诗的组合,从而也就破坏诗的氛围。满是动词、副词,主语、谓语、宾语、状语、定语齐全,原诗的虚空也被填实了。稍加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今译”基本上是把原诗句进行了扩充,附加了一些语法成分。但这样一扩充,一附加,原诗最精华的表达方式就没有了,精炼没有了,“空灵”没有了,语感也没有了,哪里还是“曲”呢?更重要的是,译者所填充的内容不过是一些废话,不仅画蛇添足,且有违原意。“荒凉的”修饰“古道”不妥;“寒冷的”修饰“夕阳”不通;“鸦”是否就是“乌鸦”,尚有争议;“昏”在原诗中非常重要,但翻译却被遗漏了;诗中最需要翻译的是“断肠”二字,因为这个词现代人已经很陌生,但“今译”恰恰没有译这个词。“断肠的游子”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很容易被人坐实为“断了肠子的游子”,而不是“极度悲哀的游子”。“今译”中唯一的翻译是把“人”译为“游子”,但这恰恰是最不需要翻译的,除了“人”这个词古今一样以外,最重要的是“人”在本曲中未必是“游子”,“断肠人”也可以理解为“我极度思念的人”。
诗歌与其他文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往往是选取生活中最富于表现力的片断和景象来表达情感,而舍弃或省略平庸与杂芜,留下精髓。所以,诗歌尤其以简练著称。译诗实际上还原了这些平庸与杂芜,因而原诗语言上的简洁现在变得啰嗦,原诗的意境荡然无存,不仅不能帮助我们欣赏原诗,反而会妨碍对原诗的欣赏。
再次,古诗词特别具有多义性,而多义性是无法翻译的。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多义性,而诗歌由于思维具有“跳跃性”等特征,多义性尤其突出。而中国古典诗词,由于用词单字化、词义的模糊,再加上用典、修辞、意象等广泛的使用,所以多义性更是比比皆是。多义性存在着多种情况,有的是整首诗具有多义性,或者意义的多重性;有的是句子多义;有的是词多义。事实上,即使是最清楚明白的诗也有进行其他解释的可能,比如李白的《静夜思》,有人认为“床”应该是“井台”,这其实很有道理。如果这一观点成立,整首诗的情景、意象以及我们想象的方式都要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这时我们应该如何“今译”呢?选择一种就会使诗的意义失去另外一种可能性。再比如,李商隐的诗一向以晦涩难懂著称,他的许多诗至今仍然歧见重重。对于这样的诗,原诗都没有搞清楚,翻译又何以为据?强行翻译势必会损害原诗的复杂性。双关语是所有翻译中迄今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古诗词中的词语很多都有双关性,我们又如何今译?
诗歌的多义性是由诗歌文本决定的,是诗歌文本引发的读者对于诗歌的多重理解,具有合理性。文本具有开放性,任何解释,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看作是诗的本义。向读者开放,向未来开放,这是文学作品的应有之义,所以“理解”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具有本体性,这有“新批评”理论和“解释学”理论为证。而翻译就把诗歌向读者开放、向未来开放的门给堵住了,把潜文本磨灭了,把其他解读的可能性都给清除了。
此外,有的古诗词根本就不需要翻译,都是一般的词语,语法也不复杂,在意思上既浅显又通俗,清楚明白,妇孺皆知。对于这样的诗,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翻译。比如李白的《静夜思》,即使“床”作“井台”解,意思也是清清楚楚的,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新诗不知好懂到哪里去了。不翻译,意思是清楚的,简洁的,主题集中,但翻译之后反而歧义丛生,旁逸出很多“俗气”来,甚至喧宾夺主。我们不妨选一种“今译”:
月光如水静静在床前流淌,/好似铺在地面的皑皑秋霜。/抬首仰望遥远天边的明月,/低头思念我那可爱的故乡。〔19〕
陶先生是当今知名的古代文学学者,他们的“今译”以及如此“今译”,实在让人费解。鲁迅有诗句“月光如水照缁衣”〔20〕,但李白这里显然没有“月光如水”的意思。月光“静静地在床前流淌”,无论从原诗来说,还是从译诗来说,都令人匪夷所思。月光何以能“流淌”?“铺”具有人为性,而地上霜显然不是人为的。“霜”无论有多厚,也不可能达到“皑皑”的地步。“抬首”比“举头”更具有文言性。既然是“举头”望明月,月亮就不应该是在“天边”,而且月亮虽然事实上遥远,但看起来并不遥远。“故乡”未必“可爱”。读这样的“今译”反而让我们一头雾水。
古诗词是古代汉语的文学,“今译”之后就变成了新诗或自由诗,属于现代汉语的文学,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归属也不同了。新诗与旧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应该充分尊重这种差异,充分尊重古诗词的历史文体。对于古诗词,由于文化环境、文学观念特别是语言方式的不同,今人与古人可能有不同的阅读,这是合理的,古诗词正是在不同的阅读中延续生命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古诗词变成现代的方式呢?
“翻译”具有建构性,现在的翻译标准都是在翻译实践中逐渐建构起来的,同样,现代翻译实践又在建构未来。作为“错误”的古诗词“今译”经过一代一代的阅读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会逐渐被认同,既认同这种“今译”理念,也认同翻译中的内容,慢慢地,翻译中的“不对等”内容在接受的意义上就成了“对等”,这样,古诗词在意义上和文学性上就会发生“衍误”,从而被“异化”。这对古诗词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是非常危险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人反对古诗词“今译”。
〔参考文献〕
〔1〕郭沫若.古书今译的问题〔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65-166.
〔2〕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1954年8月19日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A〕.茅盾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311.
〔3〕〔4〕〔5〕〔6〕郭沫若.卷耳集•《屈原赋》今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序,41,序,110.
〔7〕王力.楚辞韵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
〔8〕〔9〕 张光年.《离骚》今译〔A〕.张光年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95-196,194-195.
〔10〕〔12〕姜亮夫.屈原赋今译〔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2-3,序例.
〔11〕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7.
〔13〕廖其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45.
〔14〕徐荣街,朱宏恢.唐宋词选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22.
〔15〕杨光治.唐宋词今译〔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8.
〔16〕伏尔泰.哲学通信〔M〕.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8.
〔17〕王国维,宋元戏曲考〔A〕.王国维文集:第1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389.
〔18〕张国荣.元曲三百首译解〔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151.
〔19〕陶文鹏,吴坤定,张厚感.唐诗三百首新译〔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489.
〔20〕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87.
(责任编辑:尹 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