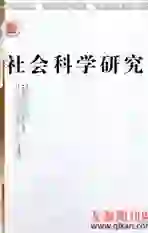《庄子》“言意之辩”的本体论视阈和诠释学维度及其意义
2009-03-10余卫国
〔摘要〕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辩”肇端于中国哲学范式原创性建构的先秦时期或中国“哲学的突破”期,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模式”为背景,以社会治乱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以本原、本体和境界之“道”的确立为基础,以“言道悖论”的发现为滥觞,既涉及对本原、本体、秩序和境界之“道”基本内涵的理解问题,又涉及“道”与“物”、“言”与“意”的关系问题;既涉及所得之“道”能否言说和应当如何言说的问题,更涉及究竟如何对待这些关于“道”的言说的问题。而如果说这些问题的提出是老子作为中国哲学之父的内在根据的话,那么,对这些问题的形上追思和理论回答,则不仅构成了《庄子》“言意之辩”的本体论视阈和诠释学维度:形而上学本体论层面上的“言不尽意论”对现象性日常生活层面上的“言尽意论”的解构和本体诠释学意义上的“得意忘言论”对“言道悖论”的超越;而且决定了《庄子》“言意之辩”的理论意义及其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 《庄子》;言意之辩;言不尽意;得意忘言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1-0108-07
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的“言意之辩”,既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内在性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哲学之所以为中国哲学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1〕
一、《庄子》“言意之辩”的本体论视阈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史上的主体、语言和存在(“道”)关系问题上的“言意之辩”的历史和逻辑的展开,是以本原、本体和境界之“道”的确立为基础,以“言道悖论”(道不可说,但又不能不说)的发现为滥觞,而以本原、本体和境界之“道”的内在超越性为根据,既涉及广义的“存在”,又涉及“人”之“在”,而广义的“存在”作为“人”之“在”的应然形态,本身则蕴含着对“人”之“在”的意义的理解和追求。所以,这里的首要问题便是何为“道”,而对这一终极问题的形上追思,正构成了《庄子》“言意之辩”的逻辑起点和本体论视阈。
综观《庄子》文本,“道”作为第一原理,首先是构成存在的本根、本原和本体:“夫道,无情无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无情无信”,言其真实而质有。《庄子•秋水》云:“‘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是信情乎?”成玄英疏:“信,实也。”又《庄子•应帝王》有“其知情信”句,成玄英疏:“率其真知,情无虚矫,故实信也。”可见“道”首先是真实的存在。“无为无形”,言其顺自然之性而无不为,但又不是具体有形之物。老子讲“无为”,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七章)引申于政治,便是“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庄子亦讲“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则阳》)并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应用于政治,便是“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治矣。”(《庄子•应帝王》)淡漠而顺物自然,就是无为。郭沫若考“无为无形”为“无象无形”亦是。“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见”,以其存在,故可传而可得;以其无象、无形,故不可授而不可见。“道”虽然“不可授”、“不可见”,但“道”却不能离开具体有形之物而存在。“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庄子•知北游》),万物都体现“道”。而“庖丁解牛”所寓意的,正是“道”的这种内在而超越的性质。“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表明,“道”的存在是自为的自在。“道”不仅是绝对,而且只与自身同一。它的这种存在是没有除它本身以外的其他任何原因的,它即是它本身存在的根据。“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则是就“道”的功能而言。成玄英疏云:“言大道能神于鬼灵,神于天地。”这表明“道”具有化育天地万物的功能,是天地万物之生命和秩序的赋予者,而天地万物皆因“道”而获得其存在的根据和运行的秩序。所谓“太极之先”、“在六极之下”而不为高深,言道的存在在空间上的无限性;“先天地生”、“长于上古”而不为久老,则言“道”的存在在时间上的无限性。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无”。正如郭象注云:“言道之无所不在也,故在高为无高,在深为无深,在久为无久,在老为无老,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也。”这正是“道”作为本原和本体的内在根据。
“道”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本根、本原和本体,同时体现为存在的秩序和人们所追求的境界,所谓“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庄子•天道》)“道”既赋予天地万物以内在的秩序和生成变化的规律,也规定着天地万物的运行方式:“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庄子•知北游》)“道”作为存在之序,不仅体现为天地万物之序,而且体现为社会人伦之序。社会人伦之序作为“道”的内在之序或存在形态,即庄子所说的“至德之世”:“夫至德之世,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矣。”(《庄子•胠箧》)“至德之世”以“至治”为特点。与“至德之世”相对应的是分化以后的非至德之世,非至德之世作为现实的社会之序,亦有治乱之分,并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庄子•让王》)以天地之序为形而上的根据,社会之序本于天地之序:“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庄子•天道》)“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庄子•天道》)“道”或“天道”作为人道之本,以无为为自身的特点:“无为而尊者,天道也。”(《庄子•在宥》)体现在人道上,就是“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庄子•天道》)其作为人的行为原则,就是“无为”:“夫帝王之道,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者,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庄子•天道》)与之相关的行为方式是利用不同的力量,避免仅仅凭借一己之力:“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庄子•天道》)与天地自然之序和人伦社会之序相适应,“道”作为存在之序,同时还体现为人存在的精神之序——精神的本然之序或自然之序——“和”的精神境界:“心莫若和”(《庄子•人间世》);“夫德,和也”(《庄子•缮性》);“德者,成和之修也”(《庄子•德充符》);“游心乎德之和”(《庄子•德充符》);“守其一以处和”(《庄子•在宥》)。“和”作为心或精神存在的形态,与“一”相联系,是“道”的存在形态或本然状态在人的心灵层面上的具体呈现;而“和”作为一种心态、心境,即平和、宁静,则是摆脱外在干扰后的一种德性与品格。如果说后者主要体现为一种精神价值追求或修养过程,那么前者则无疑具有本体和境界的双重内涵和性质。〔2〕
以其对本根、本原、本体、秩序和境界之“道”的理解和体悟为视阈,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言意之辩”,同时涉及如何“得道”的问题。以其对“失道”原因的深刻洞见为基础,庄子将其归结为三个递进的层次或境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庄子•齐物论》)其一,“以为有知”。然而,在庄子看来,“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所以说:“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庄子•在宥》)其二,“以为有物”。然而,殊不知“物”与“物”之间的区别并不具有绝对的性质。所以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秭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可睹也。”(《庄子•秋水》)“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其三,“以为有封”。“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之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庄子•天下》)“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所以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因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所谓“莫若以明”,就是恢复到是非未彰的本然或自然形态:“道”所指示的最高境界。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得道”并进入“道”所指示的境界呢?
庄子提出了“以明”、“见独”、“心斋”和“坐忘”的“得道”方法。“以明”与认识上的“有待”、“有分”相联系,其作为一种“得道”、“闻道”、“体道”之方,就是要“破对待”,“一天人”,“齐万物”、“齐是非”,消除一切对立,进入“道通为一”的无待之域。《庄子•齐物论》载:“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而“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的寓言所寓正是“道”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或无待之域。而所谓无待之域,就是解脱了有待束缚的逍遥之域或“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的自由之境。“见独”与“外物”相联系,其实质是经过一定的修养之后,忘外物,忘生死,无古今,与道合一,大彻大悟的精神境界。南伯子葵向女偊请教“学道”之方,女偊说:“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庄子•大宗师》)“坐忘”与“有己”相联系,实质是“无己”。《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之谓坐忘。”与“坐忘”相联系,“忘”同时还包括“道忘”。《庄子•大宗师》说:“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又说:“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所谓“道术”,即“得道”的途径、方法、原则和规律,这里主要是指工具化或知识化的“术”。“忘乎道术”,其实就是要忘掉或放弃工具化或知识化的思想进路,“绝圣弃知”而与“道”直接“同一”。所以,在庄子看来,与其受制于世俗的困扰和痛苦,“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庄子•大宗师》)。那么,如何才能进入“两忘而化其道”的境界呢?这就是“心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虚”与“静”相联系,“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则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则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庄子•天道》)《庄子•天道》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宗大本,与天和者也。”所以,“以明”、“无己”、“见独”、“心斋”、“坐忘”都是内向的修养方法和整体直觉的思维方法,目的都是通过虚静内心,以达到精神上的“无待”、“无物”、“无己”的“静”、“虚”形态。
与如何“得道”相联系,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言意之辩”,同时还涉及所“得”之“道”是否可以言说和究竟应当如何言说的问题。这是老子首先遭遇的问题,当然也是庄子必须面对的问题。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而庄子则进一步明确指出:“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那么,原因何在?
在庄子看来,这首先是因为“道”是本根、本原、本体,是“形形”者、“物物”者,是“实存”、“实在”,而不是西方形上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亦不是自然界的“因果规律”或“逻各斯”之类,而是具有终极性、无限性和整体性的“实存”或“实在”,并因此而具有不可言说的本质规定性。“道”既然不是作为实体存在的有形之物,因而“不可数”、“不可分”,故“不当名”,“不当名”当然也就不可以言说。当然,庄子并不否认在“物”的范围内,“言”是能够尽“意”的。他说:“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急缓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精微之可志也。随序之相理,桥运之相使。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庄子•则阳》)又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名”相对于“实”而言,故有“形名”或“刑名”之说,“道”无形当然“无名”,“无名”当然不可以言说,这是庄子的逻辑。
但问题是,“不言”,谁知其“道”?这是老子哲学首先遭遇的问题,同样也是庄子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始终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在庄子看来,“道”不可“言”、“不可授”,“言”而非“道”,“言不尽意”,并不是因为“道”真的不可言说,而是因为人们多倾向于逻辑地言说,于是才有了“言道悖论”的产生。而问题的实质就在于“言”与“道”之间的“不齐”或不对等。作为对象世界,有“道”、“物”之分,作为语言,有“大言”、“小言”之别,以指称“物”的“小言”以言“大道”,这是“言不尽意”的最根本的原因:“言而足,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庄子•则阳》)所以,“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庄子•则阳》)所以庄子说:“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庄子•则阳》)而庄子用以超越“言道悖论”的途径和方法便是:“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庄子•齐物论》)即放弃以“是”为核心的逻辑化的或知识论的言说方式,而代之以“言无言”的“诗意”“道说”的言说方式去言说那本“不可说”的“道”。
《庄子•寓言》篇在自叙其著述特点时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庄子•天下》篇总结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郭向《庄子注》云:“寄之他人,则十言有九言信。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言见信。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可见,所谓“寓言”,就是寓理于事,寄意言外,而不以直白明说的言说方式;所谓“重言”,就是借重古人之言,正反两面都说,或展示某种佯谬悖反的言说方式;所谓“卮言”,即“优语”,实质是随缘婉转、自由无著的言说方式,它可以使言说顺应天下万物复杂多样、变幻无穷的存在情态并合乎“天钧(倪)”“中道”。
其实,不管是“寓言”还是“重言”、“卮言”,其作用无非是一种只将自己体验所得的道理,或寄托在一个虚设的故事之中,或假借众人所信服的先知先哲的嘴巴说出来,或依循事理之本然而作出自然的表达,至于道理的究竟,便留待读者去自由体悟的言说方式。正如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所说:“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于人,十言而九见信也。”而“寓言”、“重言”、“卮言”之所以能够实现对“言道悖论”的超越,其实就根源于“道”的内在超越性和语言的“逻辑根性”。正因为如此,既不能离言以显“道”,也不能局限于语言的“逻辑根性”,而有效超越的话语方式便是“诗性语言”的“诗意言说”或“诗意道说”。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诗性语言”才是最能体现语言的“道说(Sagen)”本性的“本真的语言”。“逻辑—工具性语言”是作为人的一种表达工具使用的,代表的是一种“人之说”的话语样式;而“诗性语言”则代表一种真正的“语言之说”。与受制于语言自身的逻辑根性和人的工具理性、识见、偏私等等有限性的“人之说”相比较,“寓言”、“重言”、“卮言”作为一种“诗性语言”的“诗意言说”话语方式,作为一种更具本真的“道说”力量的“语言之说”,自然也就更能切近“大道”本身了。〔3〕
然而,即使是最切近于“道”的“诗意言说”或“诗意道说”,与“道”或“意”毕竟不是同一个东西。事实上,语言的产生和存在,不仅造成了人与人的间隔,而且造成了人与道、道与意的分离,而当人们不得不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道”的体认和感悟(“意”)时,便有了“言道悖论”的产生。尽管真正的哲学都要受到语言的纠缠和“言道悖论”的困扰,但人类超越语言的界限和“言道悖论”的努力从未停止过,或许永远也不会停止。可以说,正是由于“言道悖论”的存在,不仅成就了哲学和中国哲学,而且成就了人的超越性的理想和追求,只要人类不放弃对超越性理想的无限追求,那么,对“言道悖论”的超越就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庄子》“言意之辩”的诠释学维度
不过,这里的问题是,既然语言不能完全表达体认主体对“道”的体认和感悟(“意”),那么,究竟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些“道言”、“道说”?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把握体认主体对“道”的体认和感悟(“意”)?这是《老子》留给后世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庄子》必须面对和回答的基本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形上追思,正构成了《庄子》“言意之辨”的诠释学维度:语言的“工具论”对“语言本体论”的解构和“得意忘言”论对“言道悖论”的超越。
按照传统观点,圣人之“言”即圣人之“意”,圣人作为本根、本原、本体之“道”的体认主体,不仅与“道”同一,而且本身就是“道”的人格化,圣人之“言”即圣人之“意”,即“天地之道”或“道”。“言”、“意”、“道”之间不仅存在着天然的对应关系或完全的“同一”关系,而且相对于特定的“言”,其所表达的“意”也是确定不移的,因而通过“言”是可以完全把握圣人之“意”和“天地之道”或“道”的。正如《荀子•正名》所说:“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是为本体诠释学意义上的“言尽意论”。语言在这里不仅被赋予了本体的意义和治乱的功能,而且本身就意味着存在、意味着秩序、意味着价值和规范。正如孔子所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亦如《吕氏春秋•离谓》所说:“言者所以喻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所谓“正名”,所谓“言”与“意”的统一,其实质就是通过语言的秩序化来使社会关系秩序化。
然而,在庄子看来,“言”、“意”、“道”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对应关系或完全的“同一”的关系。“言”既不足以完全表达圣人之“意”,也不足以承载“天地之道”或“道”,是为“言不尽意”之说。而“言”之所以不能“尽意”,首先是因为“言”以“名”为基础,而“名”是相对于“实”而言,而“实”为具体“有形”之“物”,“名”可以命“实”,“言”可以“尽物”,但不能“尽意”,“意”是相对于“道”而言,而“道”是本根、本原和本体。“道”无古无今,无始无终,甚至可以说是“无”。“道”“无形”、“无名”,当然不可以言说。所以庄子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庄子•齐物论》)故“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闻道。”(《庄子•知北游》)“道无问,问无应”才是“道”。所以“齿缺问于王倪,四问而不知”(《庄子•应帝王》),“知问无为谓,三问而三不答”(《庄子•知北游》)。此为禅宗道断言语,不立文字,答非所问、信手拈来的禅机,借公案、问答、棒喝等“非理性”思维来传达一种强烈的不可表现之感的滥觞。
“言”之所以不能“尽意”,其次是因为“名无固宜”,“言无定意”。在庄子看来,所有命名都不是必然的。“名”与“实”、“言”与“意”之间,不仅不存在一一对应和固定不变的关系,而且充满了偶然性和变异性。不仅同一个“名”可以指称不同的“实”,而且同样的“实”可以用不同的“名”来指称;同样的“言”可以有不同的“意”,而同样的“意”也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这就造成了语言所指称和表达内容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因而通过语言是无法完全把握其所要表达的“意”的。《庄子•知北游》说:“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庄子•应帝王》说:“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所以说:“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毂音者,其有辩乎?其无辩乎?”(《庄子•齐物论》)这是说不清楚的。
“言”之所以“无辩”,在于“成心”。“夫随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庄子•齐物论》)这是产生“真伪”和“是非”的根源。在庄子看来,体认主体在体认、表达和理解与诠释过程中,由于主观情感、经验、愿望、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的目的性渗入,以及体认主体和理解与诠释主体的个体性,不仅使“言”所传达的“意”在不同的主体中具有不确定性;特别是由于主观偏见的影响,即体认主体和理解与诠释主体认识的局限性,从而使所传达的意义只具有相对的性质。
《庄子•齐物论》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所有对“道”的言说都囿于一己之偏见,充其量只能算是“小成”,其实质都是对“道”本身的一种“遮蔽”。语言中那些浮华虚饰之辞,对于语言本身已经是一种“遮蔽”了,而所谓“是”、“非”争辩,也不过是说话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言“是”言“非”,同样是对“道”的一种“遮蔽”。所以,在庄子看来,语言可以“尽物”,但又不能“尽道”;语言有其意义,但又没有绝对意义;语言能够使“道”有所“澄明”,但又难免有所“遮蔽”;争辩或许能决“胜”、“负”,但不足以辨明“是”、“非”。总之,一切言说都是相对的,都有其有限性和不确定性,因而都不足以担当言说“大道”的使命。
《庄子•寓言》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在庄子看来,“无言”是以沉默的方式在表达着“言”:对“道”的体认。沉默式的“言无言”并不等于真正的“无言”,一生静默“无言”,就是以终身“无言”的方式表达着“言”:对“道”的体认。“言无言”,《庄子•齐物论》称之为“不言之辩”、“不道之道”;《庄子•徐无鬼》称之为“不言之言”。无论称它什么,它都是用来切近那“不可言说”之“道”的一种话语方式。质言之,“言无言”应当是真正的“言道之言”。《庄子•则阳》说:“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既然无论言说还是沉默都不足以载道,当然也不足以废道。有人滔滔不绝,其实不着边际;有人默默无言,因为确实无话可说。而“非言非默”则不然,它已从单纯的开口闭口提升到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更高的境界:体道,而非言谈,才能达到物之极处,天道至境;行道而非空谈,才能获得人生意义。〔4〕
据此立论,《庄子》进而明确提出了以“意”为本,以“言”为末;以“意”为体,以“言”为用的“意义论”的本体诠释学思想,从而不仅与儒、墨诸家所倡导的“名实论”,公孙龙子的“指物论”和荀子的“约定论”划清了界限,而且导致了语言的“工具”论的产生和“得意忘言”论的本体诠释方法的提出。《庄子•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所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而传书,世虽贵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不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不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足以传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而读书就是要讲求“神遇”,贵在“意得”,不以语言文字梏其心,以超越语言文字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突破语言文字对“意”和“道”的“间隔”和“遮蔽”,而直接与圣人对话,“与天地精神往来”。所以,《庄子•外物》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那么,如何才能进入“忘言”的状态,并进入圣人之意或“道”的境界呢?这就是“言无言”。“言无言”,从“意”之表达的方面看,就是“言”而“无言”的无心之“言”。无心之“言”,不囿于“成心”、不师乎“成心”,其实质,就是以赤子之心使本然之“道”得以本然地呈现。只有达到了有“言”而“无言”的境界,才能以“言道之言” 同于“道”,从而破除语言对“道”的“遮蔽”。从“得意”的方面看,就是要以“有言”为“无言”而不落于“言荃”,从而达到对“言”所彰显的“意”,乃至“言外之意”的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
“得意忘言”作为超越“言道悖论”的本体诠释方法,其实质就是要超越“言”对“道”的局限和“遮蔽”,以空旷灵明之心洞照于“天地之道”和“圣人之意”。其作为一种本体诠释方法,与注重“文字训诂”和“辨名析理”的诠释方法一起,构成了中国诠释学中的两大传统。“得意忘言”论的提出,其意义在于,它不仅为作为历史存在的经典诠释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而且为以经典诠释为载体,以本体诠释为核心的中国哲学创新发展开拓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三、《庄子》“言意之辩”的理论意义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辩”肇端于中国哲学范式原创建构的先秦时期,既是贯穿中国哲学始终的中心论题,更是中国哲学范式原创建构的理论和方法。而如果将其置于中国哲学逻辑发展和范式建构的整个历史过程中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庄子》“言意之辩”的理论意义,则不仅在于他“以汪洋恣肆的文字形式”,以不拘常理的思想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即境界,并以其广阔的理论视阈和独特的思想进路,洞悉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构建了一个以“道”为本根、本原和本体,以“心斋”、“坐忘”为“为道”、“闻道”、“得道”之方,以“卮言”、“重言”、“寓言”为言说方式,以“得意忘言”超越“言道悖论”的气势恢弘和最具思辨色彩的“道”本体论哲学体系,而且更在于他在《老子》“道论”哲学的基础上,对“道”与“物”、“言”与“道”、“言”与“意”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从而深刻揭示了“言道悖论”得以产生的深层原因:“道”本身所具有的内在而超越的本质属性和主体认识的主观性、个体性,以及“言”与“意”之间的不对称性;更以语言的“工具论”及其“寄言出意”的“诗意道说”的言说方式和“得意忘言”的诠释方法,不仅实现了对传统的“言尽意论”的解构和颠覆,而且实现了对由《老子》所发现的“言道悖论”的理性超越。而其作为《老子》“道论”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则不仅奠定了中国哲学“言意之辩”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开启了中国哲学“言意之辩”的思路历程。而其作为一种语言哲学理论和诠释学方法,则不仅对《易传》的“言不尽意”和“立象以尽意”的语言观和言说方式、诠释方法的理论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5〕,而且以此为契机更对魏晋“言意之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作为一种本体论的经典诠释方法和哲学范式的建构方法,则不仅对魏晋玄学本体论哲学范式的理论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6〕,而且对佛学的中国化〔7〕和宋明理学的综合创新〔8〕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而且对中国哲学范式的原创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余卫国.中国哲学范式原创建构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辨析〔J〕.安徽大学学报,2008,(2):8-13.
〔2〕杨国荣.道与存在之序——《庄子》哲学的一个视阈〔J〕.哲学研究,2006,(9):48-55.
〔3〕钟华.“言道的悖论”及其超越——《庄子》话语策略新探〔J〕.学术月刊,2006,(10):95-101.
〔4〕韩东晖.先秦时期的语言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1,(5):59-68.
〔5〕余卫国.《易传》“立象以尽意”思想发微〔J〕.周易研究,2006,(6):45-52.
〔6〕余卫国.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与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魏晋“言意之辨”缘起新论〔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1):42-47.
〔7〕余卫国.魏晋“言意之辨”与佛教中国化问题探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6,(3):18-23.
〔8〕余卫国.“言意之辨”的方法论意义与宋明理学的总和创新〔J〕.福建论坛,2005,(11):55-61.
(责任编辑:李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