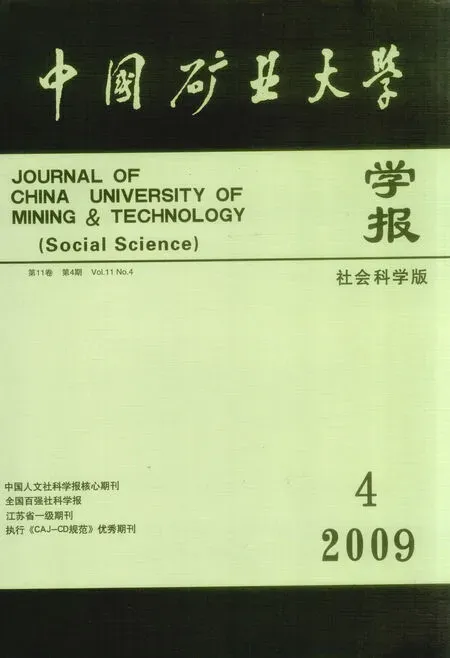作为修辞的第三空间
——兼论乡土书写中的空间样态
2009-02-09汪贻菡
汪贻菡
(天津师范大学 津沽学院,天津 300387)
作为修辞的第三空间
——兼论乡土书写中的空间样态
汪贻菡
(天津师范大学 津沽学院,天津 300387)
“故事背景”通常被认为是空间在文学中的主要存在方式,然除此之外,空间是否还有其他文学性存在?了解空间概念对于我们解读文本尤其是乡土小说能否提供新的建树?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本文从空间的分类入手,以经典文本为个案,从第一地理空间、第二想象空间、第三象征(修辞)空间三个层面,尝试解读空间在文学文本、尤其是乡土书写中的多样性存在。
空间;乡土小说;第三空间;想象;修辞
在影像艺术大面积覆盖、都市平面化浪潮的侵袭下,认识论领域的空间转向已悄然成为主流。而在文学文本当中,对空间的存在样态及其价值的探讨却不够充分。徐岱在《小说叙事学》中在关于景物的陈述部分,将空间的作用分为三类:故事发展的依据、人物性格的塑造手段和主题意蕴的昭示[1]。然除此之外,空间是否还有其他文本价值?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必要首先界定一下空间的类别。
较流行的空间分类,多以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的划分为据,他将空间分为空间实践(可感知的空间)、空间再现(构想的空间)、以及再现空间(生活的空间)三类[2]。该分类的本质仍然是物质/实践两分法,其创新点在于第三空间的提出,在索亚那里,该空间意味着一种开放性的反省世界的方法,囊括了一切边缘、异质和充满乌托邦色彩的存在。虽就笔者所搜集的资料看来,这种划分尚未被有效运用到文学空间当中,然而我们不妨做一个尝试:即以索亚的分类为参照,在对文学作品空间样态的探讨中获取我们的文学空间层次;该层次肯定会有与索亚重合的地方,但前提是,我们的分析对象截然不同。
一、作为背景或主题
(一)作为背景的第一地理空间
所谓第一地理空间,指的是文学对现实的临摹,是物质化、可感知的空间,该空间在文学中是注定存在的,是主体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前提:“人要有现实客观存在,就必须有一个周围的世界,正如神像不能没有一座庙宇来安顿一样”[3]。第一地理空间与时间一起,构成文本创作固有的时空坐标。该空间常以静态描写方式出现,并被赋予国家、城市、街道等名称;在18-19世纪欧洲自然主义小说当中,可充分领略作家对该空间的重视。而诞生自该空间的人物言语、服饰、习俗礼仪、人文氛围等,均作为该空间的精神文化标识而存在。
在不同的作品中,第一地理空间存在的意义是不同的。我们习惯于将之统称为“背景”。作为时间沉淀的结果,空间以时间标记物的方式展示了历史的更迭与欲望的沉浮,并带有特定的文化象征意味:无论是施蛰存的旧上海、老舍的北京、汪曾祺的大淖乃至韩少功的湘西蛮荒之地,无不以鲜明的地域性而著称,并因此影响到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文化情调,空间自身的美感更是能够增添文本审美效果的催化剂。当地理空间大致相同,叙述主体的差异性就凸现出来了,种种富丽人性的存在,使空间从历史的平面上耸立:绍兴便不仅仅是鲁迅所述充满落后、愚昧、残杀和看客的旧中国农村,它一并是周作人笔下温柔的江南水乡,生产着美味的豆腐干、点心和瓜子,积蕴着温文尔雅的士大夫文化。这种差异不仅源自创作个体的视角差异,同时还源自裹挟在作家心灵深处的时代与文化印痕的不同。
(二)作为主题的第二想象空间
所谓印痕,意指一种秩序。《说文部首》曰:“空,从穴、工声。穴,土屋也,是古人遮风挡雨、安身立家之所。”[4]对于古人而言,时间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不可把握的存在,是古人生命无归、命数无常感觉的根源,在对逝者如斯的永恒恐惧中,空间以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时间去而不返的苍凉相对峙,人类得以在空间中建构家园,遮风挡雨。未来遂是可掌握的,宇宙之大茔然掌中。
空间作为时间的稳定,依赖的正是一种秩序,包括政治制度、文化惯例、礼仪风俗等等,可在封闭的空间中相对稳定地繁衍一段历史。由此看来,汪曾祺的大淖与沈从文的湘西,抑或贾平凹的商州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其差异性正是不同地理空间秩序的千差万别,并因此成为故事发展和人物性格塑造的依据。以沈从文为例,正是边城的青山绿水养育了翠翠的一双眸子清明如水晶,亦是那空濛寂静的玉家菜园才使得玉家母子氤染了林下之风。而同为京派文学的大家,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共同之处正在于,他们似乎总是立于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忽视历史弃旧迎新的残酷,人物受着静态空间里真善美的稳定秩序所支配,以非暴力的方式处理人生各种层面上的尴尬。
而此时的空间描写,已不仅仅是作为背景存在,它还应当是作品描写的主题本身。也因此王安忆《长恨歌》之“恨”,恨的是王琦瑶偏偏生在繁华与堕落并存的上海。她的美丽如果和翠翠一样静静地绽放在山涧,一辈子便也罢了;可却偏诞生于上海、诞生在上海淮海路的弄堂里。也只有这样的弄堂——拥有鸽子、闺阁和流言;拥有逼仄的小巷、高高的阁楼;阁楼的老虎天窗上反射着夜幕下的霓虹灯——才可能诞生一批美丽、安静又绝不甘于安静的王琦瑶们。
在乡土书写中,从背景到主题,界限往往并不清晰。空间秩序一旦上升为描写主体,则空间就不仅是背景,而以精神文化空间的方式,影响着整个文本。该空间只存在于人物的精神想象和读者的阅读想象当中。而当空间作为主题时,文字便往往随空间一起凝滞、心灵因为有归宿的安静而使节奏也缓慢下来。乡土叙述的田园气息可能正源于此吧。然而此时,时间便常常要跳出来,与该主题发生冲突。
二、时空矛盾中的城乡对峙
空间意味着稳定,时间意味着前行,在时间潮水的冲刷下,空间的稳定却往往不堪一击。也因此,《长恨歌》之恨,恨的还是王琦瑶错误地把变动不居的空间与流水般逝去的时间相重叠,因此做了时间的祭品:王琦瑶沉浸在富贵温文的布尔乔亚气息里,走过了国共战争、文革和改革开放三个标志性的历史时间,经历了程先生、毛毛娘舅、老克腊等不同时代的男性,她却始终生活在1949之前的那个空间当中,怀念着她身为“上海三小姐”时候的一切风光、谈吐、穿戴和吃喝;在消费主义肆虐的新上海空间中,她却暗自憧憬着历史可以重演,以为空间标记物可以唤回失去的时间,以为美在不同的时空秩序中的标准是同一的;甚至,她因此不曾获得一次真正的爱情,她无非是以她对过去时空的执着,成为一个又一个男人怀旧的祭品。在被时间潮水冲刷的面目全非的新都市空间里,固执的王琦瑶风化、干枯、长恨而去。无论是张爱玲还是王安忆,她们笔下的人物(多数是女子,因为女子更容易回忆和标志一个时代),总是渴望在历史演绎的大悲怆和青春匆忙的大凄凉中,抓住空间影像作为历史洪水袭来时候的支柱,却又终将伴随那支柱一齐轰然倒塌。时空的相悖性是必然的,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因此关于第一地理空间和第二想象精神空间的怀旧情绪绵绵不绝地滋生着。
与这种封闭空间中的自我挣扎不同,近年的乡土书写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到介入城、乡之间的人群存在。在乡土书写中,城市与乡村是永恒的矛盾。乡村秩序偏向于时间,强调习惯、传统和连续性,土地和田野的大面积覆盖给人以归属感和安全感,但也因此成为保守、愚昧等精神囚禁的代名词;都市秩序则偏向空间,充斥了快速传播的媒介、分割天空的高层建筑和逼仄的情感欲动,求新求异带来历史时间的快速后撤,都市遂成为平面化、碎片化的不稳定存在,失去历史的人们同时失去自我,深度模式成为笑谈。此时,置身于时空一体当中的人们,便会一边在新的都市空间中质疑旧的乡村秩序的落后与不文明,一边对即将逝去的粗糙和原始的秩序一咏三叹;因此乡村总是被作为寻根的对象,充满回归和怀旧气息。与此同时,城市文明作为乡村文明进化的产物终将吞噬后者,因此关于乡村的书写便在怀旧之外,又带上一种注定要消亡的悲怆气息。
贾平凹是持续关注城乡叙事的当代作家,从80年代中期的《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到《腊月正月》,对由农村到城市、又迁衍至农村的改革开放,贾平凹一度是热烈欢迎的。但从80年代末期的《浮躁》开始,他更多地将笔锋转向了乡村在改革过程中的道德沦失和灵魂焦虑。往小了说是《浮躁》中金狗的精神挣扎,往大了说亦可诞生如《废都》中庄之蝶般失去灵魂归宿的肉体颓废。而在其新作《秦腔》中,从都市中疲倦归来的夏天智,却陡然发现一度作为身心归宿的乡村也早已不复是田园牧歌的存在。归宿没有了,这群因不满于乡村禁锢而向外寻求新鲜血液的空间突围者们,由此成为介于都市和乡村之间的流浪者。
该流浪者形象充斥了现代中国的乡土书写。从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到苏童《米》当中的五龙,再到《秦腔》里的夏天智,乃至《高兴》中的刘高兴,他们都属于失去农民身份、又尚未(或永远无法)获得市民身份的尴尬进城者。城市和乡村分别裹挟了各自的空间秩序和历史记忆,如果说在祥子、五龙和金狗那里,还存在两种秩序共存导致的焦虑与斗争,那么在夏天智和刘高兴这里,却因同时失去两者、失去历史记忆和生存空间,而成为双重失落的城乡之间的“第三者”。他们所生活的城乡交叉地带、如今更多的是“城中村”,便也成为介于城市与乡村之外的“第三空间”。该空间的物质实在性不可受地理学考证,亦尚未构成某种具有影响力的精神文化空间,这里是遗失和边缘的交叉地,充满了不可解释的矛盾。这类难以用既有概念来解读的空间存在,我们习惯赋之以额外的寓意。而在文学的空间视野当中,我们可试着将之命名为一种“异度空间”,也即接下来要进入的、作为修辞的第三空间。
三、作为修辞的第三象征空间
(一)第三空间与“阿列夫”
第三空间在索亚那里是个暧昧的概念,它既非物质的亦非想象的;在该空间里万事万物都得以聚集:主体性和客观性、真实和想象、心灵和身体、意识和无意识等等,一切都尽收其中,像一个不可思议的宇宙。这个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综合体,被索亚用来指称介于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之外的那些含混不明的存在,并用“阿列夫”来命名这种存在。
“阿列夫”出自博尔赫斯一部短篇小说,它是一个“微小得明亮得让人无法逼视、泛着五彩光晕的小珠子。世界上所有的空间都在里头”;从伦敦残破的迷宫到非洲黑金字塔中心银光闪闪的蜘蛛网,从隆起的赤道沙漠到孟加拉一朵玫瑰花的颜色,甚至“你暗红的血的循环、脸和脏腑”[5],都能看到。在一片眩晕当中,博尔赫斯不忘提醒我们,所有场面都是同时发生的,然而他记叙下来的却有先后,因为语言有先后。因此阿列夫是一个共时性空间,其命名出自希伯来语的首字母,它意味着一切语言—历史—意义的源头。博尔赫斯还提到镜子,他说这个泛着五彩光晕的小珠子阿列夫就像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反映了整个宇宙。
镜子—阿列夫—第三空间,如果这个联想式成立的话,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第三空间对于文学的象征意义。它们的相似性在于并不改变世界,虽然内容芜杂,却透明地折射了一切存在,从而成为一个彻底开放的空间:主体/客体、真实/想象、肉身/灵魂等等一切异质的对立物并存于这个开阔地带。该空间部分具有索亚式的颇具乌托邦色彩的调和主义,然在积极的意义上,二元对立中那些比较式微的部分也因此获得了表述自身的可能:因此女性、黑人、同性恋、被殖民者等等一切具边缘色彩的存在,得以挺身进入公众空间。
以阎连科《日光流年》为例:该作品讲述了中国华北偏僻的耙楼山脉一个叫三姓村的地方,因水土问题罹患“锁喉症”的村人,在司马蓝等四代村长的带领下为活过40岁这一理想而展开的种种抗争。该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不仅是村人顽强的生存意志,更是三姓村令人窒息的孤独、荒凉和自我封闭。为争取生命时间的延续,在封闭的空间里长达百年的挣扎,既得不到来自外界的科学或情感的援助,亦竟未想过走出去寻求援助。以中国之大,如此般挣扎在生死仪式上的病弱存在,无法迅速地被纳入国家视野并获得救助,公益慈善的乏能和信息传播的滞后令人触目惊心;而另一方面,一切外界文明的进入却均以敌对或效果相反的面貌出现,按照原始道德秩序生存的三姓村,固执地抵抗文明背后的黑暗和漏洞,也一并阻挡了一切秩序变革和空间开放的可能。在亘久的城乡对峙中,华北版图上无证可考的“三姓村”超时空的道德乌托邦意味格外鲜明。值得一提的是,在固守贫穷和愚昧的同时,三姓村的人们却从未放弃过对权力的疯狂攫夺。于是在阎连科笔下我们看到了两种对峙:城乡对峙,以及乡村内部缺乏道德反省与超越的自我对峙。在双重对峙中,司马蓝们恪尽性命的努力,遂被扭曲为一种颇富民族精神的、兼具仪式和游戏意味的徒劳。
可能这并非阎连科的本意,然而他的确贡献了一种异度空间的存在,该空间不具地理意义,精神文化影响亦未成形,解读它唯有进行超越空间的象征性思考。依此思路我们对“城中村”的解读便有据可依了。那些居住在城乡交叉地的进城者们,由于农民和市民的双重身份失落,与土地和城市的关系都是紧张的。而在第三空间当中,紧张是一种恒在的气氛,是由身份不同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差异,或者说是由于所处空间及空间秩序的差异等矛盾所造成的。
在残雪的空间文本当中,该矛盾俯首可拾。无论是黄泥街还是山上的小屋,人物形象的丑陋、行为的怪诞、感情的虚伪、关系的脆弱,构成了这个失去地理归宿亦无审美结构可言的变形空间;或者反过来说,正是这种充满压迫感的空间,让人物和事件扑朔迷离。在残雪的作品空间中,没有历史、没有地域、也没有社会;滚滚而来的是不知缘由的怒意和伤害,缓冲地带在她的作品里是不存在的,也唯有梦境和虚无才能够支撑起这个混沌、无秩序、无理性的空间[6][7][8][9]。在长久而持续的伤害想象中,残雪依据的正是现代中国的社会与精神构图,建构了一座文字的庞大城堡,居于第三空间之巅,发出幽冷、凄厉的呼啸声。从时空角度来看,这是难以解释或靠近的城堡;可若作为第三空间,那无非是折射在万象重叠的阿列夫宇宙中极其昏暗而刺眼的一小部分、是光亮的背面、是机械复制时代被摒弃于万象之后的权力运作和历史强迫力量的产物。其对灵魂的吞噬性绝不容小觑。
这里我们发现,这种作为修辞的第三空间,不仅仅存在于乡土书写当中;无论是阎连科充满洪荒之气的耙耧山脉、还是残雪那总在狂风呼啸的山上的小屋、以及卡夫卡陷于荒野深处的城堡、乃至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中的银白色星球——在一切具象征性的作品中,该空间均可借助想象而存在。
(二)作为修辞的第三空间
近年来,“想象”越来越成为学界流行术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海外学者王德威,他将文学和电影视为对中国现实的“想象”,并提出“小说中国”的概念,该概念强调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国家的建立与成长,少不了鲜血兵戎或常态的政治律动。但谈到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我们不能不说叙述之必要,想象之必要,小说(虚构)之必要。”[7]有评论说王德威明显有将小说上升至“大说”的野心,然若考察作家创作的精神轨迹,就会发现该“野心”并非王德威有意上升之,试图通过文字介入并记录国家命运与社会生活的情感历程,是潜藏在无数作家心中涌动不息的暗流。而裹挟在这暗流当中的乡土或都市叙述,便背负了建构意识形态批评的重大责任;不同的土地分别被赋予了首都、家园、“飞地”、改革开放重镇、道德淳厚之邦等公共身份,历史地理与文学想象紧密勾连,遂使得上述作为修辞的第三空间,在作为主体言说对象的同时,一并体现着主体对于言说方式有意识的选择与运用。
于是恰如霍米·巴巴所言,这种存而不在的第三空间,实质上成长为一种干预文化批评的力量,在阐释的行为中引进了一种矛盾性,也即引进一种重新评价、分割与差异的意识形态基础。本来,世界有很多重,而这多重世界的冲撞、重叠与交融,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由此,巴巴提出了“既非这个也非那个”的“第三空间”概念。该概念是一个被书写出来的模糊混杂的空间,是由“杂糅性”(hybridity)策略开辟出来的一块协商的空间,“它颠倒了殖民主义否定的后果,使他者‘被否定’的知识进入支配话语,并离间了它的权威的基础——它的肯定的法则。”[8]在这个“居间”(in-between)的杂糅空间里,文化本质主义的霸权遭到挑战,中心/边缘的严格分野被质疑;而双重视角(double vision)的存在,则赋予“真实”新的内涵。而作为一种思考性的干预力量,第三空间的象征性意义便豁然凸显:与第一、二空间并存,从而让对方认识(而非认可)自己,并有机会对话。如果说,作为背景的第一地理空间和作为主题的第二想象空间分别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载体,那么作为身份修辞的第三审美空间,则是对社会权力关系加以文学想象的结果。该关系并不是凌空存在,它依托于地理空间、以精神空间的方式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
比如说如果我们跳出城乡对立,单从文学发展自身的倚重来看,便会发现当多数学者将乡土书写作为百年中国的主流书写的同时,都市文学在乡土中国的生长便不可避免地十分困难,乡土文学的强力挤压、城乡对立的思维方式,无不是把诗意礼赞送给乡土,将异化欲望的责难留给都市。而在对都市文学的考察当中,关于上海、北京、香港等城市的想象性解读基本成为学者关注的全部热点,但很显然,仅这三座城市决不能代表全部的“小说中国”。不仅如此,从性别对峙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自鲁迅开始,男性便霸占了乡土叙事空间主导者身份,而女性则更多地蜷曲在都市逼仄、扭曲而黯淡的空间当中,担当着被想象、被检阅和被消费的永恒主角。广阔天地里的女性生存不仅是匮乏的,也终究是艰难的;即便是在声称为自己言说的女性写作当中,却通过事业与家庭、理智与情感冲突的再三展示,将女性生存与书写的狭小悲哀淋漓尽致地透露出来。当乡土书写出现在流散作家/移民作家、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们的笔下时,则更具有了超越国家的民族精神的凭吊之意。福柯说空间是权力的容器,我们和文学一起,深陷在这个容器当中,绝无出路。而作为道德想象、性别优势、家国象征等不同文化与权力的永恒的角逐场,第三空间的存在意义自此便超出文学本身,与修辞紧密相关。
而当我们考察修辞的历史就会发现,修辞是一种行为、而绝不只是文学手段,其意义在于传达词语的力量;在主体平等的第三空间里,这种词语的力量不一定是说服,而是说明和交流。同时,修辞学昌盛的时代,正是古罗马尚未被长老制所垄断的时代。这意味着当民主陨落时,作为行为的修辞学必将不复存在;同样意味着当第三空间以想象的修辞方式介入公共言说时,会给读者带来超越二维时间之外的延伸思考。空间的延展性在这里获得了一种优越感:时间是单线的,空间却具有平面联系性,其横向综合的意图正弥补了线性时间所致的封闭;从某种程度上说,时间的纵向联系或曰历史只对个体、国家有效,空间则具有公众性,对群体和世界有效。以群居方式生存的人类,需要主体平等的空间以并存和对话。而唯有在拥有不同身份和不同意识的对话当中,自由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互联网时代及网络文学的不可抗拒,或许正在于它营造了一个共时性对话的无限空间。
当然,按照朱大可的意见,公共空间本身也存在着理论意义上的不同级别,作为有限的意义空间,互联网平台尚未彻底改变国家叙事的笼罩,以及民众意见多染有暴力色彩乃至自我抵消等特征[9]。但是互联网平台作为某种“第四空间”的存在,对意见空间的未来走向肯定是有着微妙而深远的影响的,而至于网络空间对文学的多重影响,则是另一个话题了。
[1] 徐岱. 小说叙事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68-273.
[2] 索亚. 第三空间:航向洛杉矶以及其它真实与想象地方的旅程[M]. 王志弘,张华荪,王玥民,译. 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87.
[3] 黑格尔. 美学[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12.
[4] 申志均. 说文部首字典[Z].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116-117.
[5] 豪·路·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全集[C].王永年,陈泉,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306-307.
[6] 近藤直子. 有“贼”的风景——读《苍老的浮云》[J].廖金球,译.山花,2001(2).
[7] 王德威. 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M]. 台湾: 麦田出版有限公司, 1993:4.
[8] 转引自王斐. 华裔美国人的第三空间身份建构[J]. 温州大学学报, 2009(3).
[9] 朱大可.意见空间的文学丑角[J]. 江苏社会科学, 2008(6).
收稿日期: 2009 - 09 - 07
TheThirdSpaceasRhetoric——Space in Contemporary China’s Local Novels
WANG Yi-han
(Jingu Colleg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
Background is alway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common way for the existence of space in literary works. While is there any other way for space to exist?Is there any new contribution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 especially for the local novels,if we understand more concept of literary space? So far all of these questions are still unanswered. Here we’ll start from the classification of space and divide it into three categories,the first category is the geographical space, the second is the imaginative space and the third is the rhetorical space, with which we would gain more illustrations of those classic works.
space; local novels; the third space; imagination; rhetoric
2009 - 07 - 05
汪贻菡(1982-),女,文艺学硕士,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文学系助教。
I054
A
1009-105X(2009)04-01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