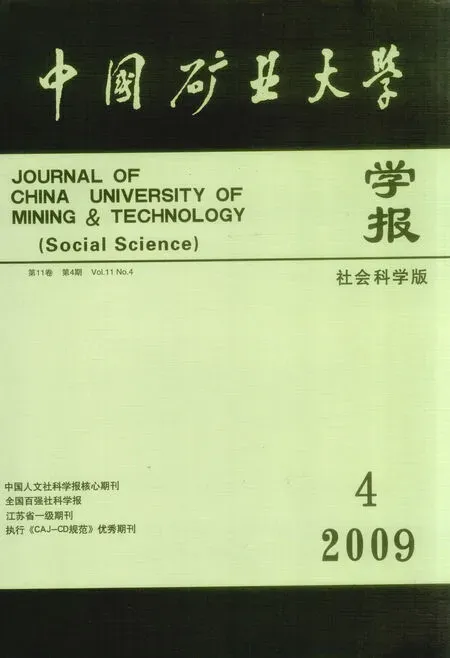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话语对后殖民批评的介入
2009-02-09朱述超
朱述超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马克思主义话语对后殖民批评的介入
朱述超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全球化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事实,也是理论家们所持续关注的领域。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如何有效介入后殖民批评都值得思考。在具体的实践中,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观在后殖民批评中引起多方面的强烈反响。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对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学状况仍有启示。
马克思主义;后殖民批评;詹姆逊;第三世界文学
一
后殖民主义批评是一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成话语,它主要研究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权力身份等问题在后殖民语境中的新面目[1]。作为一种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批评,它与马克思主义在议题上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事实上,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也是其一贯立场,马克思从经济角度批判了殖民地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提供”销售市场,而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又通过对市场的垄断加速资本积累。并且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揭示宗主国对殖民地国家的被奴役的人民在文化心理上的控制。而后者成为萨义德展开其“东方主义”的切入口,在其《东方学》中,萨义德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作为卷首扉页。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批评家却抱着一种十分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十分欣赏马克思主义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常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引用,有的后殖民批评家更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毫不讳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反感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的“普遍主义”,作为他们力图摒弃的“主导叙事”。因为在后殖民批评家看来,“当马克思主义者将殖民主义的罪恶昭示于众时,他们的批评总是限制于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产方式的叙述”(普拉卡什),而保存了资产阶级的目的论假设[2]。因此,赛义德认为像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尽管具有“对人类不幸的同情”的“博爱情怀”,依然不能解答“对正在遭受社会急遽变革之痛的东方人天生的反感与这些变革的历史必然性二者之间进行调和的难题”,“终占据上风的却依然是浪漫主义的东方学视野”[3]189-199。霍米·巴巴也借法农之口说出“与殖民地状况更切合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主奴辩证关系的解读方式,而是对立的、有差异的拉康式的‘他者’方式”[4]。
二
那么,在后殖民经济全球化语境之下,马克思主义真的毫无用武之地了吗?不少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认为马克思把所有的社会关系归结为经济关系,是一种过于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或经济简约主义。但是女学者斯皮瓦克则对马克思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所确立的二元深感兴趣。在她看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二元依然适合用来分析华尔街的繁荣,欧美大学教育的领先水平以及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与第三世界的工厂和乡村之间长期被忽视的内在经济联系。因为单纯的文化研究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触及帝国资本主义的本质,相反文化往往掩饰了帝国主义资本积累的血腥事实。因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拉克劳(Laclau)、沙米尔·阿明(Samir Amin)、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也同样认为,修正马克思的关键概念没有充分理由。在第三世界残酷的劳动条件下工作的女工和童工都非常痛苦地证明,马克思19世纪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今天的经济世界仍然相关[5]。这正好为后殖民理论家奠定了知识和政治框架。因此罗伯特·扬认为,后殖民主义批评本身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只是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而言有所偏离。对许多第一代后殖民理论家来说,马克思主义都是他们的起跑线和理论基石:“如果说后殖民理论是殖民化的一个文化产品的话,那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反殖民领域的一个历史的产物。”[6]如果仔细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里有关价值的讨论,那么就会发现,是工人生产了资本,工人生产资本的原因是工人——劳动的本身,就是价值的源泉。依此逻辑,在国际劳动分工日益明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出:是第三世界生产了世界财富,并使第一世界文化自我再现成为可能。19世纪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对立,20世纪则是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之间对立。19世纪,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榨取剩余价值获取财富;20世纪,第一世界剥削第三世界攫取巨大的商业利润。对这种对立关系的忽视以及对国际劳动分工的无视将会使得西方的繁荣,教育的发达与西方对第三世界多种形式的持续不断的剥削和控制,得以以各种方式存在和发展下去。由此,斯皮瓦克从后殖民视角重申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全球化时代的阐释力量。关于斯皮瓦克的详细论述在此不做赘述。
三
如果将视野转向具体的后殖民文学与文化批评上来,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了被称为后殖民批评思想先驱的一批作家,如赛萨尔、法农、阿切比等人,并且在当代所谓后殖民批评代表人物身上刻下独特的痕迹。赛义德明确地运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作为批评武器:“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3]9-10斯皮瓦克的《属下能说话吗?》中的“属下”(Subalternity)一词,也来自葛兰西,并且她的理论始终在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灵活穿越。此外,对本雅明、阿尔都赛、雷德蒙·威廉斯等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概念的运用,在后殖民批评中也是相当普遍的。无论是从政治实践还是从理论研究方面来看,没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批评今天的面貌都是很难想象的。不仅如此,杰姆逊、艾贾兹·阿赫默德、阿里夫·德里克等马克思主义者更是积极参与了后殖民批评相关议题的讨论,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中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更是引起了极大争论。
杰姆逊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基于“冷战”后期的国际政治格局。他申言是在批判的意义上采用这一术语的,只是没有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来“表明在资本主义第一世界、社会主义集团的第二世界,以及受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其它国家之间的根本分裂”[7]。促生“第三世界文学”概念的当代语境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伴随着跨国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西方文化霸权的激烈反应。在他们的话语中传达的是对“我们”这一集体身份的关注,对自身民族特性的深情眷顾,和对民族国家意识令人迷惑的复归,这从一开始就隐寓了概念本身的规定性:“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学所称的独立部分和自主的文化”[7]。它的充分的自律性仅存于成为当代这个文化总系统的构成之前,它注定要在与第一、第二世界文学或文化的某种相对关联中确定自己独特的位置,也就是说它必须接受来自”他者”文化的他律性—— 一种自上向下的俯视。这导致了这个世界文化图景的对抗性[7]。对抗性的历史情境一方面更为紧迫地呼唤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解和阐释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营造了一种共时语境的氛围,抹擦了第三世界不同的民族文化因演进环境造成的复杂多变的差异的历史轨迹。三层等级结构的世界文化格局简约为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应。借此,杰姆逊激烈地批判了第一世界文化以欧美文学为中心为典范的偏狭视域。通过对“异己读者”(The other reader)的阅读视野的提示,杰姆逊展现了横亘在第三世界的非典范性文本与第一世界阅读者之间的巨大的审美差异和个性距离。规范视域的偏狭即掩饰了不同民族社会生活的根本差异性,阻碍阅读者的阅读范围和阅读方式,抑止审美愉悦的多样性。对第三世界文本的“他性”的漠视恰恰提示着第一世界文化自身的匮乏。究竟第三世界文学的“他性”内涵是什么呢?杰姆逊在小心翼翼地提示了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差异之后,大胆地认定“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可以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7]。
为了支撑这一观点,杰姆逊特意举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著名作家的作品为例,阐明这些不同文本是怎样与本民族的历史经历、政治意识乃至经济状态谐和一致,个人的奇特经历和命运怎样内在地展现出民族的心灵。应该看到,杰姆逊对“民族寓言”这一概念的使用并非心血来潮,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政治无意识》等重要作品中,都论述了寓言问题。归根到底,这与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分析分不开。在西方文论界看来,任何马克思主义式的阅读从根本上说都是寓言式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把文学性文本视为纯粹的文化产物。无论从作品到读者的接受来看,还是从作者为读者而创作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都要求凸显一种目的性:作品要有意义。而寓言的设言托意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杰氏的理论激起的反应是多方面的。在美国,这一理论在一些年轻学者,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移民学者中流传。关于第三世界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多方位的展开,并逐渐形成一股潮流。
在中国,一些学者也纷纷著文讨论,响应这一理论。中国文化的第三世界处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等问题被重新考虑。中国文学被放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不平等的文化权利关系中加以审视。一定程度上说,杰姆逊的观点成为中国后殖民批评的重要理论源头。其以第一世界读者与批评家的身份解读第三世界文本,从文本的民族寓言意义确定文本的价值,确立了一种新的解读视域,对于匡正第一世界审美典范视域的迷误是有益的。
但它同时遭到了来自第三世界最激烈的批评。这就是同样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印度学者艾贾兹·阿赫默德。他首先认为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概念在认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我接触到杰姆逊所描述的实质内容时,我发现极其重要的一点在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是以它们的生产制度(分别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定义的,而第三个概念——第三世界,是纯粹靠对此外来插入的现象的‘经验’来定义的。在前两个概念中可以看出人类历史的构成性因素,但是在第三个概念中却缺乏这些东西。”[8]这样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被描绘成创造与被创造、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第三世界的定位变得殊为困难,它是处于前资本主义、或者只是一个过渡?很不清楚。像印度、巴西、墨西哥、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很难归入这样的三个世界模式,实际上第三世界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依据。阿赫默德进一步指出,杰姆逊通过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将第三世界文学统统归结为“民族寓言”也是不恰当的。一方面,历史地看,亚非拉各国从未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那样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的文化产品的流通也从来没有如欧美国家之间那样直接、广泛、便捷,因而不可能分享那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验”,而各具特性。恰恰在杰姆逊强调文化差异性的地方,他的理论走向了对立面——同质化(homogenization)的方向。另一方面,“文学文本是以一种高度差异化的方式写成的,通常受多种相互争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的决定,因此任何一种复杂的文本,在它被总体化为一个普遍性的范畴之前,一般都得产生在为它提供能量和形式的语境群之内”[8]。因此杰姆逊的做法将文学创作的制约力量简约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因素,违背了基本的经验事实,实际上寓言性的文学作品常常突破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界限,在世界各个地方出现。以“民族寓言”为基本特征的“第三世界文学”概念的可操作性是令人怀疑的。
稍后,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也否定了三个世界的划分。他一方面认为“第三世界”作为一种情愫的确应不断地发挥作用,“以对抗第一世界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文化霸权主义倾向”[2]。但基于新的历史事实,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原有的第三和第一世界的内部不断分化:一些早先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今天处在跨国资本的通道上,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发达部分;而原来的部分第一世界国家已在新的全球经济格局中被边缘化。因此,“三个世界的划分,不管是地理位置上的还是结构上的划分,也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阐述,的的确确都已不再站得住脚了”[2]。他同时指出,“后殖民”就是一个试图取代“第三世界”的术语,但是由于它本身的歧义丛生和重大局限,又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替代。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当前的文学状况,马克思主义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四
值得注意的是,杰姆逊是在“世界文学”旧话重提的情况下思考“第三世界文学”的。阿里夫·德里克在分析了当前的全球状况后指出:“跨越民族、文化、性别和种族界限,实现真正的世界主义的希望,正在以它自身的魅力吸引着人们。”[2]也许,思考一下马克思对“世界文学”的论述对我们把握当前文学的势态仍然是有益的。“世界文学”概念由歌德明确提出,并终于在马克思、恩格斯手中发展成深刻的学说。马克思对“世界文学”形成的判断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物质生产的世界性最终决定了精神生产的世界性,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共同财产正是有赖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并随着商品的流通而流通。这既是一个破坏性的进程,更是一个进步的发展过程,非欧洲的地区必须付出沉重的必然的历史代价,消灭本身的片面性与局限性,以趋近进步与文明。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必须历史地把握意识形态下的生产方式的现时状况,进而理解精神生产的实质。生产方式的现时状况是资本主义仍然在全球体系中起着基本作用,并且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杰姆逊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已经实现。不仅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已经全球化,而且,生产的国际化规模和趋势日益扩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综合化的跨国公司和多国化的高科技企业。由于金融资本在全球的灵活穿越,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制造资本主义的新起点,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的轨道而非中心化。“生产的跨国性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统一,也是前所未有的分裂的根源。”[2]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发现它在文化领域制造了一个合理的悖论:他为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也使这种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它为文化工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消费群体,也引起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无尽缅怀。同一性和多样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艺术吁求被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共存奇妙的并置在一起,形成当代独特的文化景观。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任何单维度的思考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进而,它揭示出一种整体性把握的必要性。虽然“整体性”被后殖民批评家视为本质主义的陈词而嗤之以鼻,但整体性观念的抛弃导致分裂的零散化叙述的扩散,使后殖民批评无法建构一种整体性的历史观, 从而难以解决
现实面对的全球文化关系问题,在反本质主义的空中楼阁里迷失方向,并“反过来加强了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2]。这从反面揭示了完全抛弃整体性的不可能,使我们严肃思考马克思主义面对后殖民主义议题分析的有效性。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西方文化霸权的权力是构筑在资本优势基础上的。资本分析的有效性提供了整体性把握的认识论基础。由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运行导致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并置,民族的或区域的文学与世界文学不应视为等级性的结构区分,而是出于不同研究视角的互相联系的两个概念,因而也必须相互联系的分析。从而世界文学不应看作是各民族、各地区文学的简单相加,而应看作各个文学体系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不断流动、互相制约的现象。“世界文学”的认识提供了一个理论支点,从较宏观的层次来透视各民族、各区域的文学,并探寻它们相互流通、转化、制约的深层物质根源。虽然文学受到环境、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但生产方式的转变将最终使各民族、各社群的文学发生转变,并导致世界文学的可变性。因此,马克思时代有马克思时代的“世界文学”,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也应有晚期资本主义的“世界文学”。
[1] 蒋天平,段静.文化霸权下的近代中国翻译[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
[2]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的辉光: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J].国外文学,1997(1) .
[3] [美]赛义德.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198-199.
[4] [美]霍米·巴巴.献身理论[M]//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94.
[5] Stephen Mort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Routledge, 2002:93.
[6] Robert Young. Postcolonialism: A HistoricalIntroduction[M].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167-168.
[7] [美]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M]//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32-235.
[8] [美]艾贾兹·阿赫默德.詹姆逊的他性修辞和“民族寓言”[M]//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38-353.
InvolvementofMarxistDiscourseinPost-colonialCriticism
ZHU Shu-ch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Globalization becomes a field that theorists have continuously focused on. In this contex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post-colonialism, and how Marxism effectively gets involved in the post-colonial criticism is worth reflection. In practice, Jamson’s”The Third World Literature”evokes great repercussions in postcolonial criticism.
Marxism; post-colonial criticism; Jamson; third world literature
2009 - 10 - 28
朱述超(1979-),男,四川大学2008级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A1691
A
1009-105X(2009)04-0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