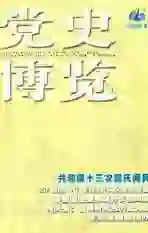零距离感受陈毅外长的风采
2009-02-03李景贤
李景贤
毛泽东“布子”,陈毅踌躇
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部长一职由周恩来总理兼任。但他的政务活动过于繁忙,他这个人又举轻若重,事必躬亲,劳心、劳力、劳神。大约四年过后,毛泽东同志为减其负,萌生出“外交换帅”的念头,并暗中“布子”,将其锁定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陈毅身上。在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心口中,陈毅人才难得,政治上强,既有战略头脑,又有外交才华。1954年秋天,陈毅从上海市长的岗位上被调到北京任副总雕,他预感到将要接任外交部长一职。
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毅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副总理的分量明显加重,由他兼任外长,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不过,陈毅并没有立即挑起这副重担,这里面事出有因。当年他在西藏考察时,因高原反应而头疼不已,返京后不久,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一次电影招待会上,陈毅突然晕倒。之后,他便向中央告假,疗养了一年。1958年2月,陈毅副总理才开始兼任外长一职。
面对毛泽东亲自点将,一向心胸坦荡的陈毅曾一度忐忑不安。他这个人有自知之明,对能否挑起、挑好外交这副重担。心里没底。一是因为,作为新中国首任外长的周恩来,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多年,被公认为全世界罕见的外交全才、奇才,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二是因为,陈毅深知自己有一个好感情用事的毛病,觉得这种不良习性对一个外长来说是敛命的,担心会因此“砸锅”,误了党和国家的大事。
在接过外交重担之前,陈毅曾坦荡荡地推辞说:“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对夫人张茜,他说得就更直:“我这次兼任外长,可能有四种结果:第一个是干出成绩,第二个是一般化,第三个是犯大错,第四个是得大病。”
陈毅在中国外长这一岗位上名义上工作了十三四年,直至1972年辞世。但是,在“文革”开始后,他就逐渐被非法剥夺了工作的权力。在只有七八年的“有效工作时间”内,这位元帅外长,在国际大舞台上,与周总理一样叱咤风云,为新中国外交立下了赫赫战功,赢得了他所预期的第一种结果。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人们更多看到陈毅外长“立马横刀”那刚性的一面,但他的才气、文采、风趣、人情味,他的人格魅力,电常常为知情者所称道。外交部的人都亲切地管他叫“陈老总”。1963年8月,我进入外交部工作后,曾有幸为他当过俄语翻译,还有机会在许多场合零距离目睹了这位元帅外长的风采。如今,40多年过去了,敬爱的陈老总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
铁骨铮铮的元帅外长
1965年秋天,亚洲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毛泽东提出,清陈老总出来向中外记者讲一讲。当时,陈毅正在外地,得知主席这一指示后立即往同赶,在回京的火车上,就开始紧张地准备起来。
陈毅同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即9月29日,就举行了一次大型的中外记者会。外交部翻译处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五大语种都派出了超一流的高翻去进行同声翻泽,领导让我也到“前方”去体验和学习。
那一天,偌大的一个会场被三四百人挤得水泄不通。答问时,陈老总训到了十五六个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他几乎都是即兴讲,时而阔论世界大势,时而推挡刁钻的问题。在没有多少时间进行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记者们所捉各式各样的问题,陈老总镇定自若,对答如流,滴水不漏,足见他刈囤际大势、国别关系与中国对外政策之精通。
这次记者会持续了近两个半小时,面对美国人的战争威胁,陈毅横眉怒目,发出阵阵吼声: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善存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
陈老总的话音一落,在场的所有中国人立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人们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激动和振奋之情。老元帅在“一切都报”这句老话后面特意加一个“销”字,加得实在是妙:总有一天,会把世界上所有的“害人虫”统统都给“报销”掉!
2008年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的大型专题片,其中有一组回顾周恩来同志与陈毅同志兄弟、战友情深的镜头。我看着看着,没想到荧屏上出现了上述记者会的画面。而且,还对陈老总当年“一切都报销”那声怒吼刻意进行了渲染。这位老元帅是位诗人。“诗如其人”,诗人那首脍炙人口的《青松》,赞美的是中国人民“压不垮”的英勇气概,也是这位元帅诗人的自我写照。
陈老总这个记者会时间之长,声势之大,涉及问题之多,答问之精彩,影响之深广,在共和国60年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我在这个记者会上听俄语高翻的同声传译,感到陈老总的骨气、陈式语言的那种“虎气”,全都给译出来了。
我们搞原子弹,最终是为了消灭原子弹
我从一些介绍中国核工业发展历程的材料中了解到,还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关注核问题。1949年夏天,刘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苏联时,就表现出对核问题的兴趣。有一次,毛泽东回忆起新中国成立之初出访苏联的感受时说:原子弹,美苏两家都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中国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时,毛泽东就向他表示过对核感兴趣。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一开始只愿给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但鉴于自己刚上台不久,尚需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于是就答应帮助中国建一个小型实验型核反应堆。
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就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兴致勃勃地大谈原子弹,并说,“正在开始研究”那个东西,1957年夏天,赫鲁晓夫通过内部斗争把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搞了下去,有求于毛泽东就更显迫切。在核武器研究方面,他主动提供了图纸、资料,甚至设备,还向中国派出了大批核专家。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苏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逐渐显现,赫鲁晓夫于1959年夏天决定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核资料,一年后,又从中国撤走了全部核专家。
上面之所以扼要地同顾一下中办之间的核关系,是因为1963年我到外交部工作之后,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听到陈老总同外国记者谈核问题,隐约感觉到他对某一核大国有些不满情绪。
有一次,有位记者说,有的核专家声称,世界上目前已有的原子弹,就足以毁灭地球好几遍,问陈老总对此有何看法。他答道:不只是核专家这样说,有一个人(指赫鲁晓夫)就拿这个东西来吓唬人。原子弹是厉害,但毛主席有句名言:原子弹是只纸老虎,这是从战略上
藐视它,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亚非拉的反帝反殖斗争才是最好的原子弹。
还有一次,有位记者问陈老总:中国核计划的目标是什么?他答称:这个原子弹嘛,既不能吃,又不能穿,搞那么些有啥子用嘛!中国只搞一点点。我们穷得很,不同人家搞竞赛。至于目标嘛,我们搞原子弹,最终是为了消灭原子弹。
要“快刀斩乱麻”,不要“钝刀子切肉”
1964年初秋的一天,陈老总突然来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司领导把他请到司里最大的一个办公室——俄文组。碰巧,陈老总就在靠窗我平时坐的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此前,我多次见过这位开国元勋,还给他当过翻译,但坐在他身旁零距离听他作报告,这还是第一次。
陈老总滔滔不绝地讲了三四十分钟。他老人家对我们外事翻译的一片深情和殷切期望,都跃然“嘴”上,深深地印在我这个刚刚踏进新中国外交门槛的新兵脑海里。下面,就引述陈老总当时在我们翻译处所讲的、我早已烂熟于心的几段话:
——一年365天,你们的高翻们几乎天天跟着我,是我另一张不可缺的嘴。如果没有这张嘴,我在人家外国人面前就成了个哑巴。因此,再忙也得来看看大家,道一声辛苦,说一句感谢。
——主席、总理把我摆在这个位子(指外交部长)上,一晃就是五六年。总理太忙,外事这一大摊,我替我这位兄长分担一点。功劳谈不上,苦劳嘛。兴许还有一小点。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外长,一直还是我们的总理。还没有解放,他早就已经是我们党的“外交部长”了。
——你们这里人才济济,卧虎藏龙。你们这些“虎”呀“龙”呀,如果给我翻得快刀斩乱麻,我就高兴。钝刀子切肉,半天切不出血来——这个最要不得!
近来,人们到处讲“又红又专”。人家“红”讲得多。我就多讲点“专”。我常常引用“艺高人胆大”这句老话。对你们这些高翻来说,“艺高”就是你们“手里”那把“快刀”。
所谓“快刀”,其实是一把“利刃”。对诸位来说,“快刀”也好,“利刀”也罢,一要中外文底子厚,二要政策水平高,三要领会领导意图准。对啦,再加上一条:还要古文基础好。主席见外宾时,常常引用占诗词,有时还用典。《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你不往脑子里装一些,怎么给人家翻?!当然,都懂——也不现实,但一年比一年多懂一些,总是可以的吧!
在“艺高人胆大”这句后面,还有一句,叫做“胆大人艺高”。我发现,有些高翻胆子太小,一见到我就害怕。我陈某人有啥子可怕的嘛,又不会吃人!没有翻你就怕,还能发挥得好?!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表个态:我支持你们的工作,你就大胆地给我翻!
——我在部里常常讲,一年365天,我天天管着你们,不管你服还是不服。但是,我想,一年下来,总得给半天时间,让大家也管管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我就坐在诸位面前。让我们来“换一下位子”,请诸位也来管管我,给我提提意见。
写到这里,我想指出,上面所引“人家‘红讲得多,我就多讲点‘专”那句话,陈老总是有感而发,话中有话。我清楚地记得,1962年春天,他在广州的一个座谈会上,面对知识界人士当时所受极左思潮的压抑,发表了一篇三万余言的“脱帽加冕”的讲话。当时,陈毅向在座的知识界人士“掏心窝子”,掷地有声地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他向全场的知识分子深深鞠了一躬。针对知识分子不敢写文章、不敢说话这种反常状况,陈老总动情地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这个后来被打成“大毒草”的“爆炸性”讲话,激起了全场60多次雷鸣般的掌声。
我是1956年秋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学习的。在校学习七年(本科和翻译班)期间,陈老总时不时地单独到我们外院,或者到北京西、北郊十大院校(联合)作报告。我到外交部工作后,听陈老总作报告的机会就更多了。他每次话匣子一打开,少于一个上午或下午是关不上的,而且都是即席,桌面上连一张小纸片也没有。大家最爱听周总理和陈毅外长作报告。那种场面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人人几乎屏着呼吸在听,简直是一种享受。陈老总那宽阔的视野、入木三分的见解、坦荡的胸怀、独特的幽默、不可复制的语言,都给我留下了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印象。
“不憋不成才”
有一次,蒙古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达赉为蒙中建交纪念日举行招待会,陈毅作为主宾应邀出席。陈老总先与各国驻华使节交谈,外交部四大语种——英、法、西、阿语的译员和我跟在他后面,需要时上前当当翻译。
事先,陈老总交代说,在招待会上,外交部准备的讲话稿他就不读了,视情况只随便讲几句。在蒙古临时代办致词后,陈毅对在场的宾客们说,最近公开讲话比较多,现在没有多少新话可讲了,只向蒙古朋友们讲几句祝贺的话。可是,陈老总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了。当时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正在升级,他的话题是围绕着越战展开的。他越讲越具体,什么越南丛林中瘴气之大,猛蛇之毒,恶蚊之大,咬几口就能咬死人……一连讲了四五十分钟,还丝毫没有打住的意思。
当时担任口译工作的是外交部亚洲司一位蒙古族青年,他的蒙汉两种语言都很好,一开始翻译得挺顺的。但随着陈老总话题的具体化,可以看得出来,他越翻译心里越发毛,头上冷汗直冒,翻译起来往往丢三落四,有时甚至站在那里发愣。
陈老总见状提高嗓门说:“偌大的一个外交部,难道就没有更好一些的蒙文翻译!?”时任苏欧司专员的戈更夫(蒙古族)连声答道:“有!有!有!”并立即向摆着话筒的地方赶。陈老总冲他摆了摆手,摇着头说:“不用有劳你的大驾了!还是让他继续给我翻。老话说:‘不憋不成才,年轻人嘛,就得让他憋一憋。憋上十次八次就好啦。让他舒舒服服的,他一辈子也成不了才!”
说到给陈老总当翻译,我不由得想起外交部翻译处五大语种高翻们“集体卡壳”的一件往事。有一次在记者会上,陈毅谈到日本北方四岛时,把择捉、国后、色丹、齿舞的名称一一列了出来。当时,我与记者们坐在一起,戴着耳机听俄语同声传译。当陈老总说完这四个岛名后,俄语传译就一下子断了。我立即把同声传译器的选择语道按钮逐一快速拨到英、法、西、阿四条语道,结果发现这四条语道一个个也哑了。原来,五大语种的高翻们全都蒙了,弄不清这几个岛的外语究竟该怎么说,又不好根据汉语的发音瞎拼一通。
外交部翻译处的领导对这次“事故”很重视,让各语种把四个岛的中外文名称对照表打印出来,人手一份,并要求大家随身带上,得便时就拿出来看看、背背。我还把一张北方四岛的地图粗线条地画了下来,并附上四岛的地理概况和历史沿革,时不时地翻出来看看。尽管后来在口笔译实践中,在与外国人交谈时,再也没有机会碰到这几个岛名,但其俄文名称及概况,4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最后一次巨大贡献
如上所述,陈毅在“文革”中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但在1969年,这位元帅外长为中国的外交事业、乃至为对内方略的改变,作出了最后一次巨大的贡献。
这一年的3月,在中苏边境地区发生几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后,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林彪提出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慎重计,毛泽东委托早已“靠边站”的陈老总主持召开“四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国际形势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从战略角度来看待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并重新审视中国的对外政策。从3月1日至10月8日,在七个多月时间内,四位老帅开了24次会。
陈老总和另外三位老帅不为一片打声所左右,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客观、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苏联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据此,四位老帅提出利用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开展外交工作的具体设想,写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
在座谈中,陈老总首先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还主张“用非常规手段”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1971年春天,毛泽东真的采取了一种“非常规手段”——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这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正是它撬开了中美之间紧闭的大门。当时已重病缠身的陈老总,得知毛泽东接受他的建议后非常高兴。
陈老总和另外三位老帅经过深思熟虑所提出的观点与设想,在相当大程度上消除了林彪等在“战”“和”问题上的干扰,最终被毛泽东所采纳。为毛泽东后来调整对内大政方针以及在中美苏“大三角”中纵横捭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