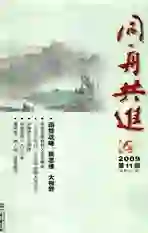开国大典:鲜活的历史细节
2009-01-20王建柱
王建柱
回首60年前,那宏大场面的幕后,其实隐藏着许多鲜活的历史细节: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原来是新中国的“接生员”,政协会徽原是新中国的最早标志,著名油画《开国大典》的坎坷命运则是我们民族曲折经历的一个缩影……
【罗浪 :林伯渠忘记宣布“奏国歌”】
1949年10月1日14时30分,北京天安门广场。
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罗浪,提前半个小时就率领军乐团站到了天安门城楼的正前方。作为整个乐团的总指挥,他紧张而急切地等待着那个辉煌时刻的到来。
1947年底,经聂荣臻司令员批准,正式组建了华北军区军乐队,罗浪任军乐队队长兼指挥。1949年初,上级决定由罗浪负责组建一支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直到1949年8月初,罗浪才知道这支联合军乐队将要参加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兵,而是开国大典,而他自己将要举起的是开国大典上那支重若千钧的指挥旗。
1949年9月,《义勇军进行曲》在政协会议上被确定为国歌。但除国歌外,其他曲目怎么定,当时曾有争论。部分人主张按老规矩办,采用旧军队阅军的乐曲;也有部分人主张“一边倒”,全部采用苏联乐曲。年轻的罗浪则提出了第三种方案,要用经改编的我军的某些革命歌曲。新中国自己的庆典,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乐曲呢!三种意见争论激烈,最后上报到中央军委。哼唱了多年的《东方红》等20多首作品征服了中央领导的心,毛泽东挥笔写下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9个大字。
全部乐曲确定后,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又采用什么乐器呢?这也是个问题。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举世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拉开了序幕。200人的军乐队面向天安门城楼,站成两个方队,各自以10行横队和10行纵队的宏伟气势奏响同一支威武雄浑的乐曲。罗浪回忆说,我把大小军鼓都安排在第一排,这在当时是一种创造性的思路,是为了展示一种威武整齐的新面貌,造成一种鼓乐喧天的大气势。
此时,毛泽东和开国元勋们正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缓缓地登上天安门城楼。
当时的气氛既热烈又紧张,林伯渠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却忘了宣布“奏国歌”。等了大约半分钟后,罗浪按预定的程序,果断地指挥军乐队奏起了国歌,天安门广场上顿时欢声雷动……
【侯波、徐肖冰 :周总理亲自为镜头记录“打下手”】
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最让她铭刻于心的是开国大典的拍摄。
作为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女摄影师,侯波拍下了毛泽东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个令人激动的瞬间,给后世留下了经典画面。谈起当年拍摄情景,老人的言语和表情仍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激动和自豪。
开国大典之前,夫妇俩同时接到上天安门城楼的通知:徐肖冰负责拍摄电影,侯波负责拍摄照片。
当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城楼西侧上来时,早早恭候在那里的侯波开始了紧张的拍摄。当时她端着的是只能装12张底片的120型照相机,为抓住好的镜头,便不停地优选角度,一边拍一边往后退,还要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拍完一卷,就要赶快换。
在整个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始终精神饱满。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侯波就要不停地跟着拍照。当她看到毛泽东走到城楼右边时,想拍一个带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侧身镜头。由于空间十分有限,她一再往后撤,但还是取不到满意的角度。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抓住她的衣角说:“你放心大胆地取景吧,我抓住你。”这时她也顾不上是谁了,使劲往后撤身体,终于取到一个很好的角度,随即按下了快门。拉着她的人还一再地叮嘱说:“要小心,要小心,别摔着。”拍完后,侯波收回身体扭头一看,帮忙的人竟然是周恩来总理。
过了一会儿,侯波又急忙换到另一个位置,因为这时毛泽东正向天安门城楼下的群众挥手致意,她想拍下这一画面,但同样需要把身体伸向护栏外。陈云看出了她的意图,主动伸过手来,抓住她的衣服说:“我来帮你,赶快拍。”
【张仃:政协会徽是新中国的最早标志】
1949年初,时任哈尔滨《东北画报》主编的张仃,应中央军委之邀进京负责编一本反映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画册。当时,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周恩来便把张仃请进中南海做美术顾问,进行怀仁堂、勤政殿等工程的改建设计。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周恩来又请他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设计会徽。
接到周恩来交付的任务后,张仃在中南海投入了紧张的设计工作。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新中国的第一枚政协会徽悬挂在主席台中央。共和国的国号、国旗、国歌、国徽等都是在这个政协会徽之下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和确定的,因此可以说政协会徽是新中国最早的标志。
与此同时,张仃还担任了开国大典仪式的美术设计。按照中国民间的喜庆习惯,他提出在天安门城楼上挂4个大红灯笼,城楼两侧各插上4面红旗,大标语牌用灯光照明,在观礼台的红墙下方画上飘动的红绸子,并安排周令钊绘制天安门城楼中央的巨幅毛主席像。而天安门上的大红灯笼,是他特意到北京前门外廊坊头条请工匠赶制的。
这期间,张仃还给新政权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具体事宜提出过许多实用美术方面的建议。比如,国家机关门前挂的牌子应是什么形式,当时提出过很多方案,张仃提出采用白地黑字并一律使用端庄的老宋体书写。这一方案一直沿用至今。“白地黑字”的牌子有何寓意呢?张仃解释说:“这主要是为了区别国民党时期的蓝地白字及青天白日标记。白地黑字,寓意明明白白,既简洁、庄重,又能体现新政权的特点。”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没有悬挂国徽。国徽的问世是在1950年建国一周年前夕,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949年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国旗、国徽或国歌,新中国形象的艺术设计便成为了当时的重要任务。
1949年7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指定下设的第6小组负责国徽方案的草拟工作,并公开发布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向国内外征集国徽图案,并且特地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了3点要求:(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政协筹委会共收到国徽图案900幅,不过有参考价值的仅有几十件。直到9月下旬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会期间,代表们仍对设计出来的国徽图案不甚满意。毛泽东建议:由原设计小组继续改进,将来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开国大典之后,组织上有意留张仃在中南海工作,他婉言谢绝说:“我是搞业务的,更愿意去教书。”此后张仃便投入筹建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不久,中央决定国庆一周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式悬挂国徽。国徽的设计任务加紧进行,具体交给两个设计组负责:一组是由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的一批教师;另一组是由张仃带领美术学院的一批教师。张仃和梁思成分别成为两个设计组的核心人物,定稿将在两个设计组提供的方案中进行选择。
当两组的方案放在一起比较时,风格大相径庭。梁思成小组设计的国徽,核心内容是一块玉璧,玉璧有国器的象征,也含指祖国统一、完璧归赵,文人气息浓郁。但周总理认为这个方案没有体现出新中国的政权特色。张仃小组的方案则明确提出: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五角星象征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和国家富强康乐;天安门为主体。
当时中央比较倾向张仃小组的方案,为两组召开了一次交锋会,负责人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张仃认为,他的原创主体是天安门,工农联盟的创意来自周恩来。在设计说明里他阐述得很明白:天安门是中国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的象征,同时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开始的地方,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发生在这里,新中国也在这里宣布成立,因此将天安门作为国徽的主体是不言而喻的。
最终,中央传达了一条意见:国徽当中一定要有天安门的形象,接纳了张仃小组的方案。周恩来将进一步完善国徽设计的工作交给了梁思成。(当时梁思成是非党人士,张仃是从解放区来的。周恩来对张仃说:“你们合作吧。”)
【彭光涵:国旗诞生的曲折过程】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设立了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彭光涵当时担任第六小组的秘书,他才31岁,是第六小组中年纪最小的。经过两个多月紧张认真的征集和审阅工作,9月14日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就国都、纪元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国旗问题争论很大。
彭光涵介绍说,对于群众的来稿,小组成员经过讨论,有三类来稿被筛选掉了:第一类是有镰刀锤子的,有模仿苏联国旗的痕迹;第二类是用嘉禾齿轮的,图面比较复杂;第三类是采用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的,模仿西方国家国旗的痕迹很明显。小组成员从2992幅图案中最后选出了较好的四十余幅作为初选图案送交周恩来审阅。周恩来对彭光涵说:“你把这些图案分类编成册,给每个图案编号,但不写作者姓名,避免审阅人带有偏见。初选图案仍由第六小组进行复选,精选出一批图案,上报大会主席团。”
政协大会决定9月30日闭幕,而国旗图案迟迟不能定案,第六小组成员都很焦急。在当晚的会议上,副组长沈雁冰对彭光涵说:“你是秘书,又住中南海,可以见到毛主席、周恩来副主任(新政协筹备会成立了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你尽快向他们汇报目前的困难情况,请他们指示如何办。”周恩来在听取了彭光涵对第六小组推荐的38幅图案的介绍后问彭光涵:“你接触过很多图案,也听了很多反映,有哪些图案有比较多的人喜欢,容易获得大家一致同意?”
彭光涵知道,张治中同毛主席有一段关于国旗的对话。张问毛主席赞同哪个图案,毛回答:“我还没有最后认定哪幅图案。”张说:“恕我直言,我反对用一条杠代表黄河图案。红底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有一条杠,这不变成了分裂国家了吗?同时,以一条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毛主席微笑着说:“噢,这倒是个问题,我约大家来研究一下,一定要选一幅大家都满意的。”
此时,彭光涵迅速地翻到《复字32号》(红底五星旗),并拿出投稿人曾联松的原稿对周恩来说:“这幅图是在截稿前两三天才收到的。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图案很有新意,但在五星内有镰锤不好,建议删去后可作为复选稿,印出来的图案是我根据小组意见重新画的图案。”
周恩来点了点头,接着问彭光涵:“那四颗星的含义是什么呢?你说说看。”彭光涵解释说:“您昨天的报告中有一段话就是最好的说明。您说‘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这样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人民的一部分,在国旗中应该有它的位置。至于如何准确说明,最好由小组的同志去拟定。”
周恩来听后很满意,拍着彭光涵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字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一定要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9月25日晚,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协商座谈会。彭光涵提前到达丰泽园会议厅,在秘书席等候。约8点半,毛泽东、周恩来领头进入会议厅,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等陆续就座。
关于国旗,毛主席首先发言:“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有中国特点,因此画一条横线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
说到这里,毛主席拿起一面红底五星旗向大家展示说:“很多人都说《复字32号》这面旗图案好……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在座的人都表示赞同32号图案为国旗,但邵力子提出要改一改《复字32号》的说明,他说:“用大星、小星的提法不好,因为上海有一种习惯,大星是大老婆,小星是小老婆,所以称大星、小星不准确。”这几句话引起哄堂大笑。毛主席也笑着说:“那就不提大星、小星,只提五颗星的关系。我看就提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
9月27日,当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主席台展示的,正是彭光涵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栅栏所做的那面红旗。大会对国旗的名称进行了修改,将“红底五星旗”改为“五星红旗”。
【周令钊、陈若菊: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画像】
国人无论男女老少,对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挂的毛主席画像都不会感到陌生。这幅画像的作者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周令钊。
早在迎接北平解放时,周令钊就带领学生画宣传画,写标语,布置会场。他才思敏捷,成了美院有名的“快手”——构思快、动手快、干得好。
1949年4月初,国共和谈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事前,周令钊接受了上级交给的布置会场的任务。经过现场考察,他利用会场里的八根柱子,分别写上和谈的八项条件,并各挂一个用木板制作的象征和平的白鸽子。他特别选择了著名摄影家吴印箴拍摄的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照片,这张照片曾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悬挂过。周令钊以此为蓝本,画了第一张毛主席像。这张约一个门面大的画像,背景为红色,毛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子略敞开,面带微笑,放置在主席台正中。这独具匠心的布置,把会场的气氛营造得平和而热烈,受到与会领导的称赞,说他设计布置得很好,尤其是毛主席像画得好。
有了这次上佳“表现”,绘制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的光荣任务便“非他莫属”了。
接到任务后,周令钊便带着学生、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在城楼上的大殿外搭起脚手架,开始工作。考虑到毛主席的性格、风度和诗人气质,而且又是刚刚解放,周令钊依旧选取了北平和谈时用过的那张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来完成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要把小照片画成巨幅画像,必须一次又一次放格、打素描。每天天刚亮,周令钊和陈若菊便带着干粮登上天安门城楼开始作画,两人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直到天黑看不见才停笔。周令钊主要是画毛主席像的眼睛、鼻子等关键部位,陈若菊则手提小油桶,往灰色军装上大块大块地涂抹油彩。就这样连续两个星期,一次又一次地爬上爬下,改了又改,做到一丝不苟。9月30日,一幅栩栩如生的毛主席画像完成了。
时任北平市长的聂荣臻特来观看,他对画像上毛主席的神态和表情比较满意,但指出开国大典是个庄重的时刻,领子还是扣起来为好。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改好后已是深夜,回去刚躺下,又被人叫起,上级领导研究后决定将毛主席像下面的“为人民服务”5个小字去掉,于是他又火速赶到天安门。此时画像已挂上了城楼,聚光灯也打开了,但下面还留着架子等着他来修改。由于画太大,梯子又小,他只能一点一点地往上涂抹,反复操作,直至看上去“天衣无缝”为止。
l0月1日,毛主席率领中央领导登上天安门城楼,毛就站在画像的正上方。“可惜的是当时没有照相机,连一张工作照都没能留下来”。这成了周令钊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李普:毛主席一再叮嘱的重要字条】
作为老一代著名记者,李普见证并记录了20世纪中国发生的很多大事,1949年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尤其令他难忘。
1949年8月底,新华社特派记者李普由武汉中南总分社调到北平总社,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与另一位新华社记者李千峰一起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报道。
李普记得:“上城楼的嘉宾们当时大都住在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下午两点,大家先一起去中南海勤政殿,交代一遍流程后,来到天安门。毛主席是第一个沿台阶走上城楼的领导人,朱老总紧随其后。那时还没有电梯,大家都是步行走上去的。”
李普还记得,那天几乎所有人穿的都是中山装,只有“美髯公”张澜穿着长衫。
10月1日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是一件标准的公文。为了能及时拿到主席手里的公告,李普移到他身后,“当时毛主席显得很平静,稿子没有任何抖动”。读完公告后,毛主席手按电钮,一幅巨大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当时,李普听到陈毅感慨地说:“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能看到这一天,就已经很满足了!”
拿到主席宣读的公告后,李普并没有马上离开。因为虽然领导人的讲话稿早就印出来了,但还是需要他们的亲笔手稿,以核对每一处字词的小改动。“那天11个人的讲话中,陈毅老总的最短,只有5分钟;宋庆龄的讲稿先用英文打草稿,然后翻译成中文,很有自己的特色。”李普看见她的手稿上,有的字旁边还注上了拼音,因为她不大会讲普通话,整篇文章都是用上海味道的普通话念的。
李普回忆说:“我拿到稿子后,看见稿子上贴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共56名)的名字。毛主席指着那张字条,一再对我说:‘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这份《公告》是铅印的,贴上去的字条是别人手写的。文件上还有他用铅笔写的批示:‘照此发表,毛泽东。”
“这篇文章现在被收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文末注明‘根据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刊印。可见补入了全部名单的《公告》,只有毛泽东宣读以后交给了我的那一份,没有来得及另留底稿”。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这张名单呢?
李普说:“我事先已经知道,《公告》补入的全部名单,是根据张治中的建议补入的。张治中曾经是国民党的一位要人,也因‘三上延安而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后来,他参与了建立新中国的工作,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建议在《公告》里公布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名单。毛泽东当即明确表态说:‘好,把56名委员名字都写上去,可以表示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毛泽东之所以欣然接受张治中的建议,其中有个大道理。从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著名的论文开始,中共中央多年来再三宣布:中国的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到了1945年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报告的标题就是《论联合政府》。现在,这个伟大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毛主席所说的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上是建立和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即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这时,所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都进入了这个名单,就不言而喻了,而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真正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
庆典活动结束时,已是华灯初上。李普又连夜赶写了开国大典的新闻稿,第二天一早,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董希文:油画《开国大典》的曲折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反映重大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屡见不鲜。其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著名画家董希文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了。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委会需要一幅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术学院教师董希文承担了创作这幅作品的重任。1954年,这幅画作为年画首次出版发行,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销量超过100万份。后来,毛主席观看这幅作品时说:这是一幅充满了“独特的民族形式”和“大国风范”的油画。
作为新中国油画史上的鸿篇巨制,油画《开国大典》在美术史上和革命历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这幅作品在新中国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中也经历了数次无奈的删改。
对《开国大典》第一次改动是在“高饶事件”定性之后。董希文接到通知,去掉画中的高岗。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
第二次改动是在1968年。由于刘少奇被打倒,这次改动要在开国大典中去掉刘的形象,换上董必武的全身像。上级领导通知董希文去改《开国大典》时,他已身患癌症。女儿董一沙回忆:“当时父亲重病在身。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哥哥要替他去改,他坚决不同意……他说,这幅画是他一手画的,他要负责到底。”就这样,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国大典》再次被迫失去了历史真实。
其实在“文革”后期,董希文还曾接到第三次“删改通知”——刷掉林伯渠。幕后指使者江青,忌恨林伯渠当年反对她与毛泽东结婚。无奈董希文此时已重病在身,无力应命了,只好请他的学生完成第三次删改。不过,学生没有改动董希文的原作,而是临摹了一幅,以应“刷新”之需。这才不致再次造成历史遗憾。
《开国大典》上没有了刘少奇,董希文心中也从此对这幅作品多了一层牵挂。他说:“一个搞艺术的人对自己的作品要负责,要负责一千年……”他多么希望有朝一日亲手将刘少奇的形象恢复在《开国大典》上,他无时无刻不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当时,董希文的癌症已到晚期,他对学生们说:“真希望再有20年……”令人惋惜的是,董希文最终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1973年逝世前,他抱憾不已……
油画《开国大典》几十年来的坎坷命运,正是我们整个民族曲折经历的一个缩影。
(作者系中组部干部、文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