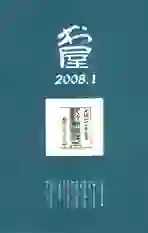《丁文江先生学行录》前言
2008-12-29欧阳哲生
书屋 2008年1期
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在长沙湘雅医院因煤气中毒引起脑部血管出血等病症,医治无效而去世。自从上年12月7日他赴湘潭谭家山煤矿勘察而伤风,12月8日晚上他在衡阳煤气中毒被送进医院以后,他的病情很快就惊动了北平、南京、长沙等地的朋友们,成为人们心悬的一块阴影。各地的亲朋好友密切关注他的病情的发展。12月11日翁文灏赶赴衡阳,决定让丁文江转往长沙湘雅医院治疗;12月21日傅斯年赶到长沙湘雅医院看望住院的丁文江,亲自与医生商量治疗方案;胡适则在北平通过电报持续了解病情发展,并与协和医院联系协助治疗事宜。
关于丁文江的死因,除了煤气中毒这一诱因,医治不得力似也是一大原因。其弟丁文治在他的悼文中检讨:“衡阳方面如果有长沙方面的医药设备和人才,不至于行人工呼吸将筋骨折断;长沙方面如果有更好的设备和人才,许多潜伏的病或不至于查不出来,这是中国内地医药和一般医士程度的整个问题。”此前,丁文江对生命的脆弱、环境的险恶和因为自己拼命工作、语锋太露可能遭到不测,似乎早有某种预感,故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已立下遗嘱,安排了后事。这样的做法,当时的确有点令人感到突兀。但联系丁文江所处的环境,似乎又并不为奇。
这是一个知识界频发事故的年代,不测的消息一个一个传来:年轻的地质学者赵亚曾在四川考察时被土匪杀害(1929年);诗人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殒命(1931年);前任中研院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办公室前(1933年);刘半农在蒙古考察时染回归热病身亡(1934年);《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狙杀(1934年)。这些熟悉面孔的消失,似乎都在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丁文江:生命是脆弱的。丁文江已明显意识到这一点。联想到自己家族成员的生命史过短,亲属中几乎没有活过五十岁的人,丁文江对生命的有限性不得不有所准备。然当事情真正发生时,人们的心灵仍不免产生一种震撼,毕竟他只有四十九岁。这样的年岁,正是一个人的事业如日中天、大展宏图的好时机。
丁文江是偏信西医的,胡适说:“他有一次在贵州内地旅行,到了一处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没有西医,在君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肯吃药。医生还没有赶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梁启超患病时,丁文江亦是力主送北京最有名的协和医院治疗,但与梁启超死在协和医院的结果一样,西医亦未能挽救他本人的生命,他在中国南方最有名的西医医院——湘雅医院溘然离世。他俩的死多少都有误诊的成分。
丁文江去世后,1月18日在中央研究院假中央大学大礼堂举行了高规格的追悼会,政界显要和学界名流,如蒋中正、蔡元培、王世杰、翁文灏、胡适等悉数参加,蔡元培主祭并亲致悼词。丁文江生前工作过的机构和学会组织,如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北京大学地质系、中国地质学会等也举行了追悼活动。按照丁文江本人的遗嘱,“死在那里,即葬在那里”,在长沙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他的好友翁文灏、蒋梦麟、梅贻琦专程赶到长沙出席。《独立评论》、《地质论评》、《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等刊开辟纪念专号、专栏,纷纷发表悼念丁文江的文章。在国际上,《字林西报》发表A True Patriot(《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社论;《泰晤士报》发表史密斯先生(Grafton Elliot Smith)的Dr V.K.Ting:An Appreciation(《丁文江博士:一个评价》)悼文;国联卫生组长拉西曼特自日内瓦电唁慰问丁夫人;日本、美国、欧洲等地报刊亦迅即报道了丁文江去世的消息。这是国际上第一次对一位中国科学家逝世做出如此众多的报道。国内外对丁文江去世所作的这种强烈反应说明,一方面大家对丁文江因追求科学事业而以身殉职深表哀悼,一方面亦是承认丁文江为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丁文江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已赫然载入中国近代科技史。
丁文江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成就的科学家。在他短暂的四十九年生涯中,他最大、最成功的事业是在地质学方面,“他的功绩特别是在实行野外调查,在这一方面讲,他是中国地质学界唯一的人物”,对西南地区的地质考察尤详。他创设地质调查所,经过严格、科学的管理,成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的卓有成就的主要机构,并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首创培养地质人才的机构——地质研究所,不遗余力地训练、提携富有才华的青年地质学者。国际著名地质学家葛利普称誉丁文江的学术成就时说:“建造中国地质学之基础,及擘划其发展之途径,丁文江博士实最大之功绩。博士之姓名在地质学上所占之位置,恐较其他任何学术方面更为重要。”此外,他以现代科学眼光发掘十七世纪明代两大科学文献《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的科学价值,表彰徐霞客、宋应星在人类科技史上的地位,使中国古代科学遗产在二十世纪重新大放光彩。他积极整理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文献(主要是壮族、彝族),编辑《爨文丛刻》,是最早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研究的高级学者。他对全国人种曾搜集最完备的材料,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开拓者。他撰写的《民国军事近纪》保存了民国前期军事编制的诸多史料,成为人们研究北洋政府时期军事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他主持编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保存了大量梁启超的书札,是研究梁启超的主要参考文献,也是近代人物年谱的经典之作。他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独裁与民主论争,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重要思想家之一。在近代中国科研环境和科研条件均极其恶劣的情形下,一个人物做出一项开拓性的成就已不容易,丁文江能取得如此之多的成就,这与他勤奋的工作精神和卓越的科研能力分不开。
丁文江遽然离世时,大家异口同声地为国家失去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而表示深深的惋惜。胡适沉痛地说:“在君之死,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无法弥补的一大损失!”章鸿钊哀叹:“我真不解世界上有这样无穷的缺憾!”“我听到了丁在君的死,我只有叹一声,人生只是一个缺憾而已!”翁文灏感慨道:“在君先生的死是中国的大损失,‘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人才如此难得,像在君先生的人中国能有几个?”陶孟和痛苦地表示:“在君的死,不待言,是我们国家无法弥补的损失。”李济悲泣地说:“在君之死,不但使认识他的朋友泪流满襟;一般有民族意识的公众莫不认为是国家的一种不可补偿的损失。这种自然流露的情绪,不是偶然发生的。这可以证明他所领导的各种事业之价值,已渐为大家所能了解。”葛利普在悼文中称:“丁博士之遽尔长逝,科学界哀悼损失一个领袖,一个工作人员,一个主动之力量。博士之学生、博士之同事与博士之朋友,又哀悼损失丁文江这个‘人’!”杨钟健评价道:“他的死,不但是地质界的损失,学术界的损失,实是中国各方面的一个大损失。”学术界这些重量级人物对丁文江的高度评价,凸显出丁文江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地质界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他的逝世使大家产生了一种失重感。
为纪念丁文江,中央研究院设立“丁文江奖金”,表彰在自然科学领域做出贡献的科学工作者。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丁文江纪念基金”,以奖励那些在地质领域富有成就的地质工作者。这些纪念奖的设立,实在是对一种丁文江式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的鼓励,“明天就死又何妨!又拼命做工,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这是丁文江喜欢吟诵的诗句,胡适以为也是丁文江最适当的墓志铭,其实也是对“丁文江精神”最好的诠释。
为便于读者阅读,本书将所收纪念、追思文章大略分为六辑:第一辑为《独立评论》(第一八八、一八九、一九二、二一一号)刊登的纪念文章。第二辑为《地质论评》、《国闻周报》等刊登载的纪念文章。另有两篇系在丁文江生前发表的介绍性文字,出自温源宁、林语堂之手,因有助人们了解时人的丁文江印象,故予以收录。第三辑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发表在台港地区报刊上纪念丁文江的文章。第四辑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学人发表的纪念丁文江的文章。第五辑为丁文江逝世后出版的各种著作序言及其相关书评。第六辑为评论丁文江的各种英文报道和文章。在处理这一辑时,我没有像许多编者那样将它们译成中文,而是直接采用原文,一方面是为免读者搜索原作之苦,一方面也是希望引起学术界直接阅读外文文献的兴趣。书后附录《纪念、研究丁文江论著目录索引》,以为进一步了解、研究丁文江的读者提供文献资料索引。本书所收文章绝大多数出自与丁文江有关的朋友、同事、学生和亲属之手,他们亲身感受丁文江的教诲,对先生的为人处世、治学精神有着直接的了解;少数几篇文章的作者与丁文江虽无一面之缘,但其文引用的档案材料亦可谓直接史料,对理解、研究丁文江极有价值。追忆、纪念丁文江的文字并不限现在所收文章,有些文字因时间已长,记忆与事实明显差误,故未予收录。
将有关纪念、研究丁文江的文字编辑成集,现已有数种:《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朱传誉编《丁文江传记资料》(三册,影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泰兴文史资料——纪念丁文江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专辑》(第四辑,1987年4月版)、王鸿桢主编《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纪念丁文江一百周年章鸿钊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雷启立编《丁文江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2007年是丁文江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为缅怀先生的学术业绩和科学精神,我们再一次编辑了这本《丁文江先生学行录》,收文数量有较大篇幅增加,其意在于传承“丁文江精神”——一种为中国科学事业而献身的奋斗精神,希望本书的问世,有助于人们对丁文江先生学行和交谊的全面理解。
(《丁文江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