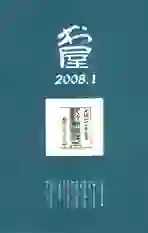自由的歧义与条件
2008-12-29何怀宏
书屋 2008年1期
“自由”的定义,据阿克顿在十九世纪末所说,就已有两百种之多。至于它繁衍扩展的含义,究竟是指法国的民主平等,还是指美国的联邦共和,是指意大利人关注的民族独立,还是德国人理想的精英统治,实在是众说纷纭。还有将宗教自由归功于荷兰革命、将立宪政体归功于英国革命等等,不一而足。而对“自由”观念的这一大堆不同解释引起的流血冲突,在阿克顿看来仅次于宗教神学。
阿克顿强调自由或争取自由是人类历史的主线。他试图写一部人类的自由史,试图“穿越我们盛衰多变的历史景观,去追索自由观念的缓慢进程,去描述那些触及良知本质的深邃思考如何促进了一种维护良知的更崇高、更神圣的自由观;直到权利的卫士变成作为权利之原因的义务的卫士,直到作为尘世财富的物质保障而受到赞赏的自由,因为保障一切宗教活动而变为神圣”。这一计划因其也许“过于博学”而未完成,但从他的一些讲演和文章已略见端倪。阿克顿也认为这一自由历程常常是忧郁而令人心碎的历程,自由的真正朋友其实并不多,自由获得的成果往往是和其他目标的临时结盟而致,所以常常是不可靠的。在人类经历的有些年代,自由的历史简直就是不自由的历史,人们对其他目标的追求常常转移乃至窒息对自由的追求。
阿克顿的自由观有两点特别值得现代人注意:其一是他强调自由与良知、道德的联系,他甚至说:“自由作为道德问题的紧迫性远远大于其作为政治问题的紧迫性。”自由的获得常常源于良知的呼唤,而它的维系也需要将自由不仅视为一种权利,更应视为一种义务。因为自由总是和法律,或者更深入地说,和法律的道德基础联系在一起。自由在个人与社会、政府之间划出一条恰当的界限,它需要一种宪政和法治来稳定地保护它,自由也需要个人尊重和遵守这一恰当划定的界限和相应规定的法律的义务。另外,自由也总是意味着一种平等,意味着在某一范围内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否则它就很难说具有普遍真实的含义。这也同样需要人们在享受自己自由的同时尊重别人的自由,在运用自己权利的同时遵守自己的义务。
其二是阿克顿强调自由的运用不仅是为了保障和扩大物质的利益,还更应使之保障精神的追求。而认识到且努力于这一点,也许就能使它们互为保障。这也就是说,自由的起源是道德的,甚至是神圣的,它的最高运用也最好是道德的、神圣的,亦即优先保障良心、信仰及其合理表达空间的自由。这种自由也许是人类自由所结出的最美丽的花朵,也是一种相对来说最为有益无弊的自由。
自由是需要通过斗争来获得的,而不是赐予的。赐予的东西总是不可靠的,随时可能收回。而解放始终应当包含一种自我解放,否则,被“解放”之后很容易又沦入被奴役的状态。所以,自由总是需要有勇敢和智慧的德性为伴。而也正是在为自由的斗争中,人们也才能真正尝到自由的真味,才能真正珍惜它,决不轻易出让它。但争取自由的斗争又不是无节制的,与其说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不如说是在原本不是平等自由的双方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所以从手段上说常常是既斗争,又妥协。自由甚至常常是一种讨价还价,争取自由当然需要诉诸一种压力,包括社会运动的压力,但最好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且最后的结果不是将一部分人打入另类,使之处于被强制乃至奴役的地位,因为那样的话,又将出现新的不自由。
自由不应当依某一个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想给多少就多少,或者想给就给,想收就收。每一个人都应置于法律的亦即平等的统治之下,都同样受法律的约束。从个人来说,每个人在享受自由的时候,不能侵犯他人的同等自由,而这也就意味着守法。进而言之,要真正保障所有人的自由,法律的性质还应当是体现所有人的同等自由权利的。为了防范来自上面的、权力的威胁——这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法律还应当是宪政和限权的。而究竟实行怎样的法律,的确又还相当依赖于民情,所以,社会的所有成员或至少大多数成员应懂得保护自己的自由,不会轻易为了面包或其他的诱惑出让自己的自由。
自由最后是要落实到个人的,但自由一定不是单个人的,仅仅一个人的自由只是暴君的自由。落实到个人今天就意味着落实到一定社会内的所有成员,这就必须引入平等的概念。自由必须是平等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自由必须以他人的同等自由为界,进而言之,每一个人的自由也许还可以通过制度调整得成为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自由就还有一个配享或承担的问题。在同一个社会里,如果自由权利都是平等的,但在不同人的运用上有高下或广狭,这里并不涉及到“特权”,而是价值取向和能力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在运用的结果上拉平,则自由必须是不平等的,即必须借助于国家的法律或政策使之不平等。这样,自由的试金石就常常是“身处弱势的少数人所享有的地位和安全状况”,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一方面处于少数,而真正理解和能够以崇高的形式运用自由的人至少在某一阶段开始的时候更有可能处于少数。“最是文人不自由”,最是“先知”不自由。但保障他们探讨、批评和创作的自由却不仅对他们是重要甚至生死攸关的,对社会的进步以及自由的扩展也是极为重要的。
本卷的编选侧重于这样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分析自由本身,自由的概念或涵义,乃至自由的种类,各种自由的地位和优先性。首先我们有霍布士的定义,即认为自由就是行为的无障碍状态,这个定义看似简单甚至狭窄,却也许把握到了自由的比较原始和内核的意义。贡斯当划分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这一基本划分看来迄今没有遇到大的挑战。而伯林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两个自由概念则引起不少争议,其引人注意的程度说明了这一划分深刻地触及到了时代的一个最敏感问题:我们将对自由抱何种期望?在伯林的这一划分后面有对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兴起的反省,也有对人性或者说在现代社会更为展露的人性的认识,而其理论的根底是一种文化和价值的多元论。哈耶克和罗尔斯也对自由的概念做了仔细的辨析,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则考虑在充分意识和肯认价值多元的情况下,如何仍然在一种政治的范畴内保有自由和就此达致一种基本的道德共识。还有像在各种自由中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优先地位,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等问题,也在本卷中有所涉及。晚近的共和主义则尝试提出第三种自由观。
第二是讨论自由的条件、自由的保障与实现,尤其是自由与政治条件的联系,自由可能遭到的威胁。第一篇伯里克利的演讲说明了民主政制和公民自由是雅典人幸福的一个基本要素或条件,而保障自由的政制本身也是需要通过斗争来争取和保卫的。孟德斯鸠阐述了有关政治自由的法律与政治制度及公民的关系,尤其是与权利的分立及相互制衡的关系。卢梭则认为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起来用强力反抗和革命是正当的。托克维尔批评法国人在大革命中因为过分追求平等而丢失了自由,反使自己置于新的政治奴役之下。密尔则考虑除了来自政治权力、政府对自由的威胁,还有来自另一方面对于自由的威胁——社会的多数对自由的可能压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考虑了另一个根本的问题,自由与人性及其差别的联系,是否多数人会比热爱自由、理性更热爱物质的东西和更相信奇迹。方纳则从美国的实际历史来考察自由条件的改进和自由范围的扩大等问题。
共和主义理论家使我们更加注意自由的政治制度的保障,但是,保障和实现自由和自由的本意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首先要弄清需要保障或需要优先保障的是什么自由,斯金纳实际上认为还是要优先保障和实现消极自由,这样,法治共和宪政在这里实际上就落入第二义,或者说,这是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对待消极自由。当然,政治制度绝不是不重要的,本卷最后一篇是佩蒂特著作的节选,与第一篇正好相呼应,也许可以见出我们对自由与政制联系的重视。每个人的基本人身、良心自由都应当是一个堡垒,其中还应包括财产和言论的自由,因为财产是人身的延伸,言论是良心的延伸,而这个堡垒应当建立在可靠的政制基础之上。
还有自由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心灵自由的问题,也许一个人能够在任何极端不利的处境中都能保有自己的心灵自由和选择自由——但选择的范围往往压缩到只能说“是”或“不”,而这种斯多亚派推崇的精神境界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的。还有意志自由和决定论的问题,它涉及到对我们的自主性和行为道德责任的认识,虽然很重要,但毕竟是一个艰难的哲学形而上学的问题,故我们只选了一篇内格尔相对通俗的“自由意志”。我们主要想讨论的还是公民自由、政治自由。所以,我们还想就自由的含义问题再说几句,而有关自由的保障问题毕竟和对自由概念的理解密切相关。
本卷近代以来的几乎所有作者都谈到过自由的多义或歧义问题,但我们也许可以给“自由”一个比较朴素的或弱势的解释。奴隶肯定不是自由的,囚犯肯定是不自由的,违反本人意愿而强制的行为肯定是不自由的。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自由的政治条件纳入自由本身的定义,我们可以以“无强制”为自由的第一要义,以行为的自由为第一要义,在这一范围内,他就应当承担自己对自己行为的基本责任了。“自由”的第二层意思即这种行动的意志后面是否还有什么东西决定或支配,我们是否真正是自主的,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判定。
而伯林大致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划分两种自由概念。一是消极自由或者直译为“否定性自由”(negative liberty ),说的是一个人的行动不受外在的干预和强制,它是“免于什么”的自由;而积极自由则是指要“成为什么”的自由,比如说成为自己的真正主人。“自主”与否是不容易判断的,尤其是当要追溯意志的原因或原因的原因的时候。而就像伯林所说:“一件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公平、正义,不是文化,也不是人类的幸福或平静的良心。”一个人可以因为正义或良心牺牲自己乃至别人的自由,但不能说所牺牲或丧失的不是自由。我们或者可以反过来说,“自由”就是“由自”,你的行为是由你自己生发出来的,是你自己决定做出的,是你自愿选择的,而不是在别人的强制或干涉下不得不做出的,这就已经是一种基本的自由了。有一些人可能认为有基本的自由就够了,而有些人却可能认为还不够,他不知道如何享用和承担自由。他甚至可能将自由理解成幸福甚至纯粹感官、物质的快乐,得不到就不高兴了,就认为自己没有自由。而消极自由无论如何是一个底线,虽然我们也不应当自设限制,还是应当考虑在消极自由的基础上去努力争取更具积极意义的自由,只是不让对积极自由的争取违反消极自由,更要防止以“积极自由”的名义使消极自由化为乌有。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你也许可以说得到了“幸福”或别的什么东西,但无论如何不再有自由。
至于自由的条件,我们也的确需要保障一种基本的物质和生存条件,当一个人饥寒交迫的时候,是谈不上什么自由的,但是,当一个人要求华衣锦食的时候,他所要求的也并不是自由。人们常常把“自由”和要得到他们想要的“自由”而认为必须的条件——尤其是社会或物质的条件混同起来了,然而,这些条件有些可能是必需的,有些可能却不是那么必须,要依人们对自由的理解是强定义还是弱定义,高定义还是低定义而定,而人们有可能因为过于专注于这些条件而反而丢掉了自由的真意。
的确,还有一个人类如何运用自己的自由的问题。会不会即使所有人都平等自由地追求自己所理解的幸福,都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但由于多数的缘故,最后却形成一种物欲流行、功利滔滔的局面。但这已经是另外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缓一步考虑,除非它已经严重到不仅对自由乃至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
(此书原为“西方经典·观念读本”丛书所编之一种,该套丛书现易名为“大家西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