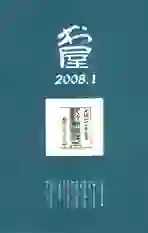书法艺术与心灵自由
2008-12-29蔡永胜
书屋 2008年1期
黑格尔说,中国人除了皇帝一人外都不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古希腊有一部分人(即希腊公民)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只有日耳曼民族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是自由的;五四反传统人士如鲁迅认为中国人是坐稳了奴隶时代与坐不稳奴隶时代的可怜一群。欧洲中心主义者与吾国民族虚无主义者几乎形成了一个普遍性共识——中国文明缺乏自由精神。而且人们似乎能随处找到这种认识的证据:古希腊罗马的绘画和雕塑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作品中的自由精神,是中国的艺术所没有的,兵马俑中的士兵是整体中的非个性体,与希腊雕塑“掷铁饼者”、“拉奥孔”、“胜利女神”(即“萨莫色雷斯的尼开神像”)比较起来显得过于刻板,缺乏个性,当然也就缺乏自由。这样,中国学者要说明中国文艺并不缺乏自由精神就很没有自信——若以希腊人崇尚的个人主义相比,则中国的艺术中表现出心灵自由的作品如汉代的青铜雕塑“马踏飞燕”(或“马踏龙雀”),似乎是太少了。
以西方的文艺理论来审视中国文艺,“心灵自由”似乎是彻底的外来物,在这个词舶来之前,中国人好像对“心灵自由”没有任何理解,许多人因此认为中国人自由精神的觉醒是在五四之后。然以此而论则中国人创造的五千年文明就显得难于理解了,缺乏心灵自由的人民却产生了《诗经》、《庄子》、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极富想象力的作品。由于文学作品不具视觉艺术的可直观性,一个时期的辩证唯物史家于是有理由说——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过是以表面的丰富想象掩盖了其本质的奴性罢了。故此近代激进的反传统人士希望通过破坏古典文明来实现自由王国,其成绩就是破坏造成的灾乱,此外一无所有。当然,废除汉字,实现拉丁化,打倒孔家店,不读中国书,这些都没有做到,破坏之外没有建设的成绩,转了一圈还是要回到传统的起点。
(一)
我们说中国人作为一群高智商的庞大历史性群体并不缺乏心灵自由,文明遗产中一个最为杰出的艺术门类由于在西方的文艺中没有对应者而被忽视了,这个被忽视的艺术门类反映的中国人心灵自由之高妙甚至达到了古希腊古罗马人没有达到的境界,这个艺术门类对自由精神的直接反映是高度概括而凝练的。以“抽象的形象”反映心灵自由的方式在西方艺术的古典时代极为稀缺,西方只是到了近现代才在他们的抽象艺术略为体现,但与中国这门被忽视的成熟艺术比较起来,显得幼稚和初级。这个直观地表现中国人自由精神的艺术门类就是书法。
书法之被忽视,很大原因在于它的普遍性与它的神秘性。所谓普遍性,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书写太普通了,由于古代有文化的人都能够以毛笔书写,书写作为艺术似显得不纯粹,曾听到某个艺术理论家认真地说书法不属于艺术,其论据之一是在西方艺术门类中没有书法,之二是他家门前收破烂老头儿也自称是书法家。所谓神秘性,就是对于西方人来说,汉字是世界上颇难学习的文字,汉字书法在他们的眼里是天书一样使人眼花缭乱的点线杂凑,由于文化传统的隔膜,即使认识中国印刷字的汉学家中能真正领悟汉字书法之美的人士也很少,这样,汉学家就无法把汉字书法所蕴涵的美以西方熟悉的文本表达出来,而使得西方的哲学家或思想家理解汉字书法的意义——它所包藏的中国人的自由精神。
以存在论来理解艺术,艺术就是精神者在世界上留下的痕迹,世界就可看作是最高精神者(上帝-上天)的艺术作品。不过就人类的一般艺术观念而言,最高精神者的艺术品是天成的,宏大如高山、河流、平原乃至遥远的星系,微小如花卉、鸟兽、虫鱼,因其属于自然,尽管蕴涵无尽美好,在人类的艺术眼光看来,自然万物不是人类的艺术品因此不叫艺术品。蚂蚁修建自己的高楼、蜜蜂建立六边形蜂房也不算艺术品,因它们的精神还处在极低微的阶段,未达到人类精神的自觉。是否人类一切痕迹都属于艺术呢?就艺术的广义而言,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想了解某个已经消失的文明,他们所遗留下的一切痕迹都反映着他们的精神完善的程度,房屋、生活用品、劳动工具无不向我们诉说其文明进化的状态,因此我们都以欣赏艺术品的眼光来打量他们遗存的一切人为痕迹。但在一个正在持续发展的文明圈内,由于生活用品的实用性和制作工艺的机械性,它们所蕴涵的精神性显得微弱,除了特别的命意(现代艺术家把便器拿到美术馆题写新的标题而参加展览),一般不认为是艺术品,而只有那些表现了创作者独特构思、显示强烈的精神性的痕迹才被认为是艺术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定义——只要显现了人类精神性的痕迹的东西都是艺术品,反过来说,一个成功的艺术品的意义就在于它充分显示了人类心灵之独特的精神自由。书法作为高度抽象化的中国人精神流露的痕迹当然属于艺术,而且是西方人渴望达到却没有达到的纯粹、独特而高妙的艺术。
的确,西方没有与中国书法艺术相对应的艺术门类。西方语文的书法尽管也有美与不美的区分——他们也很注重手笔的美观,他们关于笔迹与性格的关系甚至还形成了一门笔迹学学科,但西方的书法并没有发展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他们对于书法的美只局限在装饰性的美观,这是由于:其一,他们的书写工具(笔尖)的微小和坚硬——没有毛笔的可大可小以及笔锋弹性的粗细变化;其二,他们记录声音的字母文字的单调横向排列没有中国汉字作为视觉文字的空间性。
毛笔笔锋柔中寓刚的粗细变化是与中国民族性格以及他们的自然地理环境一致的,正像黄山云海只有用水墨表现才最为恰当,中国人宽广的胸怀和丰富的自由精神也只有以书法表现最为贴切。太巨大或太微小的工具都不适合精神的艺术表达,所以高山大河只配上天的杰作,而微雕工具或绣花针只能归为特别的工艺,至于人类的高级艺术,工具所实现的作品必需与人体的高度和眼睛的视觉相匹配,而毛笔正是这样一件使心灵自由到达世界、既顺应手臂又延伸了手臂——对于自由运用毛笔的人它仿佛是身体的一部分——的大小适中的工具。而墨的黑色与宣纸的吸水性使毛笔在运行中表现出含蓄而内敛的线条痕迹,使“有意味的形式”达到了简练与生动性的极致,当然,这一切又与汉字的造字法天然地互洽。中国汉字竖行排列使汉字的末笔正好顺应下一字的起笔,这样,不同取势的单个汉字一经书法高手自由地排列,便构成变化无穷而又流畅的点线造型,其连绵起伏的笔迹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使书法家可极尽展现自己的想象力。
(二)
中国汉字的象形性使它与自然万物保持着有机联系——这是与中国有机自然主义文明传统一致的,记录视觉形象的汉字比记录声音的字母文字高级还表现在视觉器官是人体的第一感觉器官。尽管字母亦有自己的形象,而且欧洲语文的字母形象也来自于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但当初腓尼基字母的形成是腓尼基人为了商业化实用的便捷,这样其字母形象对于声音的记录就脱离了与自然形象的血肉关系,使其一开始就是实用的文字,而非如中国汉字是艺术化的文字。汉字作为视觉艺术化文字表现在其空间的开放性,而这种空间的开放性就使精神者表达自己的心灵自由开辟了多向度的可能——这也是中国汉字有如此众多书写形式的原因,所谓汉字作为视觉艺术文字的开放性的意义是——每个汉字都可在平面空间三百六十度自由取势,而欧洲语文的单词之字母的平行排列限定了只能向右上或右下取势,汉字如建筑物的多型体,而字母文字只不过是字母构成的直线,体的空间性和直线的非空间性在书写时表现力的自由和不自由的区分是明显的,汉字作为空间性文字和字母文字作为非空间性文字的分殊决定了中国书法艺术是人类最高级的视觉艺术,而欧洲字母文字的“书法”意义只是工艺性的美观——如他们漂亮的花体字。
中国书法艺术之作为蕴涵大美的视觉艺术,不仅在于汉字作为点线的载体在平面空间上的变化的无限可塑性,而且书法家的想象力又有坚实的传统为根据(不是紊乱的变化)——即汉字书法以历史中形成的结字法为内在规定性,而凝聚了丰富的自然与心灵之含义的汉字所构成的诗文又内在于书法墨迹中——草书结字的可识性使书法艺术表现出的意义在视觉意象与诗文意象的互相启示和联想中愈加丰富。
在中国艺术史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书法家,而且书法艺术是中国艺术中“艺术中的艺术”——在诸艺术门类中是基础性的,可以说中国的视觉艺术——绘画、雕塑、舞蹈——无不以书法为造型基础——中国艺术中的风骨是书法的线,甚至中国的听觉艺术(音乐)也与书法有着本质性的联系。
书法之作为一门艺术并不能保证任何一件书法作品都是艺术品,就像并不是把色彩涂抹到画布上的作品都是合格的绘画作品一样。书法有低级的功能,书写汉字总是对身心有益,所以孩子们可以在毛边纸上随意练习或老人为健身而蘸水在公园的地上书写,书法不区分高低贵贱,它允许一切人以它的名义表达自己的情怀;书法还有高级的功能,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比书法更能表现自己胸怀的艺术了,历史上的书法杰作是人类精神的奇迹——显现心灵自由的奇妙痕迹。
精神性表现出高度自由是以物化的时间中的空间来实现的——这是书法艺术之区别于任何一门西方艺术的地方。心灵的自由必须通过物质的中介体现出来,绘画使用色彩,雕塑使用石头、青铜、木材等材料,音乐借助声波,中国书法则借助宣纸和黑色墨汁。心灵自由是内心的活动,人的自由之不同于石头的滚动在于他的行走是自主的自为活动——人以自己肉体的活动显示心灵的自在;释迦牟尼可以不说一词来说法,但他手里毕竟还拈着金色波罗花,就是说,没有物质的中介则心灵的活动无法体现出来。任何视觉艺术都是空间性的,因为艺术的中介物都占据空间,但书法之不同于一般视觉艺术在于它还具有时间性。一个绘画或雕塑作品的完成固然需要时间,但一个完整的绘画或雕塑作品是它的整体性进入你的眼帘,没有如音乐那样有一个时间的开始和结束;一个音乐作品不是指写在纸上的音符,而是通过乐器演奏出的声音,但声音是随着时间发生并消失,并不像绘画那样留下痕迹。但书法艺术既有绘画的空间性又有音乐的时间性,一件书法作品是由一连串的汉字组成,欣赏书法就需要像欣赏音乐那样有一个开始和结束,这是它的时间性;而它又比音乐多了空间性,就是它的过程是以可见的线条来完成,而线条是在纸上的空间表达出来的,不是如声音那样会在空间中消失。书法艺术这种独具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的结合就使书法的表现力超越了空间性的绘画和时间性的音乐的表现力。
草书的美妙在于线条变化的丰富性。希腊人也知道曲线是最美的,但他们却没有纯粹线条的艺术,他们的曲线是附丽于描述真实物象的绘画或雕塑的人体或服饰的皱折中。驾驭毛笔比驾驭画笔或刻刀需要更多功力是由于毛笔的柔性。毛笔的柔性对于手指力度的敏感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心灵的微妙变化;这一点只有独奏演奏家演奏音乐状态可与之相比。相对说来绘画尽管也能反映心灵自由,但由于绘画可以反复修改,则画家可以把自己的真实心灵伪装起来。
在中国书法艺术中,草书是书法艺术中的最高形式,因它最富表现力。王羲之以后历代都不乏书法大家,但草书发展到最高峰——表达出极具个性和丰富想象力之高妙境界的是唐代书法家怀素。我们说怀素前的王羲之和怀素后的王铎当然都是伟大书法家,但单就草书成就来说,怀素是最高峰,他把中国的草书艺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后罕来者的地步。
中国的文化至唐代发展到极为辉煌灿烂的阶段,与之前的先秦和魏晋并列为三座高峰。唐人的心灵秉承汉魏六朝遗风最为自由开放,由于国家以诗取仕,诗人艺术家遂在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识字者几乎人人都有诗人艺术家的涵养(甚至连强盗都崇敬名诗人),此时在诗人艺术家中脱颖出天才人物也就显得很自然。怀素与李白、杜甫基本属于同一个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有其共通性,李白奔腾豪放的诗风是对盛唐以前诗歌传统的总结,而怀素的书法则是对西汉以后兴起的草书艺术的总结,二人的艺术成就当然是由于个人天才,而其个人天才之能实现则是中国人精神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逐渐累积而成熟的结果。
(三)
接下来我就以怀素草书《自叙帖》为例具体说明中国书法艺术所反映的中国人心灵的自由性。对于不了解怀素及其书法的人,这里对他的介绍是必要的,在对怀素有一个基本印象后,我们再分析怀素的这件杰作之超越西方艺术品之处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怀素之前草书已经有了八百多年的发展,西汉以前尚无草书,不过我们现在从秦简、楚简依稀看到书者为追求速度而流露出来的些许流动的意趣(此乃草书之能发展的渊源)——这是甲骨文、商周青铜器铭文缺乏的。我们因此理解书写的“写”是草书之能发生发展的前提,而写的工具毛笔实在可说是中国人的大发明,没有这个发明则草书发展到成为表达心灵自由的高妙艺术是不可能的。草书尽管与追求快速书写的草率有关,但草书不是不认真的草率,将汉字笔画连绵、省略、概括而形成有规定性的结字法,在记录内容的同时表达出书写者的风度气质——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与自觉的结合,我们看草书巧妙的结字法蕴涵着先民的想象力和智慧绝非不经意所能成就的。草书在唐以前已经产生了有影响的名家,如怀素《自叙帖》里提到的东汉时期的杜度、崔瑗,而东汉人张芝,三国吴人皇象,西晋人索靖、卫瓘以及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也皆以章草、行草书著名。虽然张芝的草书已显露出超越章草而向大草的过渡形态,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草书法度森严,但普遍地来看,这些草书家都比较理性而不够“狂”,真正意义的狂草是从怀素同时代的张旭发端的。我们现在看张旭的《古诗四帖》(传张旭书)连绵起伏、浩荡沉雄,李白曾称颂张旭:“楚人尽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追随”,是说张旭的个人魅力,而就书法而论,吾人以为张旭与怀素狂草相比显得还不够狂狷,其线条质量也还没有达到怀素那种能在快速书写中保持的圆转、瘦劲、生动和凝练,所以我们说狂草书的高峰——得草书真精神的——是怀素。
“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这是怀素在《自叙帖》里的第一句话;《宣和书谱》记载与他的自叙一致:“唐释怀素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人,徙家京兆,玄奘三藏之门人也。”怀素是唐长沙郡零陵人,生于公元725年(即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另说生于开元二十五年,即公元737年),活了大约六十三岁。他自幼出家,《宣和书谱》说他“初励律法”,这里“律法”是音乐律吕的法度还是学习佛教的律学,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他对书法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其他,遂专攻草书,一生留下大量书迹。至宋徽宗时御府所藏尚存一百零一帖,经过千年水火兵燹传至今日算上刻本也不过十几帖了,好在他在大历丁巳冬(即公元777年,若他生于725年这一年他五十二岁,若生于737年这一年他四十岁)所完成的杰作《自叙帖》流传下来(《自叙帖》前六行并非怀素所书,而是损毁后由宋人苏舜钦补书的,不过基本衔接了怀素草书风格);《苦笋帖》、《小草千文》亦其力作。
关于怀素学书的经历以及当时人对他书法的评价在他的《自叙帖》里叙述得很详细,在这里略微复述一下。这些叙述生动地再现了怀素艺术的独特个性和使人震惊的表现力。我们说怀素在书写时的这种癫狂状态是艺术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不是孤立的现象,它足以说明中国人的心灵自由所达到的高妙程度;在我的复述中读者也需要留意中国古代艺术评论的象征式与今日分析式的区别。
怀素在《自叙帖》中说“经禅之暇,颇好笔翰,然恨未能远覩,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是说他不满意自己的见识而往游名都,而在他游历当时文化中心长安之前,他已经下苦功练习草书并且早已闻名乡里。他曾拜张旭的学生邬彤为师,相传他勤奋学书以至笔秃成冢,又广植芭蕉,以芭蕉叶练书。后世文人画家常以怀素芭蕉书题材入画,曾见近人徐悲鸿先生作芭蕉图即描写怀素在芭蕉叶作书的情景。第一次游历长安时怀素领略了历代名迹,书艺因之一进,且其奔放豪迈的艺术气质和挥洒自如的狂草墨迹名动公卿。自长安返回家乡零陵途中,怀素曾与另一位唐代伟大书法家颜真卿在洛阳相见,颜真卿对怀素草书十分欣赏,为《怀素上人草书歌集》作序。二人论书的对话在唐陆羽《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中留传了下来,书评中常见“折钗股”(怀素转述张旭语)、“屋漏痕”(颜真卿语)习语即从二人论书中来。怀素领悟笔法固然在学习前辈书家名迹,而更在于他在自然中的领悟,“一夕,观夏云随风,顿悟笔意,自谓得草书三昧”(《宣和书谱·草书七》)。怀素草书得飞动之势的另一个媒介是——酒,“考其平日得酒发兴,要欲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宣和书谱·草书七》)。诗人陶渊明、李白平生嗜酒,酒对于艺术家达到忘我境界的确大有作用。
怀素书法在当时已经获得广泛赞誉,《自叙帖》中(这里只截取韵文部分)叙张礼部云“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卢员外赞谓“初疑轻烟淡古松,又似山开万仞峰”;王永州邕曰“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朱处士遥云“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之畏盘龙走”。李御史舟则把怀素与张旭并论,“昔张旭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余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何曰不可”。而许御史瑶是这样描写怀素作书癫狂状态的:“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戴御史叔伦云:“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窦御史冀描写了怀素在粉壁上作书的疾速情景:“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戴公又云“驰毫骤墨列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这些评价采取艺术夸张的手法让人意会怀素作书时“迅疾骇人”的状态,三五声绝叫之中粉壁上飞满千万字——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如此描述则传神地表现出怀素作书时酣畅淋漓、激越飞扬的精神状态。《自叙帖》中怀素把著名诗人钱起的诗放在了最后,在评价怀素草书的诗文中,钱起诗之境界最为悠远:“远锡(鹤)无前侣,孤云寄太虚。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怀素外在狂傲所蕴涵的内在“真如”法境以孤云鹤影之喻跃然纸上。怀素对于别人的赞誉叙述之后自谦说,这些评价“皆辞旨激切,理识玄奥,固非虚荡之所敢当,徒增愧畏耳”。
《全唐诗》中收有李白对怀素草书的赞美诗《草书歌行》:“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意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诗写得汪洋恣肆、气势恢弘,使我们如身临其境地体察怀素作书时的情态以及当时人们对书法家的追捧,李白诗歌语言的夸张正与怀素飘动而又不失沉雄的书风暗合。然宋朱长文《墨池编》认为此诗乃怀素自作,托名李白。而我们细细品味诗句,的确李白家法,而怀素擅书不擅诗,《全唐诗》仅存怀素诗两首。怀素的表现欲与李白相似,但自我表现中反观自我很难,像“倚绳床”这样的细节非旁观者不能道出。
关于草书的评价,古人使用的语言与我们今人的语言有所不同,若把当时唐人对怀素草书的赞誉总结一下,他们的意思其实无非是两个字——自由。中国历史上的天才人物表达自我傲世独立的自由品格如惊鸿游龙般翩婉,而不像西方人那样直白外露,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温和的气候和平原山川的博大壮丽使然。怀素狂草显现的唯我独尊的个性自由也就极具东方精神,观其草书就好比观赏黄山云海中莲花峰,氤氲缥缈之中偶露峥嵘,又如老僧入定,虽风云激荡而法座庄严,佛音琅琅中使人如见百千亿万法驾浩荡下崦嵫,旌幡森列弥漫云天,虬螭骖驾飞舞虹霓,忽然以电闪雷鸣作狂禅狮子吼,定睛看万法归一——自然天真,朗月中天万籁寂,朵朵莲花开海宇。
以自然而喻自由是中国人形象思维的特点,以书法艺术而论,如袁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如张旭“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如李白“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如孙过庭“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种种摹状在说草书家所达到的忘我自由之化境。《自叙帖》从起笔的舒缓平和到逐渐奔放纵横到最后在狂放恣肆中戛然而止,犹如我们由远及近地观赏奔腾的大河,其一泻千里的气势内在于精美而凝练的点线之中,前后首尾贯通、自然流畅,没有任何懈怠或失笔,所表现出的心灵自由是人类精神在数千年持续的修炼才能放射出的光华。《自叙帖》像灯塔一样孤悬在文明历史航程中,今天能面对此旷世奇迹实在是我们的幸运,对于它达到的艺术高度,作为后人的我们只有敬畏。
(四)
古代艺术语言的象征性评价固然传神,但对于已经丧失了对书法直觉能力的大多数现代人而言更倾向于接受西方分析式评价。好在我们的视野比古人要宽,信息的畅通使我们能够对世界各个文明圈创造的文艺作品进行比较,现在我们就来指出怀素这件草书艺术作品超越其他文明的艺术品的地方,我想说明它在世界艺术史中应当的高标地位与世人对它的陌生的反差是很大的。
比如我们拿古希腊雕塑家米隆的“掷铁饼者”与怀素《自叙帖》里的单个文字比较——首先必须明确不同艺术门类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二者都包含着两个因素:一、稳定性;二、飞动性。两件伟大作品是这两种因素的有机统一体,稳定性中包含着飞动,飞动之不轻飘是因为稳定性,从这种意义说,古希腊人雕塑杰作与中国书法杰作所表达的精神是相通的。但怀素的草书还有古希腊雕塑所不具备的东西,“掷铁饼者”描述了一个具体的人的形象,而怀素草书《自叙帖》的任何一个字都不是现实中的物象,不是具体物象却能表达具体物象的情态,这是抽象艺术的特点。与这种抽象艺术比起来,形象的绘画或雕塑都显得不够纯粹,绘画的色彩、雕塑的石头材料都过于累赘,与怀素稳健与飞动合一的书法韵律比较,希腊雕塑作为具象艺术因其肉体形象的拖累还不能使精神向更辽远的宇宙飞翔。
我们再拿欧洲大陆的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奠基人尼古拉·普桑的作品“海神的凯旋”与怀素的草书比较,能使我们进一步领略怀素草书杰作的纯洁性。二者的可比性在于两件杰作都擅长于制造矛盾和化解矛盾。普桑的画面是肉体的色相(人物)与自然的色相(云海天)的狂欢,而怀素书法是点与线的狂欢,大师们那种驾驭复杂画面的举重若轻、赋予看似混乱画面以完美秩序的高超本领、造奇化险与虚实结合的灵动巧妙,都跃然纸上。但我们冷静地观察,就容易发现普桑的作品过于诗意昂然了,画面描写的是海神,可那赤裸的肉体太世俗化;但怀素点线冲突中的宁静宛如宇宙黑幕之上上演的飞龙的舞蹈,没有丝毫尘世的沾染,我们若截取怀素草书的任何一个片段标上“海神的凯旋”都比普桑的作品更为寓意深刻。普桑的海神显然没有达到中国书法线条的力量——以墨线的痕迹表达不露痕迹。中国书法的线(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字的造字方式)是与中国哲学《易经》图符一致的,汉字作为“图符”的哲学表达方式在世界其他民族是没有的,它显示了中国人对宇宙本质的天才领悟——符号与具象关联但并非具象,在书法的“抽象的形象”面前,西方绘画一切拟人化的肉体形象都显得有些俗庸。
对这种俗庸味道的厌烦是现代西方艺术家试图找到一种纯粹艺术的表达方式——思考如何把精神性表达在非具体形象的形式中,他们对东方艺术的借鉴使他们发展了现代抽象艺术。印象主义绘画不过稍微接近了中国画的描述方法,因中国人的绘画艺术从来都不是刻板地重现物象,而是表达主观印象。西方抽象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之一是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绘画,但他们的抽象显然是不彻底的,仍然没有舍弃形象,只不过用肢解的形象或怪诞或简约的形象消解具象与色彩的庸俗罢了。康定斯基想找到像音乐一样纯粹的非形象符号,但音乐的时间性无法在他的画面上再现,这使他的抽象作品显得支离零碎而不能企及音乐旋律与中国书法点线连绵之韵律美。现代抽象艺术日渐驳杂,像走不出迷宫的人在迷宫里胡乱冲撞留下的痕迹,我们在世界各国美术馆经常看到那种寻找舍弃具体形象而表达心灵自由的视觉艺术形式的不成功的尝试。现代艺术似乎就是一大批尝试用抽象符号表达内心感悟的失败历史的记录。我们作为中国人便能鲜明地领悟到他们那种欲达却不能达的渴望——试图趋近的理想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则一定程度地实现了,此艺术形式就是汉字书法。书法艺术之汉字抽象符号非与现象世界无关,而是与自然万物有机相连,但又绝不重复自然万物形象。草书对汉字抽象符号的再抽象是一种极具表现力的变形,这种变形具有广阔的无限性而又非没有凭依,这表现在传统草书结字法的规范和前辈书家杰作的典范使草书作为抽象艺术有法可依。汉字书法作为抽象艺术深具现代性又植根于古老而丰富的文明传统中,这是西方现代艺术绝没有的。西方抽象艺术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成熟的语言。所以我的一位朋友的诙谐就显得特别深刻:“西方人太可怜了,不懂中国书法。”
也许只有天才音乐家莫扎特的音乐艺术可与怀素的草书相比。不过拿书法所表达的心灵自由性要求更多音乐家可能仍使他们力不从心。一个音乐作品的创作是否如书法家一气呵成暂且不论,而要求演奏家如书法家那样不按照既定的作曲家的作品而即兴创作——似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一场音乐会可以是作曲家兼演奏家即兴创作而能成功的,但书法家如怀素就是此种意义上的创作。所以也只有莫扎特能和中国书法家相比——莫扎特的任何即兴演奏都是杰作,实际上不仅怀素,就是逊于怀素的其他大书法家都是一次性创作,他们可以书写相同的内容,但由于书法的表现不单是文辞而是书法“抽象的形象”,因而每次书写都表达他彼时彼刻的心灵状态,毛笔笔锋的弹性以单纯的点线的变化微妙地记录下他的心灵历程。由此可见,尽管西方音乐艺术达到了极高的成就,但与中国书法艺术比较起来还不够纯粹,没有显示出心灵表达自我自由精神的历史性的一次性——不可重复性,尽管演奏家每次演奏也有微小的差别,但不是书法意义上的历史性创作。
关于自由的理解,中国古人好比一个射箭高手,略视靶子而全凭感觉就能准确地射中靶心——哪怕它是游动的目标,但若问他如何感觉而射中的却不能言表——“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而西方人研究弹道,细致地以数学的精确描述了箭穿靶心的原理。以工程学论,后者胜于前者;以艺术学论,前者胜于后者。当然对艺术的逻辑分析——怀素如何达到了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对于我们这些基本熟悉西方思维方式的人是应该做的,但正因此我们遗失了那种不靠逻辑思维而全凭直觉达到自由境界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能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而认为——由于中国古人不懂得如何描述他们达到的自由境界,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懂得自由;倒是我们这些只会说不会做的人已难能实践古人那种画鹿忘蹄、得意忘言的自由了。
如果今人刻板地只以字面的“自由”理解自由,那么的确中国古籍“自由”并不多见,把“自由”在图书馆古籍善本书库的电脑里搜一搜,“自由”二字的确很少见,罗隐有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之“自由”是生活语言中自我意志实现、自己做自己的主的意思,没有像西方人那样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被反复论述。但没有字面上的“自由”两个字并非说中国人不理解自由理念的涵义,无论是庄子的“逍遥”,还是钱起描述怀素书法的“醉里得真如”的“真如”翻译成今日语言都与“自由”的理念论意义相关。《自叙帖》表达的怀素的心灵自由是今人望尘莫及的,书法杰作所反映的中国人的心灵自由达到的高妙程度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中国人的自由精神因而没有得到世界的公正的评价,这是我们必须改变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