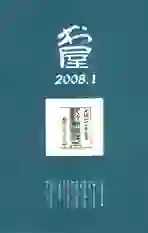中国文学的西天
2008-12-29周泽雄
书屋 2008年1期
这事儿真让人沮丧!除了汉学家,我从未在某位西方文人笔下,读到他们正儿八经地评论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或一位好歹有点名头的中国文人。虽然孤陋寡闻是原因之一,但我相信,这个“之一”也就是百分之一的意思。
俄国形式主义之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论》一书中,曾辟出专章讨论“中国小说”。对这位大批评家我佩服有加,但听他谈论中国文学,我只感到一头雾水。是的,他笼统地、空泛地议论着中国文学,好像中国文学不是由一个个响亮名字、一部部非凡作品构成(像他心爱的俄罗斯文学那样),而是只配以“文化现象”为聚焦单位,被大而化之地概括一下。你瞧,什克洛夫斯基提到了一些小说,谈论的方式却缺乏文学上的针对性,别说普通读者,即使专业研究人员,有时也不清楚他在说哪部作品,以致我们的译者竟然狼狈到只能用译音法,标注他提到的某个小说人物:季安。对一位有尊严的译者,这么做不无屈辱,因为那等于承认自己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
什氏还提到一篇小说《围棋手》,读其简略复述,分明就是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里的《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但我们的译者依旧拒绝还原,听任“围棋手”这个脱离时代的标题兀立在明清小说的上空——不过,本文不在讥讽译者,我甚至觉得,译者偶有闪失也情有可原,问题出在大批评家身上。什克洛夫斯基对中国文学的讨论实在有点漫不经心和言不及义,这会对译者构成不良诱惑,使他觉得,逐一核对作者提到的中国小说,属于不必要的严谨。何况,什氏有言在先:“我说这些话时有自知之明:我并非东方学专家。”那意思是:如果我说岔了,各位就多多包涵吧。
我见识过什克洛夫斯基如何以激扬而高明的文学批评手法评论本民族作家,如托尔斯泰,也领教过他对欧洲文学经典所做的动人分析和热情礼赞,如《安提戈涅》、《麦克白》,以之对照他谈论中国文学的方式,反差太过强烈。就像人们谈论巴西球员和中国球员时,会本能地把他们视为两类人一样,什克洛夫斯基谈论中国文学时,同样与他谈论西方文学经典的方式拉开了距离,仿佛那是两码事。他的“自知之明”也说明了这一点:东方学。众所周知,“东方学”不是一个文学概念,而更像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若结合爱德华·萨义德的见解,“东方学”现在还是一种政治学概念。总之,什克洛夫斯基与其说是在评论中国文学,不如说是在谈论风土人情,中国小说在他眼里不再是文学上的考察对象,而是一只盛满异国情调的容器,或者,一组供他展示多元文化观的典雅题材。对后者,我们早已见怪不怪。
我经常发现,一些西方人提到中国文学,不是为了谈论文学,而是显示自己视野的空阔和胸襟的博大,中国文学成了他们卖弄文化外交辞令的绝佳舞台。比如,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就特别喜欢嘴里带上一句“中国格言”,对他们来说,中国是否有这样一句格言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他借此显摆了一下自己。他们可以把任何一句想不起出处的漂亮话,都说成是“中国格言”,反正没人会追究的。众所周知,欧美人还有一个口头禅,为了说明一件事物的复杂性或古怪性,那句永远现成的比喻就是:“像汉语一样”。欧美人谈论中国文学,说对了,可以让自己赚一些风雅分;说错了,还没等你道歉,别人已抢先原谅了。更常见的情况是,你说对还是说错,没人在乎。
什克洛夫斯基为了壮大行文的声色,还援引了“卓越的中国专家弗·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见解。那是一种怎样的高见呢?且听他说来:“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不只是作为一套丛书中的陪衬或孤零零的一册。如果说成为现代欧洲文学基础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学就其意义可以称为世界文学,如果说在它们影响下成长和繁荣的欧洲各国文学由于彼此相互影响因而也成为世界文学,那么完全有同样多的理由可以断言,中国文学就其意义而言是世界文学。”
虽然啰哩啰嗦,我还是听明白了,即使在这位权威眼里,中国文学也只是“就其意义而言是世界文学”而已。这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文学外交辞令?其引而不发的含义分明是:当然,就其现状而言,中国文学还谈不上“是世界文学”。
的确,这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莎士比亚没有听说过关汉卿,托尔斯泰不知道曹雪芹是谁,拜伦没有读过李白,罗曼·罗兰不曾评论过鲁迅,马尔克斯不清楚《西游记》的“魔幻”性质……这些一概很正常。事情的另一面是,只要是西方文豪,不管他因为什么原因凑巧说了句与中国文学沾点边的话,都可能引起我们莫大的激动。比如,伏尔泰提到过一部名叫《赵氏孤儿》的中国作品,哪怕这部作品在中国历来乏人问津,我们照旧心怀感激。歌德的例子就更有代表性了,这位率先提出“世界文学”设想的超级文豪,晚年与爱克曼聊天时也提到了中国文学(有趣的是,他就是在提到中国文学时,首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在日常阅读中,我无数次见到国人引用这段谈不上高明的见解了。关于歌德的说法,且听爱克曼的叙述,时间是1827年1月31日:
与歌德共进晚餐,他说:“上次见你之后这几天里,我读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一部中国小说,现在还在读。我觉得它很不寻常。(爱克曼插嘴道:“中国小说!看起来一定够古怪的。”)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古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与我们一模一样,只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比我们更清楚,更纯洁,更正派。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井然有序、中规中矩的,没有巨大的激情和飞扬的诗意……他们还有一个与我们不同之处,在他们那里,外部的自然总是和人物形象联系在一起……还有无数其他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事物上的严格节制,使得中华帝国维持了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歌德后来又拿那篇他始终没有提及名字的中国小说,与一个叫贝朗瑞的法国文人的作品进行了对比,并发现了些“极为鲜明”的区别。“请你说一说”,歌德郑重其事地提醒爱克曼,“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当今法国头号诗人却正好相反,这难道不是十分值得关注吗?”
也许吧,这“十分值得关注”,尽管在我看来,歌德更想关注的不是中国文学,而是遥远的中国人。那洋溢于歌德内心的与其说是文学热情,不如说是一种对于异国风情的好奇。这类好奇,也恰到好处地体现出西方人文巨子所特有的旺盛求知欲,类似歌德阐发的“浮士德精神”。貌似奇怪而实则不足为怪的是,歌德明明在读中国小说,得出的结论却是关于“中国诗人”的。看来,他都懒得区分中国小说家与中国诗人的区别了(尽管在我们眼里,冯梦龙和纳兰性德不宜混为一谈),中国文学在他眼里只是一个了解域外文明的窗口而已。这不是我的推测,紧接着,歌德就对爱克曼谆谆出一段下文:
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出周围狭窄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就会过于轻易地陷入那种学究气的自高自大。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民族情况,也奉劝每个人都这样做。现在民族文学是个毫无意义的说法,世界文学的时代就要到来了,每个人都应该加倍努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泥于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楷模。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贝龙根》就可以成为楷模。不过,如果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楷模,我们就总要回头到古希腊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忠实地表现了人类的美。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只应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
至此,我们已能看出歌德的真实态度:他文学心目中真正的圣地只是来自古希腊,如中国文学这样的域外文学,他只要了解一下就行了。而且,还必须用“历史眼光去看”——居然不是文学眼光!他们打量中国文学,与他们考察布须曼人的习性、挖掘爱斯基摩人的美德,看来属于一回事。肯定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的若干长处,有助于体现他们自身的优雅教养,拓展他们的文化视野,但这绝不等于说,他们打心眼里认为,中国文学乃是可与西方文学分庭抗礼的伟大传统,值得他们花费相同的功夫深研密思。“(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A.法朗士有一天参观大英博物馆,对希腊著名的大理石雕刻赞不绝口”,大英博物馆东方馆馆长劳伦斯·比尼恩在《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一书中写到,“而当我表示要给他看一尊中国的罗汉雕像——这件雕像刚刚搞到,尚未展出——的时候,他却断然拒绝了。‘不用,不用’,他说,‘希腊人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它的美是取之不尽的’”。
2006年末,一位名叫顾彬(Wolfgang Kubin)的德国汉学家,在中国文坛掀起了巨大波澜。在我们未及对顾彬先生喊一声“来将通名”之前,德国老头的言论就把大家惹火了。一时间,针对顾彬的批评沸反盈天,仿佛我们的文学大陆遭到了强敌入侵,需要再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歼灭来犯之敌。当然,正如多元时代的常规景致那样,有人被他激怒,就有人为他叫好。在批评者看来,那些为顾彬叫好的家伙,有文学汉奸之嫌。
炒作时代的特征是,任何一个舆论热点,仅仅三个月过后,就会变成一堆过期食品,无人问津,“顾彬热”也难逃此劫。回头来看,此事值得回味之处,不在于顾彬先生说了些什么,而是顾彬先生的身份:一名俨然来自文学第一世界的学者,他对自甘为文学第三世界的中国文学的批评,注定会成为一大事件。让我尤感难堪的是,无论顾彬的批评者还是附和者,好像都没有读到德国汉学家的完整观点,这意味着,我们愤怒得不是地方,我们那一腔莫可名状的文学正义,只是不幸地成为某些好事记者的佐酒小菜罢了。事后盘点,顾彬先生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乃是通过一些小报记者偷工减料的转述,才传递到读者面前的。这些转述无一例外地省略了论证过程,只是呈现为一个个简单粗暴的结论。通过顾彬先生嗣后的抗辩,我们还发现,这些转述一概具有断章取义的特征和哗众取宠的居心。假如我们把成熟的文学观点比成一颗树,必须有根有干,有枝有叶,那么,被胡乱归在德国汉学家名下的那些断语,不过是一截截脱离了泥土的残柯断枝而已:哦,“中国文学都是垃圾”;哦,“中国作家都是胆小鬼”;哦,“要想成为大作家,必须至少懂一门外国语”……很难想象,若是颠倒一下角色,一位中国教授也用这些呓语式狠话回敬德国文学界,德国媒体竟会为之骚动几天?——可见,那摸不得的,未必都是老虎屁股,兔子屁股更不能任人触摸呢。
由于我至今都没能读到顾彬先生对中国文学的系统批评(我只是听说他是一位成绩斐然的汉学家),故我不得不认为,顾彬事件的真正价值,只是检测了我们的文学心态。我从中得到的初步检测结果是:我们的文学心态极度虚弱,文学界一触即跳、动辄哗然的反应,只不过说明,面对以欧美为主导的当世文坛格局,中国文学的自我定位,尚处于“找不到北”的神经质状态。那些被转述得如此不着调的言论,仅仅因为挂靠着某位欧美汉学家的身份,就使我们的文学方寸紊乱如斯,实在有点丢脸。我们态度上的躁动,准确折射出我们文学立场的动荡和飘摇。它似乎意味着,大多数中国文人已在内心确认了西方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领导兼统治地位,剩下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像土耳其人当年渴望加入欧盟或日本人声称“脱亚入欧”时所表现的那样,迫切希望加入那个由古希腊和罗马人开创的伟大文学传统,以便让中国文学全面接受“西方正典”的艺术体检,让那些曾经检验过莎士比亚、但丁、普鲁斯特的西式仪器,来全面评估中国文学的艺术体质?
换个角度说说。对一名当代中国的文学工作者,把文化主要分成中西两大类,把由《诗经》、《楚辞》所代表的中国文学传统,与由《荷马史诗》所代表的西方文学传统视为等量齐观、双峰插云的两大文学渊源,已经算一种自觉而又自然的文化体认了。这类转变,原非一蹴而就,毕竟,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里,中国文人曾是恁般眼高于顶、目中无人,在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天下观里,他们习惯于将本民族的作家诗人,视为唯一值得尊崇的文学巨子,从来懒得承认他人。比方说,当南朝诗人谢灵运放言“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时,他可不曾担心曹子建是否“多收了三五斗”,更没有想过要匀给西方人、波斯人、印度人四五斗,而是把中原直接等同于天下。十八世纪英国文坛祭酒约翰逊博士在谈到伦敦的优势时曾说道:“我敢说,我们现在坐的地方周围十里内的知识与文化,比全国其他部分加起来还多。”以谢灵运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文人心里,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中原一地的“知识与文化”,比中原之外的“其他部分加起来还多”。所以,我们还得承认,吾人今天形成的这份文化体认,本身已经大幅放低了民族身价,克服了情感上的各种不情愿,得来殊非易事。当今天我们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时,我们更应看到自己的进步。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往前再跨一大步,甚至在文学上也尝试“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呢?
就我而言,我高度尊重西方文学的成就,并且愿意俯首帖耳地承认,在总体成就上,西方文学确实高于中国文学。同时我还认为,中国文人绝对有必要抱着“善善从长”的态度,向欧美人多多学习借鉴。但是,只要我们依旧使用汉字,依旧为自己的文学传统而自豪,那么我要说,中国文学即使不如欧美文学,也不等于它要归化、臣服于欧美文学。中国文学的特质,对于欧美人士具有天然的排斥性。文学的西天虽有万千经卷,却未必适宜东土。我们还得看到,对一名西方作家来说,把文学分成西方和中国两类,却是不可思议的。“中西合璧”一词,在我们这里似乎谁都可以在嘴上说说,而且大家还心照不宣地认为,这是一条值得尝试、直通文学光明顶的大道(至于是否有人走通了这条道,我们又集体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了)。但是,在西方,除了个别领异标新人士,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西中合璧”乃是一条通向文学未来的道路。
文学不是商品世界,无需制订统一的标准,中国文学的创作成果,不必像电子产品那样接受由欧美人制订的行业标准的检验。再则,由于人家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并不大,一些偶发兴趣很可能还是礼节性的,故关于中国文学的成就如何,还不得不取决于我们的独自摸索及自知之明。我们不必因为人家长于我们,就贸然以为自己必须虚心听取人家对中国文学的指指点点。更现实的状况是,人家第一流的文学家——亦即真正在第一线从事文学创作或批评的专业人士——对中国文学甚至都缺乏指点的兴趣,就像我们第一流的文学家,也没有兴趣去评价、指点某个非洲小国的文学事业。中国文学与欧美文学,好像在两个彼此隔膜的大陆上各自发展着,其中一方热衷于派人向对方学习(类似日本当年派往中国的遣唐使),另一方则认为无此必要(请回想法朗士的态度)。断言欧美文人对中国文学的批评意见不值得重视,这与狂妄无关,只是表达一个实情。我们理应重视西方文学,但不必同时重视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评价,理由很简单:人家志不在此。
中国文学中的绝顶魅力,对西洋人是绝缘的,在我看来,西方人似乎只能欣赏些中国文学中相对较为平凡的作品,如“三言两拍”,他们理解不了陶渊明和杜甫,对我们视为无上瑰宝的《红楼梦》,也历来不闻不问。而我们欣赏西方的维吉尔、但丁,虽然也要打掉些折扣,总还可以领略若干。同理,我们欣赏西方的培根、蒙田,几乎不会遇到障碍,但西方文人欣赏我们第一流的随笔家,如张岱、李渔,近乎骇人听闻。我们第一流的当代作家,如鲁迅、钱钟书、余光中,可以极为内行地评论西方文人,而在西方,这类活计似乎只有一些汉学家在干。有些欧美人也能承认,中国人虽然在追求真理方面不太济事,却可以营造出美妙的诗意。不过,这类承认通常也只是泛泛而言,他们并不是结合具体的作品下此结论的。李白的《静夜思》如此让中国人动容,把它译成英语,绝对是一种灾难。日本的俳句与此类似,西方人同样窘于捕捉和体味。中国传统文学中的魅力,相当大的成分来自语言,这类贴附于汉语之上的魅力,固执地拒绝翻译,反观西方文学,虽然也有语言上的障碍,但确实不如汉语显得那么突出和排他。比如,罗念生先生在谈到古希腊文学时就说过,它们“除了一点特殊的宗教情绪和一点文字上的困难外,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语言对于他们的文学,更多地具有工具属性,而在中国文学里,语言不仅不是道具或配角,还常常担纲主演,导致我们读有些作品,甚至都不在乎作者说些什么,只是欣赏作者怎么说,换言之,只是在欣赏语言本身。这种可供欣赏玩味的语言,类似一棵深植在中华大地上的参天大树,很难想象被移栽到异域。一译就死,正是它的命。
说了半天,结论却是这么几句话:一,中国文学应该向欧美文学学习,同时承认欧美文学的总体成就在我们之上;二,聆听欧美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批评,价值不大;三,中国文学自成体系,自具美感,任何脱亚入欧式的行为,都是短视的;四、中国文学的未来,只能由中国文人自己去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