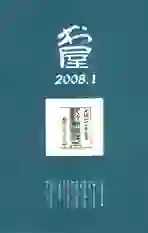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命运
2008-12-29黄波
书屋 2008年1期
说到中国近世以来的保守主义者,人们一般都会想到这样两副面目:一副是倭仁、徐桐的,他们笃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对异域文明一概鄙视和唾弃;一副是陈寅恪和吴宓的,亲历欧风美雨,主张“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问,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鉴于“保守”这一词汇在中国语境中的特定含义,对陈寅恪、吴宓这一群体,也许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更为适当,他们对中国文化怀抱着无限深情,强调中国文化本位,但另一方面,对以“民主”、“自由”为基本符号的普世价值并不拒绝,在他们这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是融为一体的。而在以陈寅恪、吴宓为代表的这一文化保守主义者群体中,胡先骕是一个被埋没、忽视了多年的人物。
其实,即使是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群体中,胡先骕也是非常特异的,因为他是科学家,本行是植物学研究,连毛泽东都称道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众所周知,近代科学主义思潮曾君临华夏,受此思潮洗礼的人,都喜欢用一把“科学”的尺子丈量传统中国的一切,并屡兴“太不科学非加扫除”之誓,而胡先骕是著名植物学家,科学、精密、实证是其应有之义,他为什么却偏偏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这是个并不好回答的问题,而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胡先骕实在是一个很有些意思的人物。
前面说过,胡先骕被埋没多年了,即使是在植物学界中,这个宗师级的先辈一度也是非常寂寞的。1983年中国植物学会在太原召开庆祝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年会,会长作回顾历史的发言,在评价开创性人物的章节中居然没有胡先骕的地位。近年来庐山植物园的胡宗刚先生专力于胡先骕研究,为他写了部“传记”,还为其一生主要事业所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写了部“史稿”,加上前几年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胡先骕文存》,和樊洪业主编的《中国科学院编年史》(胡氏1949年后供职于科学院下辖的植物分类研究所),总算使像笔者这样对胡先骕感兴趣的人有了一点基本的认识。考虑到读者对胡先骕的陌生,先不妨勾勒其一生行事之大端如下:
胡先骕,字步曾,号忏庵。1894年生于江西南昌一个书香门第。曾祖父曾中一甲进士第三名(即探花)。幼年读书时曾受一代大儒沈曾植赏识。1912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攻读植物学,希望“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但他不废研读旧文学。回国后在大学任教,专业著述甚多,开一代新风。和他人创办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又和吴宓等人合办《学衡》杂志,引发新旧文学之争。1949年后在植物分类研究所任研究员,因批评苏联李森科的理论受到批判,文革伊始即遭冲击,终于1968年7月猝死。
这样的粗线条,对准备走进胡先骕丰富内心世界的人来说,当然是不能满意的。那么,且让我们用工笔手法撷取胡先骕的一些人生细节试作剖析。
新旧文化之争中的胡先骕
提及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文学之争,便不能不提到吴宓和由他所主编的《学衡》杂志。《学衡》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学革命大潮中声嘶却气弱的吁求,当年遭到近乎灭顶的攻击,及今视之,也多有不合时宜的地方。现在有人开始做重新审视《学衡》的工作,这个工作大有价值,但一般都只是关注“学衡派”的整体价值取向,个案研究也仅及于吴宓、梅光迪等头面人物,而作为学衡派重要成员的胡先骕却受到了极不应该的疏略。实际上,胡先骕在学衡派中的地位和作用,吴宓于其日记中有清晰的表露。从《吴宓日记》中,我们屡次看到吴宓抱怨胡先骕对《学衡》杂志不尽力,慨叹自己不被同侪所理解。此中似乎透露了这样两点信息:一是胡先骕的支持对维系《学衡》杂志的重要性;二是胡先骕虽然也可归入文化保守主义者群体中,但他远不像吴宓这样对传统文化徒抱一腔浪漫主义,他要清醒得多,他即使坚持自己的取向,但显然并不认为学衡同人的努力就可以力挽狂澜。
对《学衡》杂志的成败,胡先骕虽然不像吴宓那样视为重中之重,但他还是在《学衡》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而其中那几篇关于旧文学的论文,从学理角度论,我以为堪称学衡派最有学术光芒、最不易驳倒的文字。像《评阮大铖咏怀堂诗集》、《评郑子尹巢经巢诗集》、《评俞恪士觚庵诗存》、《评朱古微强村乐府》等文,一望而知,其作者一定是一个深明中国诗词递进历程而又对旧诗创作甘苦深有体味的人。试举《评阮大铖咏怀堂诗集》一文为例。明末的阮胡子先是依附阉党,后又屈身降清,为人所不齿,可是他的《咏怀堂诗集》,尤其是其中的山水诗,自明季迄今,却始终不乏偏嗜者。山水诗是中国诗之一大宗,代代有高手,阮诗有何特异之处?试看胡先骕的分析:在阮大铖以前歌咏自然的名篇,“皆静胜有余,玄鹜不足,且时为人事所牵率,未能摆脱一切,冥心孤往也。惟咏怀堂诗,始时能窥自然之秘藏,为绝诣之冥赏”。胡先骕认为阮诗“非泛泛模范山水、啸傲风月之诗人所能作也,甚且非寻常山林隐逸所能作也。必爱好自然、崇拜自然如宗教者始克为之,且不能日日为之,必幽探有日,神悟偶会,‘形释’、‘神愉’、‘百情有触’时,始能间作此等超世语也。即在咏怀堂全集中,亦不多见,他人可知矣”。胡氏的意思是说,山水诗只有发展到了阮大铖这里,山水才上升为一种本体,不再是诗人遣怀寄意的一种工具,这种对自然的崇拜正是前代诗人没有的。世之好阮诗者众,可曾有谁像胡先骕这样分析得如此精微?这种功夫当然渊源于胡氏的家学,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那种对中国诗词天生的悟性有以致之。
正因为进入了中国诗词的三昧,又尝“寝馈于英国文学,略知世界文学之潮流”(胡氏自语),所以他要力斥胡适等人排倒旧文学之非。他的观点是:“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达意,文学则必于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辞学作文学者,咸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能称文学也。”他又以留洋学者的身份指出当年新文化运动中,“群以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为文学之极则,有谓最高之文学,斯为写实主义”,“此所以在欧美诸邦已陈旧之易卜生,犹能风靡于中国也”。
怎样看待胡先骕对胡适等新人物的批评?据我观察,二者看似剑拔弩张,其实双方之侧重点早已有所不同。胡适等人要以白话废文言,推崇写实主义为文学之极则,他们谈的是文学,着眼点实则在社会,即努力以文学改良来推动社会之变革。而胡先骕却更着眼于文学之本身的规律。双方本来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当年似乎互不相容,现在视之,也许更像一幕喜剧。
回到胡先骕的文学观。他反对日常交际说话、写字就等于是文学,反对丢掉本民族文学中的优良传统,这自然是一种既“保守”又有些“精英”腔调的文学观,在当下的语境中有些“政治不正确”了,不过他自己倒是一以贯之的,直到晚年给著名教育家郑晓沧的信中还说:“新体诗即能自立门户,亦不过另增一新体,未必能完全取旧体诗而代之”,写诗“但问佳不佳,不问新不新”。
“但问佳不佳,不问新不新”,虽是论诗,仿佛也是胡氏的夫子自道。这句话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先骕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胡先骕,同时又是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不仅胡先骕是这样,陈寅恪、吴宓等人也是这样。
这一点并不特别让人奇怪。首先,从学理的角度,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往往都是经验主义者。其次,胡先骕他们这一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已经不可能跨入倭仁、徐桐所置身的那条河流中了,不仅是时代变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远非在理学圈子里打转的倭仁、徐桐等人能比,更因为他们亲自在欧风美雨中沐浴过,而倭仁们对“夷”的各种奇谈怪论却只能停留于“想当然”。一个亲眼目睹了议会民主、自由选举的人,要他认为像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描绘的那种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的生活多么美好,大概是很困难的。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先骕,当然不如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激烈反对以白话取代文言的胡先骕知名,不过,在这方面并不缺乏可以圈点的地方:
在反基督教运动中,胡先骕说:“吾未见帝国主义之害与基督教有不可解之关系也。”对这项声势浩大的运动唱了反调,须知,当时反基督教正是知识界的一种时髦。
在东南大学易长风潮中,胡先骕撰文批评“国民党诋人,动曰反革命,曰资本主义走狗,凡非本党之人,辄视之为研究系”。“东南大学与政党素不发生关系,言论思想至为自由。教职员中亦无党派地域之别”。他虽然声称“予为对于郭校长治校政策向表不满之人”,但仍然力挺被国民党所不容的郭秉文,“综观今日之大学校长,自蔡孑民以下能胜任于郭氏者又有几人乎?”“至谓某为校长某为教授,某与政党关系如何,此何足问?但问东南大学是否受此种政党之影响,是否能保持其固有超然学风耳。不得便谓惟国民党人可任为东南大学校长与教授,凡非国民党人即应在屏除之列”。反对党化,坚持教育独立,这是标准的自由主义者的态度。
胡的乡前辈、国民党人熊纯如主持江西教育,他作为地方名人致函表示:“公主持教育,幸勿蹈广州积习,但知传授党纲,而徒为非国民党之科学家所讪笑也。”“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之外,更须有科学与教育之建设,学生固须有政治常识,然既有政治军事学校,则不可使所有学生徒浪费光阴于政治运动。”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立场。
我们看他发表的以上一些议论,都是即兴之作,证之以他在执掌大学和各大科研机构中的民主作风,这就表明,呼吸了自由空气的人,对自由的信仰已经渗入了他的血脉,与他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持何观感没有任何关系。
胡先骕到底是一个科学家,科学家的一大长处是缜密观察。《蜀游杂感》就是一篇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社会缜密观察的杰作。这是1933年,他和中国科学社同仁应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之邀入川一游后所作,既是游记,也是一篇评论川政得失的政论文,长达近万言,发表在当年的《独立评论》上。这篇文章有两大特点,第一就是缜密的观察。比如四川军阀派别林立为人所共见,如何善后则莫衷一是,胡则断定“四川裁兵屯垦,问题不在退伍士卒之安插,而在如何满足军官之大欲”,“四川裁兵犹有一困难:即为军官一旦兵权既失,地位亦即随之,昔日藉兵力压迫他人者,今且受他人之压迫”。又如他论及四川关卡林立对民生的摧残,说“其间接影响于农民之生计者,较直接重税为尤大。又每因追租过严,使农民节衣缩食贬价出售,造成农产不自然之过剩状态,因之农民生计愈劣。复以此为主因,使农民不得不高利借贷,而债台因以日高”。第二就是独立的判断。按说胡氏既是四川军人请来的客人,沿途之照拂无微不至,理当有所尊礼,但胡氏却斩钉截铁地说:“四川号称魔窟,而魔窟中之群魔,厥为军人!”“四川政治之腐败,在全中国中殆为罕见,大约惟张宗昌时代之山东可与先后辉映。”胡氏可贵的是,他并未因个人的恶感就将旧军人在建设方面的所有成绩一笔抹掉,他评价说:“在诸巨头中,杨森最善于建设……在诸巨头中头脑极新,不甚殖产,是其长处。其短处在一意孤行,做事未免操切,而当其从事其理想中之建设时,并不顾人民之担负能力如何……刘湘为人沉着有远识,不殖产,无内宠,在军人中实为难能……然彼个人对于现代政治似尚未得真切之认识……”
胡先骕本是书斋中人,抗战中出任江西的国立中正大学校长,和当局因校址、保护示威学生等问题有过一些颇不愉快的交道,后被蒋介石解职,按说这时他更应该如自己诗中所说,“春暮山花到处开,松间负手独徘徊”了。可是,随着国共两党的彻底摊牌,民生的进一步凋敝,他还是破门而出了,其主张仍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选择,侈想走第三条道路,积极与北京大学知名教授组织独立时论社,撰写了《对政务院之期望》、《今日自由爱国分子之责任》、《与翁院长一封公开信》、《论“两分军事、三分政治、五分经济”之戡乱政策》等政论文章。
这些文章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他在后来的科学院学部委员评选中落选。当然可能还有一些余波,显示得也许并不分明,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当事者的后半生。
区别与自由主义者的胡先骕
1949年后,胡先骕的处境,从他亲手创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被接收,为此成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整理委员会中竟无其一席之地即可见出。这本来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信号,但究竟是书生,除了批评李森科曾掀起轩然大波外,胡先骕还有以下一些比较“出格”的事:
因管理庚子赔款而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在1949年后的语境中被视为美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的工具和走狗,遭到彻底否定。1950年,胡先骕撰《庚子赔款与中国科学人才之兴起》一文,因文章多次涉及中基会对近代中国科学的贡献,作者和编者都被认为有崇美思想,发表此文的《北京史话》刊物被勒令停刊。
有人指责胡与蒋介石仍然没有划清界限,不愿骂一声“蒋匪”。思想改造运动过后,胡在私下里说:“我不能骂蒋介石,骂了蒋介石,就等于变节”,这些话被人反映到领导那里,记录在胡先骕的人生档案中〔1〕。
1951年12月,在许多知识分子开口“学习”闭口“改造”的环境中,“胡先骕提出学习是突击性的,大家不赞同,又渠不肯做笔记,讲自大学以来已无此习惯,抗拒抽查笔记,谓其记性甚好,可知其确存在若干包袱”。〔2〕
……
李森科事件中,内有众口铄金的紧张气氛,外临“老大哥”苏联抗议等强大政治压力,胡先骕对特地前来劝说他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副院长竺可桢表示,可以写学习心得的文章,但拒绝检讨〔3〕。本来和蒋介石父子闹过不快,骂一声“蒋匪”是很容易的,可是他却说骂了“就等于变节”;反美的大气候下,他却为美国人当初退回的庚子赔款评功摆好……斯言斯行,当然可以说是书呆子气十足,不过,这样的书呆子气十足的动作,却常常发生在文化保守主义者身上(陈寅恪的事例更是众所周知),窃以为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同样为书生,为我们所熟知的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往往是另外的抉择。许纪霖分析过金岳霖这一个案,说1949年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心悦诚服地接受马列主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49年以前一直担心中国被瓜分。正是这样的‘瓜分情结’,使得他在解放后认为共产党解决了国家的独立,所以国家有自由了,个人自由受点损失也就认了”〔4〕。
在一个与自己经验完全陌生的时代里,面对新的主流话语和价值符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或自觉或自愿或自觉而不自愿地改造自己。这里“自觉”、“自愿”、“自觉而不自愿”云云当然都是有区别的,自觉属于理性,而自愿属于意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意志上也许是不自愿的,但是在理性层面又往往是自觉的,他们觉得自己配不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应该脱胎换骨。与此相比较,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却常常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领地,就像当年要为传统文化声嘶却气弱地吁救一样。这是为什么?
不能不注意到,在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儒家理想人格的榜样所起的作用。什么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内涵和外延也许都是模糊的,但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而言,又分明有这样一种东西,它就活生生地存在于先贤的只言片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对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先贤的片言只语就仿佛是一种神示的力量,始终能让他们从艰难竭蹶中倔强地昂起头来。有时候他们可能显得太不通权变,甚至是颟顸,但他们在传统文化浸润之下,其耻感往往是最深的。
胡先骕在中正大学校长的任上,曾对学生发表演讲,宣称:“我国民族不可磨灭之精神,足以使吾国文化几废几兴,终不失坠者,仍为昔圣昔贤道德学说之精粹也。”这样的话和陈寅恪所论几乎如出一辙。今人闻之难免有一些迂腐的气息,其对世风的影响也可能微乎其微,但毫无疑问,胡先骕们即使是在立身行事的小节上,也是躬行不逾的。以骂“蒋匪”一事来说,谁都可以张口即来,骂与不骂,其中的利害得失也不言而喻,可是自己明明接受过别人的委任,现在骂人为匪,则何以自处?
胡先骕“文革”伊始即受到了冲击,据其女儿回忆:“从1966年8月到1968年这二十三个月中,我家大约被抄了六七次之多,绝大部分的生活用品,大量的书籍、文物字画、文稿、信件和首饰等物均被抄走,连过冬的大衣也未留下一件……每次抄家都在对我父母进行人身侮辱……每天逼他写检讨、思想汇报,还要到植物所接受批斗。”
1968年7月15日,即胡先骕去世前一天,单位来人通知,命他第二天暂时离家,到单位集中接受批斗。当晚,由夫人准备了一小碗蛋炒饭,吃过之后,他独自去睡觉,一只脚还没有放到床上,就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被确诊为心肌梗塞。
上世纪四十年代,胡先骕有一首题为《被酒偶书》的七律,尾联云:“奇怀一掷归平淡,不著袈裟我亦僧。”
盛年中的胡先骕是否早已预见到了自己身后的寂寞?“但问佳不佳,不问新不新”;“我国民族不可磨灭之精神,足以使吾国文化几废几兴,终不失坠者,仍为昔圣昔贤道德学说之精粹也”。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所说好像总是离现实太远,言不及义且缓不济急,在求新求异的时代大潮中,被湮没几乎是一定的。不过,我相信,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沧桑世变,总还是有人会想起他们那微弱的声音,哪怕姑妄听之也好。
注释:
〔1〕胡宗刚:《不该遗忘的胡先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2〕《竺可桢日记》第三册,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
〔3〕薛攀皋:《双百方针拯救了植物学家胡先骕》,刊《炎黄春秋》2000年第8期。
〔4〕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