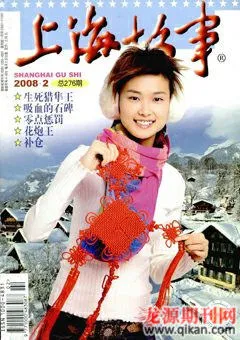伢儿的嘴,伢儿的面
2008-12-29王应良
上海故事 2008年2期
爸爸的祸,这次可就闯大了,他把垸下的二伯,按在水田的田埂上,狠狠地打了一顿。全垸的二十多户人家,见我们家人就像见到仇人一样。
在我们大别山区,不比北方,很少有千儿百户的大集镇,都是一些不足几十户的小村小寨,散居在大山的褶皱里,一个垸一个姓,打断骨头连着筋,都是共一个祖宗、不出五服的兄弟。我家却是一个另类,因为爸爸是上门女婿,奶奶常劝他说:“抬头的当家媳妇,低头的上门女婿。”可爸爸就是不信这个邪,所以邻里关系弄得很僵。
今年春上,国家搞土地二轮延包,垸里的田地,因婚丧嫁娶的原因,需要重新调整。爸爸在垸里的调整会上,据理力争,终于将一块方方正正、水源方便的大田,从二伯家争了过来。
第二天清早,爸爸就将这块大田翻了过来,还撒下了一担尿素,灌上一田肥水,才心满意足地牵牛回家。准备到了下午,全家齐上阵,将早稻秧插下去,等到了夏天,就是一季好收成。
回到家里,奶奶已经将丰盛的饭菜端上了桌,爸爸还高兴地喝了两盅。吃罢早饭,爸爸有点不放心地出门了,他来到大田边一看,大吃一惊,大田里的一田肥水放得滴水不剩,全部都流到下面二伯家的田里。爸爸断定,这是二伯心里有气,故意使的坏。他怒气冲冲地准备回垸找二伯评理,正在这时候,二伯背着一个板锄,慢悠悠地从对面田埂上走过来。生性莽撞的父亲一看见,火冒三丈,上前三言二语不合,就把二伯按在田埂上,狠狠地擂了一顿。垸里的人听到打斗声,都赶了过去,他们与其说是劝架,不如说是给二伯帮忙,如果不是我和姐姐操着两根扁担,像两只小狼羔一样冲过去,爸爸的亏可就吃大了。
第二天,我和姐姐要上学,妈妈一大早就跑到菜园里掐菜,准备炒一点新鲜的青菜,让我们带到学校中午吃。可等她来到菜园一看,满园的菜苔、菠菜拔得一根也不剩,妈气得眼泪都下来了,她想,这一定是二伯家里的人报复我家。一气之下,妈妈回到家里,拿出一块砧板,放上一把稻草,抄起一把菜刀,坐在我家门前,看着二伯家的大门,一边剁,一边祖宗八代地破口大骂。这在大别山里,是最恶毒的骂人方式,直骂得二伯家的人大气也不敢喘,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如果不是奶奶把她吼进去,论妈妈的脾气,她可以不歇气地骂上一整天。
傍晚,我和姐姐放学回家,听见爸爸还躺在床上,痛得直哼哼,看见桌子上只有几碗难以下咽的腌菜,心里就恨得痒痒地。我和姐姐咬咬牙,暗暗地相互瞧了一眼,就心有灵犀一点通,决定今晚瞒着大人采取报复行动。
夜里,待家里人全部睡熟了,我和姐姐悄悄地爬了起来,轻轻地打开后门,拿起早就备好的毛竹条,乘着月色来到了田畈。我们找到了二伯家的油菜田,就下到田里,挥起手中的竹条,往那刚开满黄色花蕊的油菜花,狠命地抽,一边抽,还一边说:“叫你拔我家的菜!”这一夜,我和姐姐满怀着仇恨,手臂都抽肿了,还不知道痛。直到鸡啼五更的时候,我们把二伯家一块二亩多的油菜,全部抽得七零八落,倒在地上,才回到家里。
当我和姐姐正准备悄悄进屋时,没想到被早起的奶奶逮了一个正着,她见我们俩全身露水、满身花黄的样子,就一下子明白了。我们还高兴地向她表功,没想到,奶奶一听,就气得脸色苍白、浑身打颤,她抄起一根烧火棍,就把我和姐姐按在地上,劈头盖脸地一气猛打,一边打,还一边咬牙切齿地骂:“你这两个混账东西!在我们山里,伢儿不记大人仇,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仇一代接一代地结下去啊!”奶奶打断了一根烧火棍,还不饶过我们,就押着我和姐姐来到二伯家里,当面向二伯家赔礼道歉,并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把平时出嫁在外的姑姑们孝敬她的几百元钱,全部拿了出来,赔给了二伯家。
回到家里,奶奶告诫我和姐姐,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她还要求我们从此后,见到垸里的任何人,不管他与我家的关系怎样,该叫爷的叫爷、该叫伯的叫伯。如果她发现我们没有叫,她见一回,就打我们一回。在奶奶的高压下,我和姐姐尽管心里不愿意,只好照办。刚开始,垸里的人不理不睬,既而就用鼻子哼哼,再后来,就满脸笑容地答应。说来也怪,我们这一叫,垸里的人对我和姐姐态度就好多了,垸里的孩子也和我们一起结伴上学了,我和姐姐从他们家门口经过时,碰到有好吃的,他们也会分给我们一份。
尽管这样,但垸里的人对爸爸和妈妈,还是横挑眼睛、竖挑眉。特别是到了夏天的晚上,垸里的人都把凉床搬到一起,在一块儿有说有笑地乘凉,就把我们一家孤零零地抛在垸头。我和姐姐看了,心里痒痒地,想过去玩,又不敢。爸爸和妈妈见了心里就有气,他们俩在一起就嘀咕起来,在我们垸里,家家都是白墙黑瓦的土坯房,还没有一家建楼房,他们决定在垸里抢先建第一座楼房,从气势上压压他们,气也要气死他们。
爸爸和妈妈说干就干,从夏天开始,他们俩就像蚂蚁搬骨头一样,从山上把砌屋脚的石头抬了下来,又把从外面买回的砖瓦、水泥一担担地挑了回来。幸亏爸爸学过几天的泥瓦匠,接着,他们一个当师傅,一个打下手,开始一砖一瓦地砌房。一个夏天下来,房子一寸寸地往上长,他们俩也一天天地消瘦下来。到了秋天,一座三连的楼房就显形了,到了该砌预制板、上梁盖瓦的时候。
按照大别山里的乡风,不管谁家盖房,到了上梁盖瓦这一天,全垸的青壮劳力,不要人请,都应该主动来帮忙,这是祖宗留下的规矩,哪怕有杀父之仇,也应该要来,不来,那还叫什么乡风?那还叫什么乡里乡亲!这一天,我们全家人早早地就作好了准备,奶奶不仅从山外买回了三大坛好酒,还请人专门杀了一头猪。可是,我们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一个人来。
奶奶见了,只好叹气。生性倔犟的妈妈一看,气就上来了,她就不信没人帮忙,就建不起一座房。可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几百斤重的预制板,她和爸爸刚抬上去两块,妈妈的双腿就累得打抖,不听使唤。在抬第三块上楼时,妈妈的脚一滑,这块预制板就滚了下来,如果不是爸爸机灵,闪得快,他的双腿就会残的,尽管这样,他的脚还是砸得鲜血淋漓。妈妈见此情景,委屈得坐在家门前,号啕大哭起来。
就在这时,首先是垸里的二伯从家里伸出脑袋来看了看,一会儿,他就背着一根抬杠走了过来,紧接着垸里的其他青壮劳力和一些婶婶们一个接一个不请自来。在二伯的指挥下,他们抬预制板的抬板子,帮忙做饭的开始做饭,倒剩下我的爸爸和妈妈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俗话说,人多好办事,一天下来,我的爸爸和妈妈忙了几个月的房子,一天就上了梁,盖了瓦,大功告成了。
这一天,最高兴的是奶奶,她迈着一双小脚,屋里屋外地忙个不停,太阳刚一落山,她就叫爸爸在家门口的空场上架起了几个一百瓦的电灯,从垸里借来的六个大方桌,一字儿摆开。刚一收工,奶奶就将山里人招待贵客用的粗瓷大碗,装上满满的鱼肉,一碗碗地端上了桌。妈妈抱着酒坛,跟在爸爸的身后,将垸里男人们的碗满上,爸爸双手擎起一碗酒,看着乡亲们,声音就哽咽起来,他说:“乡亲们,兄弟我是个粗人,不会说话,过去有什么对不住大家的,请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说完,就将一碗酒一口喝下。
听了我爸爸的话,垸里的人都没有做声。这时,二伯端起一碗酒,站了起来,他看着我爸爸说:“今天是你家大喜的日子,有些话本不应该说,既然兄弟说了,我就敞开了说吧。不是我说你,你的性子也太强了,我们大家本没有把你当外人,是你们自己把自己当外人。就拿春上那事儿来说吧,你家田里的水,我的确没有放,是因为那田埂上有老鼠、鳝鱼打的洞,我本想告诉你,可一看你得理不让人的样子,就忍住了。可你倒好,不问青红皂白,就动手打人。唉!我们这些做大人的,有时还比不上伢儿们。就说今天这事儿吧,我们本硬着心肠,宁可败了乡风也不来,可一想起你家的伢儿,平时,一见面,就伯呀婶的喊,那热乎劲,把人的心都喊化了!”
奶奶听了,把我和姐姐推了一下,我们赶紧上前,脆生生地喊了一句:“二伯,喝酒吧!”二伯一听,就举起手中的一碗酒,对着大伙儿说:“乡亲们,看在伢儿的嘴,伢儿的面上,没有过不去的山,没有忘不了的仇,兄弟敬的这碗酒,我们就干了吧!”听了二伯的话,看着垸里的乡亲们大碗喝酒,奶奶高兴得在边上悄悄地抹眼泪。
这一夜,我们家的三大坛酒喝了个底朝天,这还不算,二伯和乡亲们都跑回家里,将家里的酒也抱了出来。这一夜,我们垸里弥漫着浓浓的酒香,整个垸都醉了,乡风也醉了。
(责编/方红艳插图/桑麟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