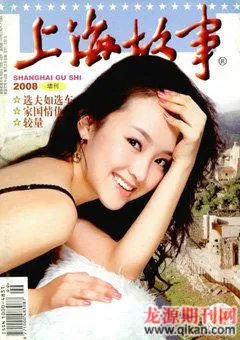谁是美食家
2008-12-29王应良
上海故事 2008年13期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有位鼎鼎大名的餐饮大享,叫管三和。这一年,他的儿子管新华,在英国留学四年,取得了酒店管理博士学位,学成归来。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的管三和,就将地处上海霞飞路繁华地段的“上林宛”,放心地交给儿子打理,自己则带着几房太太回青浦老家朱家角颐养天年。
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的管新华,一上任,就对“上林宛”的陈规陋习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认为父亲的那一套经营之道,在如今的上海滩十里洋场早就过时了。他不仅斥重资,将“上林宛”改建成中西合璧的风格,将餐厅里过去那些穿着长袍马褂、跑堂打杂的店小二全部辞退,换上一批穿洋裙、花枝招展的女招待,就连门口的接引,也换成了红头阿三。而且,他还不惜重金,将上海驰名海外的锦江饭店的淮扬菜名厨、红磨坊的西洋糕点名师挖了过来。一心想把“上林宛”做成上海滩餐饮业的头块招牌。
这还不要紧,管新华还在“上林宛”装修竣工前夕,召集上海各大报刊记者,别出心裁地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上林宛”将于即将来临的八月十五、蟹黄豚肥的中秋佳节,重新开业迎宾。届时,他将广发请柬,邀请上海社会贤达、洋人使节,推出一系列拿手招牌菜,举行评餐品菜美食大会,不管是谁,不论贵贱,只要对“上林宛”的美食评点到位,指出瑕疵,他将评出上海滩美食家中的“状元、榜眼、探花郎”,并给予三千、二千、一千大洋的花红。
上海滩本是一个无风三尺浪的热闹地儿,这一下,可谓丢下了一记重磅炸弹,当天,各大报纸纷纷以套红的字号,头条发布这条新闻,一时间,“上林宛”和管家大少爷成了上海大街小巷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一些社会贤人、饕餮之徒都翘首以盼,等着八月十五这一天,到“上林宛”大快朵颐,看看是谁能够夺得上海美食界的“三鼎甲”!
这一天,管新华忙着给一些上海的社会贤达,亲自登门送请柬。当他开着车,回到装饰一新的“上林宛”时,禁不住皱起了眉头,只见三三两两老弱病残的乞丐,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地聚在“上林宛”前的屋檐下,或坐或立,有的拄着一根打狗棒,伸着一只脏兮兮的粗碗大碗,向过往的行人乞讨,有的干脆半躺着,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翻弄着破袄子,找虱子,丢到嘴里津津有味地咬得“嘣嘣”直响。
管新华一见,心里就恶心起来,他想,这怎么行!客人来了一看,还没进“上林宛”就倒了胃口,还有什么心情享受山珍海味。他当即就将店里的大堂经理吼了出来,把他臭骂一顿,喝令他马上将这些有碍观瞻的乞丐全部赶走。大堂经理听了,面露难色地说,少爷,这都是老掌柜同意的,这么多年他们就在这儿……
管新华一听,禁不住心头火起,他早就听别人说过,父亲喜欢和这些乞丐盲流交朋友,他不仅每年的二月初二龙抬头这一天,关门歇业一天,将借住在城隍庙里,以虞元礼为首的一大帮叫化子请到店里来,大鱼大肉地款待一餐,而且还吩咐店里,每天将客人吃剩下的残羹剩饭分给门前屋后的游丐,让他们在这里栖风避雨,饱食一顿。
管新华听了大堂经理的话,脸就沉了下来,他冷冷地说:“现在是老掌柜当家,还是我当家?既然是我当家,这规矩就得改!”大堂经理听了,连忙一边点头哈腰,一边大声地指挥店里的侍应生和门口的红头阿三,赶紧将这些乞丐轰走。
没想到,这些乞丐滑得很,赶走了张三,来了李四,拉起了这个,那一个又躺了下去,惹得那一位人高马大、浑身长毛的红头阿三一时怒起,举起腰中挂着的狼牙大棒,一阵猛打,打得乞丐们东躲西藏,一个年老的瘸足乞丐,因腿脚不利索,被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面。这一下,可就捅了马蜂窝,只见一位年少的乞丐沿着霞飞路一溜儿狂奔,一边跑一边喊:“快来呀!上林宛的少东家为富不仁,店大欺人!”转瞬间,一条街的乞丐一听到喊声,都涌了过来,将“上林宛”门口的道路围得水泄不通。
管新华一见,这帮乞丐太无法无天了,禁不住勃然大怒,当即就给英租界的巡捕房打了一个报警电话,没过一会儿,一队全副武装的洋巡捕杀气腾腾地赶过来,他们又是鸣枪,又是催泪瓦斯的,乞丐们见了,一个个溜之大吉,跑得比兔子还快。管新华见了,心里就好笑,父亲当年太心慈手软了,这帮狗东西欺软怕硬,不给点颜色给他们,就不知马王爷几只眼!果然,从这一天起,乞丐们知道“上林宛”的少东家有洋人撑腰,再也不敢来胡闹了。
转眼八月十五就来了,这一天,“上林宛”里张灯结彩,鼓乐喧天,好不热闹!一大早,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一副洋泾浜打扮的管新华,和专门请来当司仪的上海当红交际花一道,站在门首的红地毯上,笑态可掬地喜迎宾客。也算他真有面子,不仅上海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等豪富公子来了,就连跺一脚上海就地动山摇的黄金荣、杜月笙也过来捧场。
正当管新华陪着尊贵的客人们,在贵宾室里谈笑风生,畅谈他在海外求学的见闻,以及他发展“上林宛”的宏伟蓝图时,酒店的大堂经理脸色苍白地走了进来,把他拉到一边附耳说了一通。管新华一听脸色就变了,他向客人说了一声:“抱歉!去去就来!”就连忙跟着大堂经理一起赶到前面的餐厅。只见一百多位老老少少的乞丐,散坐在餐厅的楼上楼下,一人独霸一桌,一人面前一盘茴香豆,提着一葫芦自带的水酒,在那里自得其乐、慢慢悠悠地吃喝着,瞧他们的架势,没有大半天还散不了席。在餐厅里的一大帮小姐、太太们,一个个皱着眉头,掩着鼻子,作势要走。大堂经理在边上哭丧着脸说,他看今天是开业大喜,来的都是客,这些乞丐来了,既没有动粗,而且还出钱点菜,就给他们上了,谁知道他们这样!
管新华一见,心里就明白了,怪不得这几天他们没来,原来是准备今天来拆台闹事的。于是,他不动声色地又给英租界的巡捕房打了一个电话,没过一会儿,一大队荷枪实弹的巡捕们又赶了过来。可这一次,巡捕们上前与乞丐们一交涉,都退了出去。巡捕房的洋探长,拿着一张报纸走到管新华面前,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对他说:“对不起,管先生!你不是在报纸上说,开业这一天,不管是谁,不论贵贱,都可以来品尝?况且,他们出钱点菜,合法买卖,没有违法,我们不能抓他!”说完,就无可奈何地朝他耸了耸肩,摊了摊手,带着巡捕们走了。
这一下,管新华傻眼了,如果乞丐们就这样耗下去,今天的评餐品菜美食大会就要被他们搅黄了。正当他急得六神无主时,他的父亲管三和,急急忙忙地从乡下坐车赶了过来,他一进门,就笑容满面地朝着乞丐们拱着手,大声地说:“各位老朋友!今天是我家开业的大喜日子,各位能来捧个人场,我管三和感激不尽,各位慢用!”说着,他朝着大堂经理一挥手说:“给老朋友们上菜!”说完,他又回过头,看着儿子管新华,虎着脸说:“你今天都请了哪些人?请没请我的老朋友、大叫化子虞元礼?”
管新华摇了摇头说:“没有。”管三和一听,大吼一声:“胡闹!”说完,就大踏步地走出门外,吩咐司机赶快送他到城隍庙,他要去接一位尊贵的客人。没过多久,车子就开回来了,只见管三和先下车,毕恭毕敬地打开后座车门,将一位瘸了一条腿、瞎了一只眼、秃成一个瓢、背着九只口袋的老乞丐搀扶下来。
管新华一见,心里就不以为然,原来虞元礼就是这么一个糟老头!可他没想到,虞元礼一进门,一句话还没说,餐厅里的那些大小乞丐,一个个赶紧起身离席,向他唱了一个诺,就不声不响地走得一个也不剩。管三和将虞元礼请到楼上最高档的雅座,与一帮最尊贵的客人坐在一起,更让管新华惊讶的是,就连黄金荣、杜月笙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见他进来,也客气地将他推到首座,他居然也不推辞,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到这时,管三和才对着儿子说:“现在可以开席了,请客人们评餐品菜!”
管新华连忙从雅座里走了出去,大喊一声:“吉时已到,上菜!”他的话音一落,一大队女招待们就托着名厨们精心炮制的美味佳肴走了出来,不一会儿,一桌桌山珍海味就摆上了。管新华端着一杯酒,如同蝴蝶乱入花丛,在楼上楼下、雅座单间里穿梭。只见客人们一个个觥筹交错,狼吞虎咽,大声叫好,更有一些酸腐文人,为了得到美食家的头衔和数千块大洋的花红,极尽谄媚,把所有能用的溢美之词全都用了上来。管新华听了,禁不住心花怒放。
当他回到雅座,只见父亲也端起酒杯,走到虞元礼的身边,小心翼翼地说:“虞老先生,请你也开开金口,评一评这些菜怎么样?”虞元礼一听,翻着白眼说:“老管!你是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
管三和赶紧正色地说:“当然是真话,你老就看在我和你多年的交情上,如实评点吧!”虞元礼就拿起筷子,把面前的菜肴每样尝了一口,皱起眉头说:“老管啦!尽管你儿子把店面装成了一个金銮殿,可这菜做得大不如从前!”说着,他用筷子指着面前的一道红烧鲥鱼说:“俗话说得好,年有四季,菜有四时,萝卜过时则空心,山笋过时则味苦,这鲥鱼过时了,则骨硬味酸,应在四月吃它才对,况且这红烧鲥鱼单取鱼肚,而不知鲥鱼鲜在鱼背,这样做菜,真是暴殄天珍!”
虞元礼又指着满桌的菜肴,大言不惭地说:“别看这满桌的山珍海味,别看它价值千金,只不过一桌耳餐而已!”管三和一听,赶紧问道:“何为耳餐?原闻其详!”虞元礼接着说:“所谓耳餐,就是只追求菜的名声,而不注重味道和实惠,就拿这盅燕窝来说,缸臼大的碗,足足有四两,客人是来吃燕窝的,不是来贩卖燕窝的,如果虚求价格和体面,不如在碗中放入百颗明珠,那就价值万金了,管它吃得吃不得!”
管新华在一旁见他说三道四的,心里腾地一下火就上来了,他想,你一个老乞丐,成天饱一餐饿一顿的,你知道什么叫美食?乱说个啥?禁不住鼻子里“哼”了一下。管三和听见了,大吼一声:“放肆!你别以为你喝了几年的洋墨水,就看不起人!要知道贩夫走卒、乞丐行中藏龙卧虎。你看你虞大爷,是乞丐行中九袋长老,他这一生走过了九省八十一府,沿街乞讨,尝尽了万家饭菜,可谓尝尽了天下百味,什么样的奇珍异味他没吃过,别看我们这些人整天的锦衣玉食,谁能与他比,他才是真正的美食家!”
说着,管三和又看着儿子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年要将他们请来款待一次?我是请他们来对我家经营的菜肴提提意见,以便改进,这就是我们上林宛的菜时尝时鲜的秘诀!”
管新华听了父亲的话,一张脸血泼一样,连忙叫人将三千大洋的花红捧了上来,要当场送给虞元礼,没想到,他一摆手就推辞了,他起身站了起来,对着管新华和在座的客人们拱了拱手说:“这花红,我老乞丐就不要了,在座的各位,都是上海滩有头面的人,我只希望各位日后碰见了我的徒子徒孙们,能够赏他一碗残羹冷炙,容他一块屋檐,让他们能够栖风避雨足矣!”说完,就一瘸一拐地走了。
(责编/方红艳插图/杨宏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