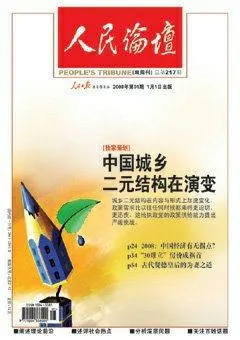中国国情的五个新特征等
2008-12-29
人民论坛 2008年1期
中国国情的五个新特征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国情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特殊国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第一,经济总量不小,但经济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第二,“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依然很严重。第三,我国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比较严重的国家,经过29年的转轨以来,现在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性的、机制性的障碍,还严重地存在着。在深层次上要“攻坚”要“破难”,这个任务还相当之严峻。第四,我国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观念还比较淡薄。第五,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我国的前途命运和世界的前途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如何提高中国与世界的亲和力和亲和度的问题,非常迫切。(常修泽/文,据12月25日《北京日报》)
■改革双重身份:乡镇政府改革的重点
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中,政府不仅仅是政治实体,要履行基本的政治性公共服务职能,而且还因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要履行经济实体的职能。乡镇政府一身兼具“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的双重身份,使乡镇政府既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共服务者,也不能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推动者。因此,改革乡镇政府的双重身份,无疑是乡镇政府改革的重点。(陈 朋/文,据《中国发展观察》)
■产权拍卖阻碍了国企产权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股权的改革,不论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引进战略投资者,还是国企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及对经营班子的期权激励等等,都牵涉到股权转让。企业的兼并重组是企业的最高机密,产权的转让绝对不能走公开拍卖的形式。如果要靠市场拍卖决定,则很难引进战略合作者,国企改革也很难深入,最后也只能是内部人控制一买了之。在国际上,这种兼并重组未完成之前,是绝对保密的。兼并重组这种企业的核心机密在中国则变成物品拍卖这样的市场行为,也是咄咄怪事。(何一平/文,据12月13日《光明日报》)
■转变发展方式重在政府改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实质是改革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方式亦即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改革尚未成功,且受到一些部门、地方、行业垄断的特殊利益和在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问题上不时泛起的旧意识形态观念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阻碍和干扰,这又对中国发展在其新阶段上凸显出来的诸多问题和矛盾提供了基本的解释。现在要更加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在政府改革。说它是根本也好,核心也好,关键也好,无论用哪个词都一样,都是为了说明政府改革对转变发展方式的决定意义。(吉 力/文,据12月11日《学习时报》)
■物业税可能会推高房价
物业税是房地产市场的内在稳定器,从长期来讲征收物业税会降低房价。但是,这样一个房地产调控目标,最后也有可能推高房价。运用税收来调整房地产,已经实施的在交易环节的交易税,本来目的是打击炒房,最后是由买家来埋单,实际上提高了房价。对于高房价来说,地方政府实际上一次性就把土地价格推高、多少税都可以包含在内的收益,如果再来征收人头税一样的整体房屋物业税,是与国家“提高人民财产性收益”相违背的,有重复收税的嫌疑。(许青安/文,据12月18日《证券时报》)
■中国股市正确的参照物不是美国股市
用美国标准判断中国股市市盈率,是个愚蠢而低级的错误。中国的经济增速为11.6%,而美国的经济增速还不到3%,凭什么用美国标准判断中国股市市盈率高低?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处在完全不同的阶段,翻翻近十年的历史,美国的经济增速始终在1%-3%之间起起落落,最好的年份也从未达到过5%,而中国经济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10%以上。美国股市已有百年历史了,而中国股市今年才17岁,还在青春期,中国股市个子当然比美国股市长得快。中国股市要像美国股市那样长,那叫侏儒病、矮小症。(魏雅华/文,据12月19日《上海证券报》)
■就业决策的几个误区
从观念和意识上来讲,决策者往往存在着以下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解决就业。中国目前实际上重视特大和大型企业的发展,忽视并歧视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第二个误区是政府自己解决就业。这种思路力图用政府本身和政府所办的事业解决就业,如增加和扩大党政机关单位,并且发展教育、卫生等行政性事业。第三个误区是农村和基层能大量增加就业。我们的一些领导,甚至一部分学者也认为,基层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是就业容量最大的地方。第四个误区是经济不发达和边远地区可以增加就业。(周天勇/文,据12月17日《北京日报》)
■政府应消解中产者对未来的恐惧
一个社会里中产者的增加,不仅体现在其工资收入以及其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在缩小贫富差距上下工夫——让更多的人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并买得起房。然而,当下中产者难成大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人们对未来心存恐惧。比如,近期水电气热、食品、教育、医疗、住房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在急剧上涨,引起老百姓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人们害怕手中的一点点积蓄贬值成一堆废纸。而转型期社会所造成的高度不确定性——比如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职业前景的变化莫测,都可以形成人们对未来的忧虑。笔者认为,政府有义务采取措施化解人们对不确定未来的恐惧。(丛 未/文,据12月16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