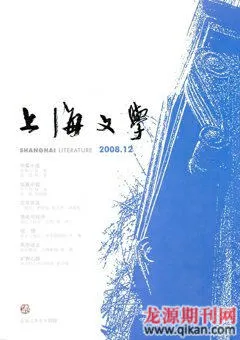昆明印迹
2008-12-29张昆华
上海文学 2008年12期
交三桥
地名是一个自然与人文的符号;是一段生活与历史的碑铭;是一座蕴藏过去时光和积淀未来风尘,既能任你朝夕亲吻但又使你不能伸手抚摸的精神塑像。
这就是交三桥,湮没在千千万万地名中的曾经有人在这里流血、牺牲、哀伤,令人无法忘却、永存记忆的昆明的交三桥。
在一个冬末春首、季节悄然变幻的薄雾淡泊的早晨,我们从城南的滇池之滨驱车前往城北的闹市中心,陪同从丹麦来的梅和她的丈夫去用美元兑换人民币以作云南之旅费用。不知从何时起出现这个颠倒的金融行情——过去只要你有响当当的美元,何愁无处用场。可是如今美元储备过多,转而促使人民币升值吃香了。连梅和她丈夫旅居的四星级酒店也不直接收取美元,使手持美元的外宾很不方便。幸亏有酒店经理的热情指点,我们才能拨开一阵阵乍暖还寒的滇池清风,绕过缠缠绵绵的一条条车流,等候严肃的一盏盏红灯闭上眼睛或是依靠含情的一盏盏绿灯挥手指引,终于来到了全城唯一可以用美元兑换人民币的中国银行。梅和她的丈夫去大厅里接待外国客户的专柜办理相关手续时,我便抽空到大楼外观赏繁华的街道风景。
此前除了偶尔乘车快速通过这片闹市区,不曾有过在这儿漫步或停留的机会,使本应熟悉的一切反而显得陌生。这是两条大路交叉衔接的交通枢纽,从东到西是人民路,从南到北是北京路。昆明人虽然妇幼皆知人民路与北京路这两条车水马龙的交通要道,但却未必了解这两条犹如粗壮臂膀所紧紧拥抱着的一个小而又小、老而又老的地名:交三桥!
呵,交三桥!要不是站在你的地名牌前,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你就是我久别未见又十分思念的交三桥。你有没有搞错?我大声地问着交三桥,也小声地问着自己。是谁?从何时起又把你这古旧而不腐朽的地名寻呼出来,归还给这片新生的土地呢?农家草帽一样普通平凡的历经了多少雷雨袭击太阳、几度阴晴圆缺月亮的地名,在“文革扫四旧”之后又重新戴在了你的头上,再一次显示了老地名作为符号、碑铭或精神塑像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力量。地名的生命在于它所植根的这片土地是否还有生命。
可是,交三桥依然还是从前那个交三桥吗?
椐我所知,这地名的缘起并不是说这里有三座桥相交,是因为这里南有太和街,北有环城路,东有小猪场路,这三条城外的街道交汇于大东门前盘龙江上的溥泽桥而得名。溥泽桥是盘龙江上的第一座桥,始建于元代至正年间,所以早年又称“至正桥”。明朝取代元朝后改土城墙为砖城墙,大东门更加威严雄壮,那座盘龙江上的桥便被称为“大东门桥”。直到清朝灭亡明朝,在康熙年间重修此桥之后仍沿用此桥名。由此可知是先有此桥才有交三桥的地名。这样说来,交三桥这地名大约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名龄了吧。那么交三桥必然会有不断交替的春夏秋冬、花开花谢、雨飘雨歇、果熟果落、风寒风暖的岁月让历朝历代的人们去传说,那么我对交三桥又可以说点什么呢?
我之所以知道交三桥,难忘交三桥,则是由于六十多年前我的童年时代,侵华日军的飞机空袭昆明的猛烈轰炸中铭刻下的惨痛记忆。那是乌云低沉的冬天里的一个早晨,刚刚听见五华山上拉响的“呜呜”警报声,日机已经飞临城市上空。祖父用颤抖的双手把我拉到背上背起,从盘龙江西岸的一间小屋里跑出,要去城外躲避轰炸。不幸的是大东门的城门甬道被一辆抛锚的卡车堵塞着,蜂拥的人群推搡着、拥挤着、踩踏着,好不容易才逃到城外郊野。残暴的日机对着手无寸铁、只知逃难的密密麻麻的人群进行低飞投弹、贴近扫射,顿时哭声四起,血肉横飞……祖父随即卧倒在田埂一侧,把我搂在胸怀,用他的脊梁骨护卫着我,爷孙俩才幸免于难。后来听说,那次在交三桥被炸死的市民多达五百余人。我至今仍记得那时的交三桥,田地里的油菜花蚕豆花上溅满了殷红的鲜血,道路边的老朴树枝干上挂着同胞们被炸断了的肠子和炸碎了的衣衫……
而此时眼前的交三桥,早已是改天换地了。下面人流如织、车流似潮;上面是高楼入云、大厦蔽空。不是因为保留着从前的地名,哪里还能联想到当年日机轰炸的灾难痕迹呢?在人民路东段西段和北京路南段北段纵横结构的十字形地盘上,完全成为银行扎堆、金钱出入、富甲四方的风水宝地。且看东北角上是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东南角上是中国建设银行;西南角上是中国农业银行;西北角上是广东发展银行,真是所有重要的银行都跑到交三桥列队集合了。而与银行为友邻的是新华图书城、星宫大酒店、昆船大厦等宏伟博大的建筑物,只有那萎缩了波浪的盘龙江在东岸和西岸的挤压下默默地流淌 着……
不知道是由于岁月远逝也难以洗净过去被侵华日军狂轰滥炸的耻辱与愤恨,还是因为看到今天有那么众多的银行高楼大厦顶天于日机曾经横飞的空中、立地于日机曾经炸烂的地上,为祖国变得日益富强而觉得自豪呢?亦或是两种感情都在翻腾吧,交三桥在我心里、在我眼前轮回着映现出一幅幅或历史或现实的图景,让我时而怀旧,时而喜新。此时,我真想对交三桥说点什么,又很想请交三桥对匆匆来往的人们说点什么……
梅和她的丈夫已经用美元换好人民币走出了银行大楼。我们便一起上车向北郊的风景名胜黑龙潭驶去。因为早先说好要去观赏那里举办的梅花展览。这位以梅为名的梅女士说,从她出生起名后几十年来还从未见过梅花呢。听她这么一说,我们更加兴致勃勃地向梅园奔去。我本想说的当年交三桥被日军轰炸的沉痛往事,话到嘴边便又咽下去了。开车的是位穿便衣的警察女作家,同车的还有我的老伴。路边不时有一蓬蓬血红色的叶子花或一丛丛金黄色的迎春花扑面而来又一闪而去,但是最引人神往的还是路旁一棵棵苍翠如人的老朴树和一片片美丽如画的油菜花蚕豆花。这树这花会让我想起些什么,除我而外,可能谁也不会明白。交三桥高楼林立,不再是广阔的田野了,不再有老朴树和油菜花蚕豆花了,虽然在交三桥之外的其他地方,朴树和油菜花蚕豆花仍在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地生长、繁衍着后代子孙。但树对于树、花对于花不会有记忆的讲述,不会再想起六十多年前那些死难者的血肉和破衣褴衫。只有人能够通过地名寄存着漫长的历史和那些不该忘的故事。即使天地演变得面目全非了,只要当初的地名还在,只要有人一声呼喊,便能从遥远的过去唤醒沉睡的岁月,便能看见中华民族同胞们的鲜血浸润过的土地上依然生长着的朴树、开放着的油菜花蚕豆花……所以,我常听史志工作者说,不要废弃老地名,不要更改旧地名,以便让历史文化得到延长和持续。想着这些,面对原野,我便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祖父当年教我的那首芬兰民歌《在森林和原野》。意想不到梅的丈夫海宁虽然不会说中国话,但却听懂了歌曲旋律,也跟着唱了起来。梅说,这首歌在丹麦和北欧很是流行。真是音乐没有国界,有的是音乐的心声。我老伴和警察女作家当然也会唱。于是我们又从头唱了起来。全车响彻了不同国籍不同语言的合唱:
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的逍遥,
亲爱的少年呀想些什么?
……
栽下一棵开花结果的树呀,
这是多么美丽呀多么美丽呀……
滇王故都的长青树
滇池之滨,当年从石寨山发掘出一枚镌有“滇王之印”的金印,见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汉武常元封二年“赐滇王印,复长其民”的历史确有其事。此后又从天子庙发掘出春秋战国末期的铜鼓、铜鼎等标志王位的青铜器,再一次见证了滇王庄及其子孙先后在那片土地上建立过滇国都城。文物记存着远去的历史。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滇王后代的后代又在滇王故都的遗址上建设昆明新城的时候,我漫步在那些钢筋水泥生长起来的高楼大厦之间,看到了两棵依然茂盛的文物长青树……
在新城建设中文物古迹保护得最好的恐怕就是“冰心默庐”了。这是百年前呈贡斗南村华氏家族在三台山东坡修建的用于守墓和祭祀祖先的青瓦土墙小宅院,正屋为坐西向东两层三间小楼,南北两厢为平房,早时称为“华氏墓庐”。山上还有一座三台寺古庙,因已破落而断了香火。一段倒塌的旧城墙,陪伴着老树荒草昏鸦,也早已废弃无人居住。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4月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转移到昆明。冰心和丈夫吴文藻及其子女也随校到达,后由于日机轰炸昆明,冰心一家于1938年9月由昆明搬到市郊呈贡避难。那时吴文藻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任,组建社会学系并任主任,每周往返于昆明和呈贡。冰心住在华氏墓庐,主要是养儿育女,同时也在呈贡中学和简易师范任教。其间冰心住所便成为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和被称为“三剑客”的罗常培、郑天翔、杨振声等教授和住在呈贡的陈达、戴世光、史国衡、沈如瑜、倪因心、孙福熙、费孝通、沈从文等学者、教授聚会畅谈之处。直到1940年9月,冰心收到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特别致函以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名义邀请到重庆做妇女工作,吴文藻到国防最高委员会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工作,一家人才离开住了两年的呈贡赴重庆。
在呈贡期间,冰心将“墓庐”的“墓”字按谐音改称为“默庐”,并于1940年2月28日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散文《默庐试笔》,赞美呈贡的秀丽风光。文中写道:“回溯生平郊外的住宅,无论是长居短居,恐怕是默庐最惬心意……论山之青翠,湖之涟漪,风物之醇永亲切,没有一处赶得上默庐”。同时冰心还为其义务任教的呈贡中学写了校训“谨信弘毅”,创作了校歌,“西山苍苍滇海长,绿原上面是家乡,师生济济聚一堂,切磋弦诵乐未央,谨信弘毅,校训难忘。来日正多艰,任重道又远,努力奋发自强”。
临别呈贡前夕,冰心为学生李培伦题写条幅,表达了忧国忧民、坚持抗战的情怀:“一发青山愁万种,干戈尚满南东,几时才见九州同?纵然空,世事、世事岂成空。胡马窥江陈组练,有人虎帐从容,王师江镇相逢九原翁,应恨世上少豪雄。”由于吴文藻、冰心夫妇在呈贡默庐进行的教育、文学活动和抗战期间大批文化名人与默庐的缘分,呈贡县报请上级有关部门审批为昆明市文物保护单位,并按修旧如旧的原则维修,更名为“冰心默庐”,在“庐”内长期展出“抗战时期冰心在呈贡”、“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呈贡”、“石碾下的抗战烙印”等图文资料和抗战文物,使冰心默庐成为名副其实的保护良好的文物单位。
张天虚故居位于呈贡龙街中栅子,建于1890年前后,为土木结构四合院布局,被列为呈贡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近已经迁走了原先占用故居的单位,并将进行维修保护。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张天虚,但呈贡人民却为这位革命作家感到自豪和骄傲。1911年12月8日,张天虚在此屋后楼出生,在故乡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十二岁便外出求学,投身革命,直到1941年1月因肺结核病重从抗日前线回家中养病,于8月逝世于老屋,终年还不满三十岁。张天虚被安葬于昆明西山聂耳原墓左侧。郭沫若在为张天虚写的墓志铭中这样说道:“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增辉,滇池不孤。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世壮图。”郭沫若把张天虚四十七万字的长篇小说《铁轮》与聂耳谱写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相提并论,可见《铁轮》的成就很高。张天虚与聂耳是中学同学,成为爱国运动中的好朋友,他俩分别于1930年离滇赴沪从事文艺革命活动,分别于1933年加入共产党,又分别于1935年离上海赴日本。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溺水身亡,是张天虚为其料理后事,并随后将聂耳骨灰送回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天虚到达延安,参加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股长,负责宣传工作。张天虚创作的独幕话剧《王老爷》在延安演出时,受到中央领导高度赞赏,毛泽东还当场送张天虚一支钢笔作为奖励。1938年滇军60军奉命从昆明开赴抗日前线,党中央决定派张天虚等云南人到60军所属、张冲任师长的184师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张天虚负责宣传组织工作。他在台儿庄战役中编印《抗日军人小报》鼓舞士气,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随即又参加武汉保卫战。1939年初,张天虚因病重回呈贡家乡养病,病情稍好,又于次年赴缅甸仰光参加《中国新报》编辑工作,宣传抗日思想。后又因病重返回呈贡故乡,八个月后逝世。张天虚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抗日战士,而且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先锋,其中长篇小说《铁轮》在当时被评论为“人间丑态从头写,曾使文坛老将惊”的恢宏巨著,此外还有《运河的血流》等四十多篇作品问世后受到好评。保护张天虚故居并在故居陈列展出有关史料和文学著作,使更多的群众了解张天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以及抗日战争和文学史上的卓越活动与贡献,对呈贡对昆明的文化建设都必将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
在冰心默庐或张天虚故居漫步,我感觉到文物是历史的长青树,那绿叶不会枯黄,那红花不会凋落,总会给后人讲述着过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