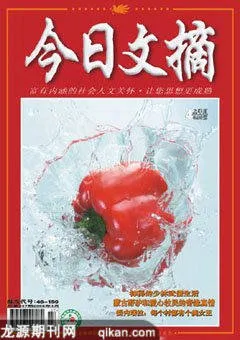第一次卧底
2008-12-29胡玥
今日文摘 2008年7期
背景:缉毒英雄陈新民的卧底经历曾经被改编为热播电视连续剧《行动代号626》。今年50岁的陈新民现任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副局长,已经和毒贩打了25年的交道。他通过卧底与毒贩周旋,参与近百次卧底行动,从未失手过。一名大毒枭在临刑的前一天晚上,提出了死前的最后一个愿望:要见陈新民一次,当面证实一下这位曾经与自己称兄道弟的人真的是一个卧底警察。
虽然身经百战,但陈新民永远忘不了自己的第一次卧底。
见到真的毒贩,他的手在颤抖
那一年陈新民25岁,刚刚被招到缉毒队不久。这是他的第一次卧底,跟他行走在一起的,是领着他去缅甸山中接头的线人……
12月的冬夜,无星无月。陈新民望着远远近近茫茫的黑,心里无着无落无底……
接头的两个毒贩子藏在半山腰上的一个背风处。就在他看见毒贩们的一刹那,原来的冷像一张皮,一下子被瞬间凝聚起来的惊、惧、怕,还有心虚给剥离得无影无踪。
他知道自己的膝盖有些发软,腿脚有些不听使唤。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真的毒贩们,他对毒贩们所有所有的一切都不了解。在异国他界,他的身后,除了山,除了河,没有救援,没有一个自己的兄弟。
当其中的那个矮个头的毒贩递给他烟的时候,他才知,他接烟的手也是抖的,差点因抖得不行而将烟掉到地上。擦火点烟的时候,那火几次都灭了。
毒贩们也看见了他的抖,那个矮个头的示意线人退后一步说话:“妈的,这是什么老板?看着他妈的就不像……看他那熊样儿?”
一步之外的陈新民把这话真切地听在耳里,他心急呀,怎么办?他想着他必须得说点什么,可是说什么呀?他知道这个道上混的都不是白给的,都不是傻瓜,他若有一句话编得不圆,他此次就是有来无回。为什么编呢?为什么不可以实话实说呢?实话实说的好处就是不必怕编得有漏洞……
想到此,他冲黑影里的人说:“你还别他妈骂我熊样儿,妈的,我告诉你,我来这儿他妈的心特虚,特怕。刚才过那个河本来我就不敢过,是他硬把我拽着过来的。现在黑吃黑太多,哪有不怕死的?再加上我东南西北也分不清楚,我现在跟你们呆一分钟我心里都怕,都虚得不行。我是手发抖!我受不了,这买卖我不做了,我得走!”
他的这招“以实补虚”还真救了自己。那两个毒贩一听这“黑大个”说的都是大实话,话里也没什么破绽,也就不把他往是否是条子这档子事上想了,因为哪有警察像他这个熊样儿的?那个高个子毒贩赶紧打圆场说:“哎哟,你怕什么呀,告诉你,我们特讲交情!黑吃黑是我们这样的人干的吗?”
毒贩又捅捅线人,暗示线人也一块跟着做做工作,三个人一同围绕着陈新民,给他讲他们在这道上怎么怎么地讲信誉,如何如何地讲交情……
陈新民知道已经打消了他们的疑虑,现在,他们在努力争取他,坚定他把买卖做下去的信心。他说:“这样吧,我实在太累了,身上湿透了,全身发抖。咱们先生个火,烤烤吧!”
矮个说:“不能生。哪有深夜在深山里生火的?火一生,目标特别大!咱这不就是自己把自己往火坑里推了吗?”
初出茅庐的陈新民对毒贩当年所说的这句话一直记忆深刻:道上的人,个个心细如丝,你必须要修炼得比他们更心细才行。大事儿一般不会出纰漏,出纰漏的都是一些过不上心的小细节,而往往是小细节上出了差错而毁了大事儿啊!
陈新民看了一眼线人,看见了那线人背上的背包,眼一亮,说:“哎,咱不是带着酒吗?快快,把咱那酒拿出来,妈的,喝酒!”
陈新民从线人手里夺过酒瓶子咕咚咕咚就把半瓶子酒灌下了肚……
那酒是酒精勾兑的劣质酒,劲头来得特快。陈新民感到内里有一股烧灼的热正将那冷一点一点地逼出体外,真是酒壮怂人胆啊,酒力烧得陈新民那刚刚还禁不住抖颤的胆里仿佛一下子生出了许多的豪气:妈的,不就是几个毒贩子吗?牛什么呀!我他妈不也是条汉子吗!
这样想着,他感觉自己镇定了一些。刚才,大脑就像是进了一场水,思想就像被水泡了,思维自然就不灵光了。
“今晚上呢,咱就是见个面,别的什么事儿咱也别谈。要谈,明天。咱明儿个,先吃饭,先聊天,我请你们吃饭然后再谈,好不好?”他看那两人面有犹疑,他觉得话不能说绝,要给个和缓的坡才行,所以,他紧跟着又调整着说:“不行的话,这样吧,咱时间先定一定,还有,我需要的数量,有吗?”
陈新民以为,既然他是老板、买方,他就得说话硬一点,掌握主动,不能让对方牵着他的鼻子走。
事先讲好的毒品交易数量是25斤,关键的问题是叫价。这犹如演一场戏,只能演好,不能演砸了。陈新民是第一次,他并不懂得毒品买卖的行情,虽然怎么谈事先有人都给他教好了,他的角色就是从底价的1500元开始叫,最高不能超过4000元,最后,是每一件3000元谈定。
鸡卦凶险,他欲擒故纵
价敲定了,毒贩们得先看现钱。
第二天,按事先说定的,在一个小乡镇,陈新民带着他的马仔进到一家小吃店,马仔手里拎着一个小皮箱,箱子里是10元、5元、2元、1元数量不等的钱,2元、1元的居多,被放在箱子的底下,10元和5元的都摆在了箱子的浮头……
一箱钱,大概有七八万元的样子。看也是象征性地给他们看看,箱子打开,就那么一大摞,看一下行了,别想再看,更别想下手到底下探究竟,迅速将箱子盖拢,顺手就递给马仔,赶快把钱收走了,撤退。
他告诉毒贩,买25斤绰绰有余,如果货好,还准备买更多数量:“怎么着,钱也看了,该给我看看货了吧?”
陈新民一提看货,才发现那群人贼呀,个个老手。
一个人说看看吧,几个人便会意要看什么。几个人到附近一个村子里去买小公鸡,干叫的那种小公鸡──会咕咕干叫,后尾上还能“欧欧”出一个声的那种,也就是刚会发情的小公鸡,看鸡卦。
把鸡杀了之后,去骨,先看看鸡头,把鸡头上的毛一点一点地拨开,看看鸡头,然后看看鸡脚,把鸡脚上的骨头刮开,鸡脚上的骨头是很讲究的,每只鸡的鸡脚上的骨头都有鸡眼,看鸡卦的人要看那眼的排序……
最后是看鸡屁股,那叫鸡翘。把鸡翘拨开,看是否完好,完好且像船,再把鸡头上的那个脐插在鸡屁股上,把鸡骨头排列好,看看吉不吉利,顺不顺,路通不通……
看鸡卦的人最后综合这么一看:“不对,不通。”
钱路、财运不通!陈新民心里打鼓鼓,不能久久耗于此,先撤吧,不要再谈了,回去再总结吧。毒贩们是很信鸡卦的。
陈新民这心里急呀,但他装作镇定地说:“行啦,财路不通,走吧!往后再说。我们认识了,往后,如果有缘分的话,咱们走成好哥们!”
陈新民越是作出决意要走的架式,那个看了钱的毒贩便越发地想要做成这笔买卖。陈新民看出他的意思,越发地给添堵着说:“我说,你们还讲迷信,跟你们这帮人做买卖,心里不爽!你们他妈不像道上的哥们!做起事来粘粘糊糊的……”
这几句这么一说,没想更坚定了毒贩们干成这笔买卖的决心。
看卦的圆滑,他也得给那毒贩一个台阶才行,所以,他也装作犹疑的样子说:“也可能鸡不对。”另外的人就附和着说:“对呀,也可能是鸡没挑对!这个鸡可能走水了!”
陈新民看他们这样一说也跟着说:“是啊,你们呀,不是我说你们,这做买卖、做生意是靠自己的脑袋,怎么能靠一只鸡呢?!这人有没有本事是靠人,怎么能靠鸡呢!操,我就感觉到你们是瞎折腾!我对你们没兴趣,我呀,走吧!”
陈新民的这一番话正是起到了欲擒故纵的效果,毒贩拽住他,更不让他走了。几个人在一旁低声商量,讲好了今晚就交货。
双方争执再三,最后定下:凌晨五点,由毒贩送过河交货,以手电为信号,那边亮三下,陈新民这边亮三下。
夜里,设了个埋伏圈。
信号发出,战友们却没有出现
凌晨五点钟,河水清冷。那边有水声,手电筒摇了三下,陈新民也摇了三下,一个人冻得嗑嗑发抖地游过来。
游过来的这人,两手空空。
陈新民说:“你他妈怎么空着手来?”
那人发抖着说:“得再看看钱。”
陈新民让他看钱。看了,又给那边发了信号。
左等没人来,右等还是没人来。晨风扎骨地凉。陈新民说:“他妈的再不来,天就亮了,谁也跑不了。”
很长时间过去了,还是没人来,那小子冻得浑身发抖,紧挨着陈新民吸烟。
陈新民说:“他妈的你没看天快亮了,我不等了,我得走了!”
那小子狠狠地把烟一扔,折头回去叫人拿货。
那人把货一接手,哗哗地搅着水又过来了。
陈新民拿着火柴棍挑出一点出来,一烧,闻着那味,挺香,很特别的那种味道,而且,很快,很平稳地,没有其他响声就烧完了。
划火柴其实是给自己人发的一个信号,告诉布圈的人该动手了。
可是,陈新民划了火柴,一烧,旁边却没有动静。
那一个时刻,货在陈新民手里,钱在那个人怀里,那个人,他抱住那个钱箱子,只要一涉河就走了。
陈新民急中生智拖住那人说:“不行,你这货是多少?我感觉你这货不对呀?”
那人说:“哎呀,妈的,昨天晚上他们拿去了5斤,现在是20斤……”
“你奶奶的,你想蒙我?他妈的你太贼了你!你得让我把那5斤的钱撤出来呀!我还得检查一下,这里面是不是全是真的?”
那人说:“全是真的,这不蒙你。”
陈新民说:“不行,我看看,你别他妈的把牛屎给我包一包来充他妈的货,那怎么能行?”
他又把毒品掏出来,又划着火柴,又烧。这时候,陈新民终于看见远处有人一边跑一边喊“不许动”……
那人听见喊,泥鳅一般扔下钱入水跑了。
陈新民冲着喊“不许动”的人愤怒地喊:“你们怎么搞的?发半天信号受了半宿冻你们就是不出来,出来还懒洋洋地喊什么‘不许动’!不许动什么球呀?这他妈的要人命的!”
年轻的陈新民在凌晨五点多钟的光景里咆哮过。那时候初生牛犊,那时候血气方刚,但,那时候真的是没有经验啊,整个缉毒队都是新的,新的人,新的面孔,新的队伍……
这许多年过去了,陈新民从来没有给人讲过第一次卧底的故事,而这个第一次是他的缉毒生涯的开端和始点,他总能想起站在那个河岸上的自己:那一天,他其实也没有咆哮的理由,因为计划虽然严丝不怠,可是,所有执行任务的人都没想到,12月的冬日的凌晨,河岸上有雾,雾浓浓密密,划火柴的那个亮光很难穿透大雾传给自己的战友们……
他的战友们也是估摸着:“差不多了吧?怎么这么久还没动静?陈新民不会出危险吧?”他们没有看见他发的信号,他们是估摸着冲进包围圈的……
许许多多年过去了,陈新民和他的战友们一直生死相依。■
(陈挺荐自《法律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