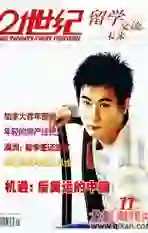用石头书写的史书
2008-11-19知音
知 音
还是原来的那个前门大街吗?
2008年8月7日,北京奥运会召开的前一天,也是前门新大街的开街日。这条曾经记录典型的老北京市民生活的古老街道,经“大力”修缮后的开街,迎来了无数想一睹其风采的中外游客,用摩肩接踵、人山人海来形容绝不为过。而且,这一现象从8月的奥运会、9月的残奥会,一直持续到“十一”黄金周之后到现在。不过,说起人们的感受,一位在开街那天去过的记者在他的博客里这样写道:
“我们坐在慢悠悠行驶的铛铛车上,看着街道两边的仿古建筑和落地大玻璃窗;我们穿梭于各式各样的北京老字号里,一回头,却看见的是世界知名的奢侈品牌。那时,不知道感受到的会是奇妙的时空穿梭感,还是混沌的时空错乱感。”
“现在的前门大街,那还是原来的前门吗?”发出这质疑声音的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研究所讲师,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乡土建筑研究所副所长罗德胤博士。
罗德胤,还有他的导师陈志华先生,是目前少数一些执著于乡土建筑保护的学者,在当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他们的呼声与推土机的轰隆声相比,实在是太微弱了,难免不被淹没。
乡土建筑保护是近几年新兴起来的学科,是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一部分。用陈志华先生的话说:“文化遗产保护是比登月亮还要新的学科。”因为这门学科的形成和被人接受是在上世纪70年代,比登月还晚。要让大多数人接受,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面对被无数次提起过的“圆明园要不要重建”的话题和一些支持重建的呼声,罗德胤说,大家都知道的是,圆明园是被英法联军烧掉的,其实英法联军烧掉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英法联军走了以后,由于没有人管理,大量的老百姓住进去,需要自己盖房子、用材料,就不断地拆建、破坏,大部分破坏是由中国人自己造成的。
当下在中国,重建历史与人文景观之风盛行,在重建与否的争论中,牵扯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保护?如何去保护?为什么要重建?重建的意义何在?
乡土建筑在迅速地消失
2005年,一个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在走完长安街后感叹:“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规划设计遗产的国家,正在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
很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谈到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时以“像个大工地”来概括,准确地说出了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破旧立新”、进行大量基础建设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像北京四合院在内的中国乡土建筑,其遭遇是毁灭性的。伴随着一座座高楼大厦的立起和一条条胡同的消失,老北京的市井文化、胡同文化也随之不复存在了。
浙江西南角有一个叫二十八镇的地方,一座座带有江南特色的房子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在当地百姓改善自己居住环境的欲望驱使下,拆了这些漂亮的旧房盖新房几乎成了全镇上下的一致举动,住着高楼大厦的人们,有什么理由去阻止他们呢?
也有自然消失的。河北省蔚县,历史上是内地与塞外的必经之地,频繁的战乱形成了这里的独特建筑景观——村村都是城堡,全县有上千个城堡之多。当年的景象如果航拍下来,肯定蔚为壮观。随着铁路的修通和社会的安定,人们不再在修葺城堡上花费气力,多年的风雨侵蚀,城堡的坍塌与消失在人们眼中成了正常的事情。现在,能数出来比较完整的城堡大概只有100多个了。
类似的情况在全国每个省份里都可以找到,而有计划地将这些建筑保护起来的全盘计划似乎并没有耳闻。专家们提出:全国找出300个聚落或村落保护起来是不是可行?目前,这样的提法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中国乡土建筑的历史价值体现
乡土建筑,指得是乡土社会中的建筑。一般指建在农村、乡镇的建筑,也包括北京的四合院。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一小部分人住在城市外,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可见乡土建筑对于中国之尤为重要。
有句话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对中国建筑来说,可以说建筑是木头的史书。只要是史书就会携带不同时期那个领域的信息,乡土建筑记载了中国5000年的农业文明,它的价值涵盖了艺术、科学、情感和使用诸多方面。比如人们说某个建筑好,就是指当时工匠的水平很高,具有艺术的价值。建筑又有情感价值,比如圆明园,对中国人来说有强烈的、复杂的民族情感在里面,重建也好,不重建也好,都不能否认这一点。目前大量还在使用的老房子,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建筑的使用价值,文革期间的破四旧之举,将神像统统砸掉,却被保留下庙宇,将神明的祭祀场所变成了粮库、牲畜棚,甚至住家。
然而,往往被人忽略的是建筑的历史价值,“但恰恰这一点是确定其是否是文化遗产的关键。”罗德胤说,“因为,同其它的价值相比,只有历史价值是无法改变、没有任何弹性的,你欣赏它也好,恨它也好,有用也好,无用也好,都无法否认它。同时,它超乎于个人、国家和民族标准之上,它记载着人类知识的传承,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把是否具有历史价值作为文化遗产的核心,包括历史上的乡土建筑。”
因此说,文化遗产绝不仅仅是让现在的人们看一下享受一下体会一下怀念一下旧东西的事情,它是知识的象征和载体。保留它们,有利于了解人类不断积累的步伐。毁掉了,这个载体不存在了,它所承载的知识与历史的信息也就不存在了。从这个角度说,所有的文化遗产意义都十分重大。
罗德胤说:“单独看一座座房子,好像保护的意义确实不大。故宫毁了我们照样能上班,能吃饭。但是只要把故宫保留下来,一旦人们看见故宫,作为中国历史上建筑的代表,它就是一种知识的传承。”中国的乡土建筑,是东方农业文明的见证,见证着我们如何从农业文明一步步走来的印记。在世界已经从传统走到现代的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正处在高速发展当中,乡土建筑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地被破坏和消失似乎无法避免。为了让后代能够认识我们的传统,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很必要,意义特殊。
绝不是简单地“修旧如旧”
当今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往往受到商业行为的掣肘。罗德胤说,我们做文化遗产普查,前脚刚出门,文物贩子后脚就来了,跟老百姓讨价还价,反而加快了破坏的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等于是给盗墓者提供了线索。
中国已经完成和正在修建的仿古建筑多如牛毛,多为借“文化遗产”之名,实现商业目的之举。罗德胤说,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经历了几个流派之后,确立了现在国际上公认的遗产保护的原则。
在英国,阴霾有雨的天气让人总是崇拜一种废墟般的浪漫的想象,叫做富有诗意的死亡的浪漫情结,使得他们主张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一点都不让动,就是要看着破破烂烂的,人称废墟派。现在到英国还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地方,这自然有它的价值。
法国的建筑师是大手笔、完美的推崇者。他们喜欢将建筑按照一种特别理想的方式,形成一种大轴线的构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毫不吝惜地破坏一些老建筑。其代表就是豪斯曼的巴黎规划,把从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城市、特别有情趣的小城镇巴黎,嘁里咔嚓几刀切下去,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轴线,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就是那时的产物,人称建筑师派。这个做法在今天的中国很流行,如北京内城。
1964年写进《威尼斯宪章》、逐渐被世界上的文化遗产界人士接受并成为国际上主流的,是意大利的历史学派。其主张向考古学家学习,尊重历史,历史是什么样的,就让它是什么样。历史学派的核心思想就是要保存历史信息,其原则不超过20个字,即:原真性;最小干预(能不动就不动,能少动就少动,能简单支撑就不拆掉重建);可识别性和可逆性。
当然,在实际当中,百分之百地保护古建筑的历史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凡是为延长其寿命的保护措施,其增加的部分多少会有副作用。加上与保护相比,拆掉重建最简单、最省钱,因此在实践中,拆掉重建是目前看到的普遍现象。所以说,急功近利的短视是造成传统文化流失的渊薮。
有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高境界。阿富汗最著名的、高达35米的巴米扬大佛被塔利班炸成了一片废墟后,日本人出钱做了一个程序,把所有的石块都进行扫描,然后用计算机计算编号,把它重新垒回去。计算机的正确率只有90%,于是他们用一种可以卸掉的材料不完全粘死,告诉人们,如果以后计算机水平达到100%,可以卸掉重粘。罗德胤说,“这就是可逆性的最高境界,要花很多钱、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是这门学科从此建立起来了。”这也证明了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历史价值,尤其是对中国的乡土建筑。
还有,对建筑师来说,他们希望创新和创造,与文物保护的思维是相逆的,觉得不能从这里面体现自己的价值,这是个很突出的矛盾,在中国,很多建筑师只注重自己的创造力,常常忽视尊重历史,致使几乎所有文化遗产的操刀人都是建筑师。
建筑师如是说——
被保护“死”的遗产
罗德胤:拿现代人的居住标准去要求古代人的房子,那肯定不现实。上百年的房子很难不成为危房,所以才要修缮。把老房子定义成危房,然后以危房为由将它拆掉,这是逻辑混乱。我们提倡的原则是里面能住人的传统建筑,能不拆就不拆,实在是住不了人了,我们可以先把人迁出来,再进行修复。修复的时候尽量找和原来的建筑相同的材料,尽可能保护它的历史信息。但这么一来,很多建筑师和开发商就不干了,因为太麻烦了,又浪费时间,没办法满足工期,于是就怎么简单怎么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拆掉重建,“多快好省”。
张闻鹤: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仅是一个政府行为,他更多地涉及到民众的认识问题。中国人从来就有喜新厌旧的传统。比如说古时候,一个地方出了举人,就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如果明年再出的话就再修一遍。还有我们办奥运会,就要把整个北京城重新刷一遍,其实这对古建筑是一个很大的损坏。我觉得建筑师首先得有这个意识,旧的并不代表它没有价值,我们得先学会保护建筑的原生态,再谈其他。
我觉得我们不是不保护,而是太想保护了,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破坏。中国有很多遗产是被“保护”死的。野蛮拆除的不说,很多遗产由于人们的无知和过分在意,而得到了超出正常维修范围的“保护”。其实未必非得做什么,放在那里就好了,比如长城。没见过埃及人把胡夫金字塔的尖补齐的。
乡村,我们的精神家园
龙翔:我一直认为中国最美的地方在乡村,那种男耕女织、很生态的田园风光,房子也是统一的建筑语言,因地而建。但现在因为城市化的原因,很多农村消失了,或是很多农村的建筑生态被破坏掉了,所以现在的农村反倒变成最丑的地方了。其实我们最应该进行的是农村的文化遗产保护,比如乡土建筑的维护等等,因为在后工业时代,城市没多大吸引力,人最终会从城市里出来的。城市给人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接受良好教育的过程,而乡村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希望建筑界多关注一下农村文化遗产保护,虽然设计费可能会比较少,但却是很值得关注的。
我们保护那些老胡同、老建筑,不仅仅是为了让北京看起来像北京,更是要记住历史,要让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反省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