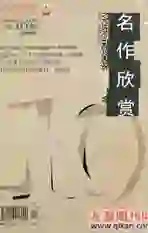归去来
2008-10-21韩少功
韩少功
很多人说过,他们有时第一次到某个地方,却觉得那地方很熟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我也得到这种体验。
我走着。土路一段段被山水冲坏,留下一棱棱土埂和一窝窝卵石,像剜去了皮肉,暴露出一束束筋骨、一块块干枯了的内脏。沟里有几根腐竹,有一截烂牛绳,是村寨将要出现的预告。路边小水潭里冒出几团一动不动的黑影,不在意就以为是石头,细看才发现是小牛的头,鬼头鬼脑地盯着我。它们都有皱纹,有胡须,生下来就苍老了,有苍老的遗传。前面的蕉林后面冒出一座四四方方的炮楼,冷冷的炮眼,墙壁特别黑暗,像被烟熏火燎过,像凝结了很多夜晚。我听说过,这地方以前多土匪,什么十年不剿地无民,怪不得村村有炮楼,而且山民的房子绝不分散,互相紧紧地挤靠着,都厚实,都畏缩,窗户开的小眉小眼的,又高,盗匪不容易翻进去。
这些很眼熟,也很陌生;像平时看一个字,越看越像,也越看越不像。见鬼,我到底来过这里没有呢?让我来推测一下吧:踏上前面那石板路,绕过芭蕉林,在油榨房边往左一折,也许可以看见炮楼后面一棵老树,银杏或者是樟树,已经被雷劈死了。
片刻之后,推测果然被证实了。连那空空的树心,树洞前有两个小娃崽在烧草玩耍,似乎都在我的想象之中。
我又怯怯地推测:老树后面可能有栋矮矮的牛房,房前有几堆牛粪,檐下有一张锈了的犁或耙。当我走过去,它们果然清清晰晰地向我迎来!甚至那个歪歪的麻石舂臼,那臼底的泥沙和两片落叶,也似曾相识。
当然,想象中的石臼里是没有泥水的。但细一想,刚下过雨,屋檐下不应该流到那里面去吧?于是,凉气又从我的脚跟升上来,直上我的颈后。
我一定没有来过这里,绝不可能。我没得过脑膜炎,没患过神经病,脑子还管用。也许是在电影里看过?听朋友们谈过?或是在梦中……我慌慌地回忆着。
更奇怪的是,山民们似乎都认识我。刚才扎起裤脚探着石头过溪水时,一个汉子挑着两根扎成A字形的树,从上边来。见我溜溜滑滑,就从路边的瓜棚里拔出一根干树枝,丢给我,莫名其妙地露出一口黄牙,笑了笑。
“来了?”
“嗯,来了……”
“怕有上十年了吧?”
“十年……”
“到屋里去坐吧,三贵在门前犁秧田。”
他屋在哪里?三贵又是谁?我糊涂了。
随着我走上一个小坡,一片檐瓦门庭在前面升起来。几个人影在地坪中翻打着什么,连枷摇得叭叭响,几下重,又有一下轻。他们都赤脚,蓄寸头,脸上有棕色的汗釉,釉的边缘残缺不齐。日光下一晃,颧骨处的汗釉有一小块反光。上衣都短短地吊着,露出软和的肚皮和脐眼,裤边也松松地搭在胯骨上。只有发现他们中的一个走向摇篮开始解怀给小孩喂奶,又发现都挂了耳环,才知道她们——是女人。有一位对我睁大了眼。
“这不是马……”
“马眼镜。”另一个提醒她。觉得这个名字好笑,她们都笑了。
“我不姓马,姓黄……”
“改姓了?”
“没改。”
“就是,还是爱逗个耍方呵?哪里来的?”
“当然是县里。”
“真是稀方客。梁妹呢?”
“哪个梁妹?”
“你娘子不是姓梁?”
“我那位姓杨。”
“未必是吾记糟了?不会不会,那时候她还说是吾本家哩。吾婆家是三江口的,梁家畲,你晓得的。”
我晓得什么?再说,那个什么又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似乎是想去找她,却来到了这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
这位大嫂丢下连枷,把我引进她家里。门槛极高,极粗重,不知被多少由少到老的人踩踏过,坐过,已经磨得中部微微凹了下去。黄黄的木纹,像一圈圈月光在门槛上扩散浸染开来,凝成了一截化石。小娃崽过门槛要靠爬,大人须高高地勾起腿才能艰难地倾着身子拐进去。门内很黑,一切都看不清楚。只有一个高高的小窗眼漏下一点光线,划开了潮湿的黑暗,还有米潲和鸡粪的气味。好半天瞳孔才适应过来,可以看见壁梁上全是烟灰,还有同样苍黑的一个什么吊篓。我坐在一截木墩上——这里奇怪的没有椅子,只有木墩和板凳。老妇和少妇们都叽叽喳喳地挤在门边,喂奶的那位毫不害羞,把另一只长长的奶子掏出来,换到孩子嘴里,冲我笑了笑,而换出的那一只还滴着乳汁。她们都说了些奇怪的话——“小琴……”“不是小琴。”“是吧?”“是小玲。”“哦哦。小玲还在教书吧?”“何事不也来耍耍呵?”“你们都回了长沙吧?”“是长沙城里还是长沙乡里?”“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小罗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陈志华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熊头呢?找了娘子没有?”“也有娃崽了吧?一个还是两个?”……
我很快觉察到,她们都把我错当成一个既认识什么小玲也认识什么熊头之类的“马眼镜”了。也许那家伙同我长得很像,也躲在眼镜后面看人。
他是什么人?我需要去想他吗?从女人们的笑脸来看,今天的吃和住是不成问题了,谢天谢地。当一个什么姓马的也不坏。回答关于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让女人们惊讶或惋惜一阵,不费气力。
梁家畲来的大嫂端来了一个茶盘,四大碗油茶,我后来知道,这是取四季平安的意思。碗边黑黑的,令我不敢把嘴沾上去,不过茶倒香,有油炒芝麻和糯米的气味。她把地下两条娃崽的脏衣捡起来,丢进木盆,端到里屋去了,于是一句话被分切成两截:“老久没有听到你的音信,听水根夫子话……(半晌才从里屋出来)你一回去,就坐了大牢?”
我吃了一惊,差点让油茶烫了手。“没有。什么大牢?”
“背时的水根,打鬼讲!害得吾家公公还吓心吓胆,为你烧了好多香。”她捂嘴笑起来,“哎呦,要死了。”
妇女们都笑起来。有一嘴黄牙还补充:“还到戴公岭求了菩萨呢。”
真是晦气,扯上了香火菩萨。也许那个姓马的真的撞了什么熊,有牢狱之灾,而我代替他在这里喝油茶,在这里蠢笑。
大嫂又端上了第二碗茶,一只手照例横搭在端茶这只手的腕子上,大概是一种礼节。而我第一碗还没有喝完,水干了,芝麻和糯米却没有滑到碗边来,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斯文体面地吃上。“他老是挂牵你,说你仁义,有天良。你那件袄子,他穿了好几个冬天。他故了,我就把它改了条棉裤,满崽又穿……”
我想谈谈天气。
屋里突然暗了下来,回头一看,一个黑影几乎遮挡了整个门。看得出是个男的,赤着上身,隆起的肌肉没有曲线,有棱有角像一块块岩石。手里提着一个什么东西,从那剪影来看,是个牛头。黑影向我笼罩过来了,没容我看清面孔,嗵地一下丢掉了手里的东西,两只大掌捉住了我的手锉起来。“是马同志呵,哎哟哟,呵呀呀……”
我又不是一只毛虫,惊恐什么呢?
当他转到火塘边,侧面被镀上了一层光亮,我这才看清是一张笑脸,有黑洞洞的大嘴巴,两臂上都刺了些青色的花纹。
“马同志,何时来的?”
我想说我根本不姓马,姓黄,叫黄治先,也不是深沉而豪迈地来寻访旧地的。
“还识(认?记?)得吾吧?你走的那年,还在螺丝岭修公路,吾叫艾八呵。”
“艾八,识得识得。”回答得很卑鄙,“你那时候当队长。”
“不是队长,吾记工。你嫂子,还识不识哟?”
“识得识得,她最会打油茶。”
“吾同你去赶过肉的,识不识得?(赶肉,是否就是打猎?)那次吾要安山神,你话(说?),那是迷信。收末还不是,你碰上牧麻草,染了一身毒疮。那回你还碰了只麂子,从你胯下过,没叉着……”
“嗯嗯,没叉着,就差一点点。我眼睛不好。”
黑洞洞的大嘴巴哈哈笑起来。女人们慢慢起了身,摇晃着宽大的臀部,出门去了。自称艾八的男人搬出一个葫芦,向我大碗大碗敬酒。酒很浑浊,有甜味,也有辣味和苦味,据说浸过什么草药和虎骨。他不抽我的纸烟,用报纸卷喇叭筒,吸一口,烟纸烧起了明火。他不急,甚至看也不看一眼,带我急了好一阵,才从从容容一口气把明火荡灭,烟还是好好的。
“如今酒肉尽你吃,过年,家家都宰了牛。”他抹着嘴巴,“那年学大寨,谁都没得禄。你晓得的。”
“是没得禄。”我想谈谈大好形势。
“你视见德尤哥了吗?他当了乡长,昨日到捉妹桥栽树去了,兴许回来,兴许不回来,兴许又会回的。”他谈起一些令我糊涂的人和事:某某做了新屋,丈六高;某某也做了新屋,丈八高;某某也要做屋了,丈六高;某某正在打地基,兴许是丈六也兴许是丈八。我紧张地听着,捕捉这些话后面的各种脉络。我发现这里的话有些怪,看成了“视”,安静成了“净办”。还有一个个“集”,是起的意思?还是站立的意思?
我有点醺醺然了,对丈六或丈八胡乱地表示着高兴。
“你这个人过得旧,还进山来视一视。”他又把烟纸吸出了浅浅的明火,又让我暗暗急了两秒钟。“你当民师那阵发的书,吾还存着哩。”他咚咚地上楼,好半天才头顶几丝蜘蛛网下来,拍着几页黄黄的纸。这是几页油印的小书,大概是识字课本,已经撕去封面了,散发出煤气和桐油气。上面好像有什么夜校歌谣、农用杂字、辛亥革命,还有马克思论农民运动及什么地图,印得很粗糙,一个个字大得很,还有油墨团子。我觉得这些字我也能写出来,没什么稀奇的。
“你那时也遭孽,饿得脸上只剩一双眼睛,还来讲书。”
“没什么,没什么。”
“腊月大雪天,好冷啊。”
“好冷的,鼻子都差点冻落。”
“还要开田,打起松明子出工。”
“嗯啦,松明子。”
他突然神秘起来,颧骨上那一小块光亮,几颗酒刺,朝我逼近了。“吾想打听件事,阳矮子是不是你杀的?”
什么阳矮子?我头盖骨乍地一紧,口腔也僵硬了,连连摇头。我压根儿不姓马,也没见过什么阳矮子,怎么刑事案都往我身上扯?
“都话是你杀的。那家伙是条两头蛇,该杀!”他愤怒着,见我否认,似乎有点怀疑,又有点遗憾。
“还有酒没有?”我岔开话题。
“有的有的,尽你的量。”
“这里有蚊子。”
“蚊子欺生,要不要烧把草?”
草烧起来了。又有一批批的人来看我,拐进门来,照例问起身体可好和府上可安一类。男人们接过我的纸烟,滋滋地抽得很响,靠门或靠墙坐下,眯眯笑,不多言语。听他们自己偶尔说上一两句,有的说我胖了,有的说我瘦了;有的说我老多了,有的说我还很“少颜”,当然是由于城里的油水厚。直待烟烧完,他们又笑一笑,说是去倒树或下牛粪,有几个娃崽跑过来,把我的眼镜片考察了片刻,然后紧张得兴高采烈,恐惧得有滋有味,“里面有鬼崽!有鬼崽!”一边宣告一边四下奔跑。一位姑娘,总是咬着一根草站在门边,痴痴地望着我,还好像亮晶晶地旋着泪花,不知是什么意思。弄得我很不自在,只好正经地总不时地盯住艾八。
这类事我已经碰得多了,刚才去看他们种的鸦片,路上碰到一位中年妇人。她一见我就显得恐惧,脸像一盏灯突然暗淡,赶紧拔着鞋后跟,低头择路而去,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艾八说我还应该去看看三阿公——其实三阿公已经不在,说是不久前被蛇咬死了,只是在人们的谈论中,还留下一个名字。在砖窑那边,还有他一栋孤零零的小屋,已有一半倾斜,眼看就要倒塌。两颗大桐树下,青草蓬蓬勃勃地生长,有腰深,已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阴险地迈上了台阶,摇着尖舌般的草叶,像要吞灭小屋,像要吞灭一个家族的最后几根残骨。挂着锁的木门,已被虫蛀出了密密的黑洞。我不知道主人在的时候,房屋是否会破败得这么厉害。难道人是房屋的灵魂,灵魂飞去,躯壳就会腐朽得这么迅速吗?草丛里倒栽着一盏锈马灯,上面有几点白白的鸟粪。还有一个破了的瓦罐子,你一碰,罐子里就嗡地一下涌出很多蚊子。艾八说这瓦罐总是浸酸菜,当年我经常到三阿公家里来吃酸黄瓜的(是吗?)。墙上灰壳剥落,隐隐约约有几个油漆字,仅笔触的边沿还未完全褪色:“放眼世界……”艾八说那还是我写的(是吗?)。艾八扯了一把车前草,又打望树上的鸟窝。我则朝窗里瞥了一眼,见屋角有半筐石灰,还有一个大圆盘,细看,发现是铁杠铃,绣得不成样子了——我感到惊异,这种罕见的体育用品,怎么会出现在深山里?怎么运到这里来的?
大概不用问,也是我送给三阿公的,是么?我把它送给三阿公去打锄头或耙头,而他终究还是没有打。是么?
有人在坡上唤牛:“呜吗——呜吗——”于是对面的林子里有隐隐的牛铃声。这里唤牛的方式比较奇特,像喊妈妈,喊得很凄凉。也许那炮楼的砖壁就是被它喊黑的罢。
一位老阿婆背着小小的一捆柴,从山上下来。腰弯得几乎成了直角,走一步,扯出的下巴就一锄,像锄的步子。她深深地仰望了我一眼,几乎不是看我,而是从前面看到了我脑后的桐树,模糊的黑瞳孔全顶着上眼皮,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满脸皱纹深刻得使我一震。她看看三阿公的老屋,又回头看看寨子口上的那棵老树,没头没脑地咕噜了一声:“树也死了。”又慢慢地锄着步子远去。头上几根枯枯的银丝,随着风压下去,压下去。
我现在相信,我确实没有来过这里。我也无法理解老阿婆的这句话——一个无法看透的深潭。
晚饭弄得很隆重,牛肉和猪肉都大模大样,神气十足,手掌大一块,熬得不怎么熟,有一股生腻味。堆出了碗口,就系上草箍,一层层往上码,像码砖窑——几千年前就有这种吃法罢。男客才能上桌。有一位没到,主人在空着的位子上放了一张草纸,大家吃一块,往纸上夹一块算是他也吃了。席间我谈到了香米,他们根本不肯出价钱,简直是要白送。至于鸦片,今年鸦片好是好,但国家药材站统购。我不好再说什么。
“阳矮子该杀。”艾八嗬嗬地喝下一口热汤,把汤勺放回桌面那黏糊糊的老位置上,又眼盯肉碗敲着筷子,“翘屁股,圆手板,什么工夫都做不像,还起屋,不就是阴毒?”
“就是,哪个没挨过他一绳子?吾腕子上现在还两道疤。操她老娘顿顿的!”
“他到底是何事死的?真的碰了血污鬼,跌到崖墈下去了?”
“人再狠,拗不过八字。命里只有一升,偏要吃一斗。夏家湾的洪生也是这个样。”
“连老鼠都吃,几多毒辣!”
“是蛮毒辣,没听见过的。”
“熊头也遭孽,挨了他两巴掌。明明是几袋颜料,吾视见过的,染不得布,只画得菩萨伢子。他说是炮子。”
“也怪熊头的成分大了点。”
我鼓足勇气插了一句:“阳矮子的事,上面没派人来查过么?”
艾八咬得一块肥肉吱吱响:“查过的,查卵!那天来找我,我就去寻鸡婆,哎,马同志,你的酒没动呵?来,取菜取菜,取。”
他又压给我一大块肉,我喉头紧缩,只好再次做出去装饭的模样,躲入暗处,把肉拨给了胯下一挤而过的狗。
饭后,他们说什么也要让我洗澡,我怀疑这是不是当地一种风俗,得装得很懂。没有澡盆,只有澡桶,很高大,足可以装几大锅热水,就放在灶屋一角,女人们可以在桶前来来去去,梁家畲来的大嫂还不时用瓜瓢来加水,使我不好意思,往桶内一次次蹲,只要她提桶去喂猪,才偷偷出了口长气。我已经洗得一身发热,汗气腾腾了。大概水是用青蒿熬出来的,全身蚊虫咬出来的红斑也不怎么痒了。头上那盏野猪油的灯壳子,在蒸气中发出一团团淡蓝色的光雾,给肉体也抹上一层蓝。穿鞋之前,我望着这个蓝色的我,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好像这身体很陌生,很怪。这里没有服饰,没有外人,就没有掩盖和作态的对象,也没有条件,只有赤裸裸的自己,自己的真实。有手脚,可以干点什么;有肠胃,要吃点什么;生殖器可以繁殖后代。世界被暂时关在门外了,走到那里就忙忙碌碌,无暇来打量和思量这一切。由于很久以前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的巧合,才有了一位祖先;这位祖先与另一位祖先的再巧合,才有了另一个受精卵子,才有了一个个世世代代以后可能存在的我。我也是连接无数偶然的一个蓝色受精卵子。来到世界干什么?可以干些什么?……我蠢头蠢脑地想得太多了。
我擦拭着小腿上一道寸多长的伤痕,这是足球场上被一只钉鞋刺伤的。似乎也不是,而是……一个什么矮子咬的。是那个雨雾蒙蒙的早上?那条窄窄的山道上?他撑着阳伞过来,被我的目光吓得颤抖了。然后跪下,说他再也不敢,再也不敢;还说二嫂的死与他毫无关系,三阿公的牛也不是他牵走的。最后,他反抗,眼球凸得像要掉出来,咬住了我的腿。双手开始揪住套着喉管的一根牛绳,接着又猛地伸开去,像两只螃蟹在地上爬着,弹着,抠进泥沙里。不知什么时候,这两只螃蟹才慢慢地休息了,安静下来……
我不敢想下去,甚至不敢看自己的手——是否有股血腥味和牛绳勒出的痕迹?
我现在努力断定,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也不认识什么矮子。这一团团蓝色的光雾,甚至梦也没有梦见过。没有。
堂屋里很热闹。有一位老人进来,踩灭了松明子,说他以前托我买过染布的颜料,欠了我两块钱,现在是还钱来的,又请我明天到他家去吃饭和“卧夜”。这就同艾八争起来了,艾八说他明天接裁缝,已经砍了肉,明天我毫无疑义地该到他家去……
趁他们还在争执,我潜出门,浅一脚深一脚,想去看看“我”以前住过的老屋——听艾八说,就是说树后的牛房。前年才把它改做牛房的。
又经过桐树下,又看见了杂草将要吞灭的老阿公——倾斜茅屋的黑影。它静静地望着我,用乌鸦的叫声咳嗽,用树叶的沙沙声与我交谈。我甚至感到了一股似有似无的酒气。
孩子,回来了么?自己抽椅子坐下吧。吾对你话过的,你要远远地走,远远地走,再也不要回来。
可是,我想着你的酸黄瓜。我自己也学着做过,做不出那个味来。
那些糟东西有什么好吃呢?那时候是视见你们饿,遭孽,一犁拉到头,连田塍上的生蚕豆也剥着吃。吾才设法子做一点。
你总是惦记着我们,我知道的。
谁没个出门的时候呢?那是该的。
那次担树杈,我们只担了九担,你记数,总说我们担了十担。
吾不记得了。
你还总要我们剃头,说头发和胡须都是吃血的东西,留长了会伤精气。
是么?吾不记得了。
我该早点一来看你的。我没想到,变化会这么大,你走得这么快。
该走了。再活不快成精了么?吾就是喜欢一口酒,现在喝足了,可以安安稳稳睡了。
阿公,你抽烟么?
小马,喝茶自己去烧吧。
……
我离开了那股酒气,举着将要熄灭的松明子,想着明天早上的农活,不时听到脚边的青蛙跳到水圳里去,回家了。但我现在手中没有松明子,我的家也变成了牛房,显得如此生疏和冷漠,看不清什么,只有牛反刍的声音,还有牛粪草热烘烘的酸气,涌出门来。牛以为是主人来了,头挤头往外探,碰得门栏咔哒响。我一走,脚步声就从牛房的土壁上回过来,像还有一个人在墙那边走,或是在墙土里面走——这个人知道我的秘密。
对面的山壁黑森森的,夜里比白日里显得更高大更近了,使你有呼吸困难的感觉。仰望头上那宽窄不匀的一线星空,地近天远,似乎自己就要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拉住,就要往这地缝深处沉下去再沉下去。
巨大的月亮冒出来,寨里的狗好像很吃惊,狺狺地叫。我踏着树影筛下的月光,踏着水藻浮萍似的圈圈点点,向溪边走。我猜测,在溪边可能坐着一个人,也许是一位姑娘,嘴里正含着一片木叶。
溪边没有人。但我回来时,终于见老树下有一个人影。
夜色这样好,是该有个剪影的。
“是小马哥?”
“是我。”居然应答得毫不慌张。
“从溪边来?”
“你……你是谁?”
“四妹子。”
“四妹子,你长得好高了。要是在外面碰到,会根本认不出你。”
“你跑的世界大,就觉得什么都变了。”
“家里人都好吗?”
她突然沉默了,望着那边的榨房,声音有些异样。“吾姐,好恨你……”
“恨……”我紧张地瞥了瞥通向灯光和地坪的路,想逃跑,“我……很多事不好说。我对她说过……”
“那天你为哪样要往她背篓里放苞谷呢?女崽家的背篓里,随便放得东西的么?她给了你一根头发,你也不晓得么?”
“我……我不懂,不懂这里的规矩。我……想要她帮忙,就让她背几个苞谷。”
大概回答得不错,还可以混过去。
“人家都这样话,你是个聋子么?我都视见过,你教她扎针。”
“她喜欢学,想当个医生。其实,我那时也不懂,只是乱扎。”
“你们城里人,是没情义的。”
“不是这样……”
“就是!就是!”
“我知道……你姐姐是个好姑娘,我知道的。她歌唱得好听,针线也做得巧。有一次带我们去捉鳝鱼,下手就是一条。我病了,她哭得好厉害……我都是知道的,可是,有好些事你们不懂,也说不清楚。我一生都会奔波辛苦,我……有我的事业。”
终于选择了“事业”这个词,尽管有点咬口。
她捂着脸抽泣起来。“那个姓胡的,好狠毒哩。”
我似乎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继续试探着回答下去:“我听说了,我要找他算账。”
“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她跺着脚,哭得好伤心了,“你要是早说一句话,也不会成这个样。吾姐已变成了一只鸟,天天在这里叫你,叫你。你听见没有?”
月光下,我看见她瘦削的背脊在起伏,上面是光滑的颈脖,甚至头发中缝中白白的头皮也清晰入目。我真想给她擦泪,想抓住她的肩膀,吻她那头皮,像吻我的妹妹,让她的泪水贴到我的嘴唇上,咸咸的,被我吞饮。
但是我不敢,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我不敢舔破它。
树上确实有只鸟在叫唤,“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声音孤零零的,像利箭射入高空,又飘忽忽地坠入群山,坠入绿林,坠入远方那一抹乌云和无声的闪闪雷电中。我抽了支烟,望着雷电,像在对无声的历史问话。
行不得也哥哥。
我走了,行前给四妹子留了封信,请梁家畲来的大嫂转交。信中说她姐姐以前想当医生,终究没当成,但愿妹妹能实现姐姐的愿望。路是人闯的,她愿意投考卫生学校么?我将寄给她很多很多复习资料,一定。我还说,我不会忘记她姐姐。艾八把那只树上的鹦鹉捕住了,我将带回去,让它天天在我的窗前歌唱,与我成为永远的朋友。
我几乎像是潜逃,没给村寨里的人告别,也没顾上香米——其实我要香米或鸦片干什么呢?似乎本不是为这个来的。整个村寨,整个莫名其妙的我,使我感到窒息,我必须逃。回头看了看,又见寨口那棵死于雷电的老树,伸展的枯枝,像痉挛的手指。手的主人在一次战斗中倒下了,变成了山,但它还挣扎着举起这只手,要抓住什么。
进了县镇的旅社,在床头鹦鹉的咕咕嘟嘟声中入睡。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还在皱巴巴的山路上走着,土路被山水冲洗得像剜去了皮肉,留下一束束筋骨和一块块干枯了的内脏,来承受山民们的草鞋。这条路总也走不到头。我看着手腕上的日历表,已经走了一小时,一天,一个星期了……可脚下还是这条路。甚至后来我不管到哪里,都做这同样一个梦。
我惊醒过来,喝了三次水,撒了两次尿,最后向朋友挂了个长途电话,本想问问他在牌桌上把那个曹癞子打“跪”没有,出口却成了打听自学成才考试的事。
朋友称我为“黄治先”。
“什么?”
“什么的什么?”
“你叫我什么?”
“你不是黄治先吗?”
“你是叫我黄治先吗?”
“我不是叫你黄治先吗?”
我愕然了,脑子里空空的。是的,我在旅社里,过道里蚊虫扑绕的昏灯,有一排临时床。就在我话筒之下,还有个呼呼打鼾的胖大脑袋。可是——世界上还有个叫黄治先的?而这个黄治先就是我么?
我累了,永远也走不出那个巨大的我了。妈妈!
(选自《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