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必说今人语
2008-08-23刘恩平
刘恩平
开放的戏曲本体
对于京剧以及戏曲的变革观,梅兰芳当年曾以一语名之——“移步不换形”。然而笔者认为,梅兰芳的戏曲改良仍着眼于表演上的技术创新——“步”是新程式,“形”是旧程式,是在延续技术传统基础上的技术“发明”。换言之,戏曲的“本体”并没有动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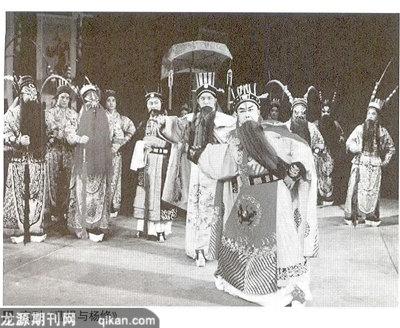
究竟什么才是戏曲的“本体”呢?仅仅是那些技术层面的要素吗?
无数连篇累牍的学术著作都在重复王国维的一句经典:“戏曲者,以歌舞演故事也。”再延续下去,无非就是齐如山所说“无声不歌,无动不舞”。他们强调的都是戏曲表演形式上的表现技巧和审美呈现。
不过,任何技术层面的发展必然关乎观念的变革。反过来说,不触及观念变革的技术行为,是不具有真正的发展意义的。观念的变革才是推动发展的核心动力。以蒸汽机发明为引擎的工业革命,开创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和保障人权自由的体系模式;以计算机发明为标志的信息革命,展现的是全球化浪潮的格局图景——后者才是“本体”所在,前者只是“技术”而已。
好比工业革命在奔往现代化之路上埋伏着着经济危机,信息革命在世界趋同之势中也加剧了强弱的对比,作为观念上的本体自身也会有着先天的弊端和局限,这就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加以矫正。同样,作为审美艺术样式、文明组成单元之一的戏曲,也须在改革创新中求发展,赢得新的生存空间。既然如此,戏曲的本体就不是一个“自给自足”、“自我完善”的闭合系统。“歌舞演故事”中的技术,固然可贵,却难掩其肌理显而易见的残缺,它们共同构成了戏曲的“善恶交织”的本体。仅仅强调技术层面的沿袭和改良,并不能疗治本体质里使其新生。
笔者以为,在戏曲本体中,以“剧诗”为体裁、以“留神”为机趣的文学意象精神,以虚拟化、程式化、音乐化为代表特征的“写意”演剧形态应予以承继光大,至于其他方面,可以改造之处甚多。只见“歌舞”是一叶障目,因噎废食则与自杀无异。
互补的戏剧体系
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中,“主题思想”是一出戏想要表达的理念,“最高任务”则是创作这出戏的艺术家通过它想要追求的一个带有整体性文化思考的追求。前者是一个具有逻辑性的理性范畴,后者则包含着艺术家的情感化意志色彩,比较而言,后者更具整体和超越的意识。
在中国的艺术家,尤其是戏曲艺术家中,这个“最高任务”很少具有整体性和超越性的创造观念。如甬剧《典妻》的主题思想,是表现一个被侮辱、受损害的底层女性的悲惨遭遇,细腻多姿地刻画了其于冰冷黑暗的人生境遇中不可泯灭的温暖情怀,从而呼唤人的平等和人性的尊严。但它绝不仅限于此,《典妻》的实验价值在于倡导“传统戏曲的现代化”、“地方戏曲的都市化”,从而实现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在现代审美心理上的对接。这才是《典妻》升华而出的最高任务。进一步来说,以这“二化”为双轨,承启的是通往“古老戏曲青春化”的“高速列车”——尽管它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改造梦想的色彩——而这,恰恰就是我所以为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戏曲运动”(我也杜撰一个说法)的最高任务。

“最高任务”是斯氏演剧体系的核心要义之一,比中国传统中的“文以载道”要深刻得多。我们一阵子追学斯氏体系,一阵子又全部鄙夷。其实,我们和斯氏体系的真髓之间的距离仍然很远,而且在“东张西望”中迷失方向。我们既要守住本体的艺术自觉,又不能陷入狭隘的“本位主义”的囚笼。
现实的历史观念
我以为,传统戏曲本体中,“哲理化”、“人文精神”、“新思潮”是普遍缺失的。《西厢记》中崔莺莺“自荐枕席”,《牡丹亭》中杜丽娘“梦情而死”,《桃花扇》中的“扇底兴亡”,这些优秀作品无不具有当时所稀有的叛逆思潮、深刻哲思和人文精神。在当下走向数字景象的现代、后现代时期,我们的戏曲创作视界没有理由不更畅达,胸襟没有理由不更雄健,思想没有理由不更敏锐。如果有学者担心因此会导致戏剧情节淡化、新编戏失去历史感等,那就未免低估了当代观众的智商和情商。黄梅戏《徽州女人》情节是淡化的,但它的诗画意蕴拓宽并提升了黄梅戏的艺术品格。《典妻》的情节性也不强,而更像一出西式心理剧,可它的婉约唯美却激起了观众审美的内心风暴。我以为,这两出戏庶几可视为一种“画剧”与“心理剧”的佳作。京剧《曹操与杨修》、淮剧《金龙与蜉蝣》的创作,剧作家若是没有古希腊悲剧直到莎士比亚戏剧的人文积淀,就不可能有这样振聋发聩的喷发。至于昆剧《一片桃花红》,直接宣泄了人自身的形式美对道德美的逆向胜利,她传达的完全是当代青年“靓男美女”的情爱心声。——这种健康、民主、明快的情绪张扬,从哪里可以找到知音呢?《荷马史诗》中敌对双方为争夺“美神”海伦而兴起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而均无悔怨;《埃及艳后》中无论是失败者恺撒、安东尼还是战胜者屋大维,在克莱奥·帕特拉的绝世之美下都成了臣服者,他们全部都是值得骄赞的英雄。我们看到,在《一片桃花红》中,以美骄人的换成了男性——齐王。这就剥去了中国传统教化中伪善的纯道德评判外衣,直指美的自然本性,由此全剧获得了自觉、自醒般的惊奇与共鸣。显然,对于那些坐在所谓“历史感”太师椅上的人,这些“新戏曲”是不会被理解、更不会被喜欢的。
对于反对“让历史人物说今人的话,做今人的事”的意见,我却以为,从来的优秀作品都是“让历史人物说今人的话,做今人的事”。戏里的真实远比历史的真实重要得多。
倘若历史的原貌是“本体”的“真实”,那就应该去读历史教科书。倘若不能“忘本”是条“铁律”,那么人类自己都可以搬到动物园去,跟猴子们长相厮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剧”都是现代戏。不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戏剧无论是在观念与形态、技巧与载体、传承与革新上的理解和实践都将是无本之木、无帆之舟。这在当前各种“申遗”的一窝蜂、非理性的文化投机生态下,尤其值得令人警醒。
创新的艺术手法
戏曲借鉴包括话剧在内的其他艺术门类,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绝大多数戏曲剧种都是从民间歌舞及说唱中诞生的,就像歌舞里孕育了音乐剧,音乐剧里孕育音乐话剧,芭蕾中诞生了现代舞,照像术中诞生了电影。话剧中也频频使用戏曲的故事情节和表现方法。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总是一代瞧不起下一代,尤其对新生事物持本能的贬视态度。如唐诗在先,则贬宋词为“诗余”,再贬元曲为“词余”。而后世至今视作文学“霸主”的叙事型体裁,被当初国人贬为“小说”,不登“大雅”。这种“瞧不起”的本质,不是虚矫的自傲、自欺,就是虚伪的自卑、自卫,惟独没有坦荡的自信和乐观的自强。
笔墨当随时代。很多人口头说改革,但在实践中就全忘却了。曲牌体曾何其正宗,却被板腔体后来居上;计划经济三十年何尝不是规律,而被市场经济三十年取而代之。变革是硬道理,规律是软道理。规律是可以再造的法则,而非压箱底的紧箍咒。规律是一个冒号,而非句号,更不是用来唬人的图腾符号。百姓有饭吃是真,人们有戏看也是真——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于丹在《百家讲坛》新说《论语》,赢得了众多青年的喜爱,原因在于她主要抓住了“乐道”二字,作了紧扣时代脉搏的衍生。也就是说,“快乐的道理”原来这么经典,又这么亲切、这么简单。于丹阐发的是在当代拥挤的生存环境和逼仄的生活节奏中,人要如何看待和把握生命的宽容、悟性和关爱——这就是快乐的源泉。这就跳脱了“四书五经”式的“微言大义”和“圣王之道”的沉重负荷,轻盈置换为今世人心容易接受的“微言俗义”和“自在之道”。这没什么不好,这种新潮的通俗化应该被肯定。当然,如果有人非要认定朱熹老夫子那套解释才是“本体”所在,倒也悉听尊便,谁也别拦着。
“一言堂”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学术、文化,皆乃天下公器——这也是老古话了。
我以为,新戏曲的演进和新戏剧形态的诞生,尚远未至于以“本体”去对峙、对抗“客体”门类艺术的境地。在现代品格的人文精神、人物形象的新颖丰富、叙事结构的灵活多姿、演出风貌的严谨完整、剧种样式的探索营建、欣赏心理的时代节奏等诸方面,都须要强力地向古今中外各种艺术汲取养料、取长补短,开发出新的气象。
一代有一代之盛衰,一代有一代之消长。与其抱残守缺,坐视观众的流失,不如八仙过海。一来有创造新的剧种样式和演剧形态的机会,二来有培育新的观众群落的可能。站在“大戏剧观”的泰山之巅,遥想孔子当年情怀,我们对戏剧在多元传媒时代的发展、蜕变与新生,应该有着乐观、平和的期许和进取、创造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