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求正大,不务新奇
2008-05-30阳敏
阳 敏

青年人的信
《南风窗》:你和王先生交往多年了?
吴洪森:我第一次上门拜见王先生是1983年1月底放寒假的时候,至今已经25年了。
《南风窗》:能讲一下结识的经过吗?
吴洪森:1980年我在九江师专中文系读三年级的时候,写了一篇文学评论,评法国古典名著《红与黑》,花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1980年底完稿,之后先后投寄多家刊物都被退稿。1982年6月再次接到退稿,一气之下就寄给了王先生。那时我已经从九江师专毕业,在新办的九江九中任高中语文教师快一年了。
《南风窗》:怎么想到寄给他呢?
吴洪森:1978年底中国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美学、文学理论都很活跃,有个名叫王元化的人,写的文章我每次读到都非常敬佩。王先生的文章思想深刻文字精炼。有家报纸发表他文章的时候曾经介绍作者工作单位是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我就按这地址寄去了,里面还附了一封很情绪化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王元化先生:您好!
寄上三投不中的稿子。此稿为扫荡教条主义评论文风而作,望先生能拨冗指教。
敬祝大安!
吴洪森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
《南风窗》:你也够狂的。
吴洪森:那时年轻不懂事,比较狂妄。就是现在,我还是缺乏谦虚谨慎的品德。我这方面缺点比较严重。
《南风窗》:王先生给你回信了?
吴洪森:回了。
《南风窗》:回来怎么说的?
吴洪森:我看到回信的时候已经8月底了。王先生那时候已经不在上海社科院,平反解放后调到大百科全书工作。社科院文学所收到信后,派人送到了大百科。王先生因病去黄山疗养,未能及时看到我的信。到放暑假,还没接到王先生回复,心想人家大人物未必会理会我,可能忙得没时间看我稿子。我就回上海过暑假了。过完暑假回到九江九中,门房说有我的信,我拿到手一看,信封上回信地址是上海古北路650号大百科王元化,心里很激动,总算有回音了!拆开信,只见王先生写着:
洪森同志:
六月十日来信并附稿,最近才看到。原因是我于六月六日遵医嘱去黄山疗养院
(近来身体很坏),前天因得上海长途电话有工作上的安排,始提早还沪(原定八月中回来)。因此复信较迟,你一定等急了,请谅!
我读了大作,感到十分欣慰:因为我觉得你的文章很好,被埋没是不公正的。因此我想介绍到刊物上发表。大作自然也有略嫌不足之处,即对于连最后时刻,也即他显示了心灵最纯洁的时刻,你写是写了,但较前面少了一些。我觉得你的细致深入的分析能力是极可贵的,希望你多写点文章出来。
我已年逾花甲,年老体衰病多,但成天打杂(搞行政),只能挤点时间写些东西。终日碌碌,成就有限。作家受冷遇,处于孤独,也有好处,可砥砺自己,进行深思。匆此
祝好!
王元化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
《南风窗》:你看了一定很感动吧?
吴洪森:是的。很感动很激动。先生在信里不但鼓励我安慰我,还鞭策我不要害怕受冷遇,要砥砺自己。当时我的处境很糟糕。我毕业分配所去的九江九中,前身是九江火柴厂子弟小学,只有几间低矮的破平房,新教学大楼还没盖起来,我去的时候,学校都无法安排我睡觉的地方,办公室里的乒乓球桌成了我睡觉的床。一头放着我的箱子,就是我的全部家当。直到我离开这所学校,还是连睡觉的床都没有。只是从乒乓球桌换到了一块黑板上。乒乓球桌太硬了,睡得腰背疼,用板凳架起来的黑板有点弹性,就不再腰背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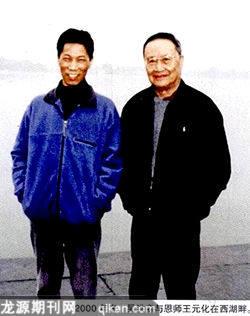
那种处境之下,前途渺茫,心理压抑,收到先生的信,心里激动可想而知,对我的鼓舞,难以言表。从回信日期来看,先生7月18日回到上海,20号就回信给我了。先生这样认真对待一个远方陌生青年的文稿和来信,这种为人做事的风格挺让我感动的。
师专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得知这消息都很为我高兴。我还写信把好消息报告毕业后回到都昌家乡教书的摩罗和修水的丁伯刚,他们得知这消息也很高兴。我想王先生的信不仅鼓励了我,也鼓励了他们。九江师专那么个破学校,当年我们刚入校读书的时候,学校连图书馆都没有,出了摩罗和丁伯刚,和先生的鼓舞是有关系的。
《南风窗》:和他们也有关系?
吴洪森:当然有关系啦。一是精神和心理上的作用,相信只要自己努力一定会受到公正对待;其次,我得到了先生提携后,认识了文坛一些名人和报刊编辑,我再推荐摩罗和丁伯刚的作品,这样,对他们来说就不存在被埋没的问题,只是能不能写出好作品的问题了。你想想,一个小年青,知道自己只要写出有价值的东西来,就不愁发表,和对前程毫无把握,这种心理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南风窗》:这倒是的。还是继续讲你和王先生的故事吧。
吴洪森:我回信向先生表示感谢,告诉他我刚从上海过完暑假回来,回九江前,在上海书店里看到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就买了^当时船票紧张,没能买到四等仓,买了五等大统仓的票,天气炎热,在船上读这本书,居然忘记了炎热和周围的嘈杂。这书写得太好了,当时很希望先生保重身体多出大作。
两个月后,先生又来信告诉我《上海文学》将发表我的文章,信的内容如下:
洪森同志:
上月去京开会,本月中旬返沪。回来后诸事待理,因此复信较迟,乞谅。
上次寄我的大作已转此间《上海文学》,他们决定发表(可能十期或十一期)。我请编辑部和你直接联系,不知你们通过信否?我认为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希常写些东西,不知除对外国文学作品分析外,还写其他性质文章(如理论、美学)否?我相信你从事写作是有前途的。
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基本上写于六十年代文革前,你读后请直率提出批评意见。年内我有本文学评论选(由冯牧同志主编)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行,可能即将出版。
你鼓励我多写点东西,很感谢,但我已年逾花甲,体弱,而目前又在岗位上打杂,所以是心有余力不足。许多拙文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挤出的。
我不知你在上海,否则可约一时间谈谈。下次有机会来沪,事先告我。匆匆不尽。
祝好
王元化
九月三十日
三件印象深刻的事
《南风窗》:这样你就去拜访王先生了?
吴洪森:是的。放寒假我到上海就去拜访王先生了。我是晚饭后给先生家里打电话约拜访时间,先生说你要是方便,现在就可以过来我们聊聊。这样我就去了先生家。按先生家门铃的时候,心里既激动又忐忑不安。自己实在没学问,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位大学者,很紧张。
《南风窗》:第一次见面先生和你聊了什么,还记得吗?
吴洪森:先生先问了我在九江九中教书的情况,然后就问我最近看了什么书。我
一一作了回答。记得我回答自己最近读的书时提到了庄子,先生随口就背诵了一段,然后问我是怎么理解的。我回答后,先生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提醒我读庄子的时候要注意的几个方面,说读书切不可贪多求快,一定要逐字逐句搞懂搞深搞透。
第一次见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情,一件是先生建议我读陈寅恪和熊十力的书。这两人的名字我从没有听说过。
《南风窗》:你那时就因为王先生知道陈寅恪和熊十力了,那好早啊。
吴洪森:是的。陈寅恪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才走红,熊十力到现在,影响力大概还只是在中国哲学界和新儒家范围内。和先生来往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他指点下读书,少走很多弯路。读了一点陈寅恪,我懂得了不要轻易相信和接受对历史的现成结论;读熊十力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解决了唯心唯物的问题,心和物是不能两分的。这些对清除以前被灌输到头脑里的错误观念帮助极大。
去年先生多次叮嘱我读的书,一本是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还有一本是陈澧的《东塾读书记》。我在书店没找到这两本书,我不习惯到图书馆借书读,钱文忠有《无邪堂答问》送我一本,我读了,只读了一遍,先生说一遍不行,还得多读两遍。这本书里面朱一新说“学问但求正大,不务新奇”给我印象很深。后面一本书还没找来,先生已经过世了。

《南风窗》:你刚才说两件事情印象很深,还有一件是什么?
吴洪森:还有一件是先生问我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有些什么打算,我说对想象问题很感兴趣,想钻研一下这个问题。这个想法获得了先生的肯定。先生说想象问题确实值得研究,国内在这方面还缺少深入研究。说完先生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他翻译的刚出版不久的《文学风格论》,签名题赠给我,说供我参考。
《南风窗》:想象问题你后来研究了吗?
吴洪森:1985年我考上了华师大文艺理论研究生,师从张德林先生,才有足够的时间来集中学习和思考这个问题。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想象问题的,题目叫《存在与想象》,3万字,当时在华师大主办的《文艺理论研究》发了一个9000字的纲要,12年后《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偶然看到这文章,才得以全文发表并获得了评论奖。这点小小的成果,起因就是第一次见王先生。
现在回想起来,第一次见先生,印象深的应该有三件事情。
《南风窗》:第三件是什么?
吴洪森:临别的时候,先生给我写了三封介绍信,把我引见给上海作协李子云老师、复旦大学蒋孔阳先生和华东师大徐中玉先生。先生叮嘱我去之前先打电话联系。我手持先生介绍信一一拜会了这几位文坛名人,在聆听他们教诲过程中,我很强烈感觉到他们对先生很敬重,这敬重不仅仅是因为先生的学问,更包含对先生为人和人格的敬重,我这才知道先生原来是大人物。我至今仍很清楚记得,按照约定时间到作协拜访李子云老师和周介人老师的时候,李老师见到我就说,我们已经在等你了,想看看元化介绍来的青年是怎样的。我听了真是受宠若惊。
提携后学
《南风窗》:文坛大门从此为你敞开了?
吴洪森是的。经先生推荐的那篇评《红与黑》的文章《形象的爱情理学》1983年5月发表后,因为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解读文学作品,当时还比较少见,引起评论界一定的注意,以前是写文章数投不中,现在有报刊杂志向我约稿了。不过我写得少,投稿更少。
《南风窗》:为什么?
吴洪森:我第一次见先生的时候,先生就告诫我,多读多思考,不要轻易下笔。我知道先生对文字要求很严格,怕被他骂,不敢随便写,除非你不想再和他来往。和先生交往,稿费上要吃亏,呵呵。尤其对自己没弄懂的问题乱加发挥,他会严厉批评的。有一次我去他那里,他正在写字桌上看一篇报纸上的文章,他说洪森,你先坐,等我把这文章看完。看完后,他坐到藤椅上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人我看是完了,根本不懂的问题也胡说一气。之前先生已经当面和他讲过两次了,叫他下笔慎重不要乱写。他不听劝告,先生只好叹气了。
《南风窗》:先生既提携青年,又要求严格。
吴洪森:是的。和先生来往多了,渐渐知道得到先生帮助的人很多,我相信,把类似故事收集起来,可以编成一本书。钱文忠也是在先生帮助下于1995年重新回归大学的,在这之前,他在社会上游荡了5年。
我再举个例子,先生去世前一星期,5月2日,中国美术大学教授范景中和太太一起来看望先生,当时先生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时睡时醒的。趁他醒来的时候,蓝云在先生耳边大声告诉他,范景中来看你了。先生病危后耳聋得厉害,不大声喊听不见。见先生没反应,蓝云又大声说范景中来看你,你是不是不认识了。先生很费力的嘟囔了一句:“你以为我糊涂啦。”大家都笑了起来。然后听见先生对范景中说:“我知道你的时候,不知道你人在哪里,到处托人打听你。”
周围人不明白先生讲的是什么,正好我了解这件事,就解释给大家听。那是8年前的事了,先生在杂志上看到范景中的文章,说这人厉害,有学术水平,翻译也好。问我是否知道,我说不知道。当时我刚从香港回上海定居,国内刊物已经多年不看了。后来先生打听到了,在美术大学舒传溪教授引见下,范景中教授来上海和先生认识了。我交代了这背景后,在座的都很动容。
学风之重
《南风窗》:王先生给你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什么?
吴洪森:我难以回答,哪些属于印象最深,这要留待时间来告诉我,尤其在这样的时刻。昨天有记者问我类似问题,我张口结舌、无从谈起,我就说你提问题吧,让我笼统地谈,我不知道从哪里谈起。事后我想到先生这么多年来经常反复强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学风问题,还有就是风骨、志气问题。2000年底先生80周岁过后送给我的字写的就是:
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传统。每逢危难关头,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敢冒天下不韪,迎着压力打击去伸张正义,为真理而呼喊。这些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肯降志辱身的人,堪称中国的脊梁。
先生晚年经常提到胡适的话,“不降志、不辱身、不避危险、不曲学阿世”,说这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座右铭。
市场经济掀起物质主义狂潮,名利金钱地位不但为官场所膜拜,知识分子也被席卷而去,这个国家已经找不到精神堡垒了。先生对这现象非常忧心。他多次书写这幅字,我想是很有针对性的,他希望还有人能坚守精神的、思想的阵地。
《南风窗》:学风问题先生说了些什么?
吴洪森:1997年底,我从香港艺术发展局得到一笔拨款办《香港书评》,请先生题写刊名还请先生撰稿支持。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多年来,他对我总是有求必应)。他写的文章就是介绍熊十力关于学风和如何读书的见解。我第一次见先生的时候,他
谈到读书,也引用过熊十力的两句话:“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根底无移其固,裁断必出于己。”我请先生为《香港书评》撰稿的时候,先生那时正在苦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薄薄一本书,先生反复读了几遍,上面划了密密麻麻的杠杠,不但写眉批,还写读书笔记。不但读中文本,还把英文本找来对照,英文本对照后,心里还是不踏实,又从上海外国语大学请来法语教授请教。先生那时已经79岁了,读这本书的起因是吴江来信和他讨论卢梭的国家学说,先生足足花了半年多时间,他才觉得有把握来回复吴江的质疑。6个月的心血,写成的文字不到2万。
《南风窗》:老先生看书真是认真。
吴洪森:我以前把先生强调学风只是看作要我们认真刻苦读书。后来才慢慢理解了,学风问题不只是学术能否健康深入发展的问题,更是培养人才训练人才的问题。没有好的学风,这个国家就没了认真踏实做事的人,没有认真踏实做事的人,无论文化创新还是经济创新,都是沙上建塔,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学风、学术的根本问题就是人才人品的问题。一个国家学风浮靡,假大空,学术上不可能有成果,学术没成果,智商智慧人格都出不来。
举个例子,前一阵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责骂文科,说搞清楚曹雪芹是三十晚上死的还是年初一死的有什么意义?我忍不住责问他,一个人要是有本事搞清楚几百年前的曹雪芹到底是死于三十晚还是年初一,有这种本事的人去破案,什么案子破不了?这种人如果当大官,手底下哪个蒙得了他?他的方法如果普及开来,全民智商将提高多少?没有认真钻研精神,思想独立,精神自由根本就是空话,头脑成了别人灌输给你的死水池,哪里还有什么思想独立,精神自由可言?
陈寅恪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北宋时期达到了顶峰?陈寅恪的解释就是因为思想独立,精神自由,学术发达,人才辈出。因此,学风直接关系到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问题,思想独立、精神自由又关系到学术问题和人才问题,最后就关系到文化能否发达,国家能否真正兴旺的大问题。这些问题是互相连贯在一起的。遗憾的是我很晚才有这种认识。
“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传统。每逢危难关头,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敢冒天下不韪,迎着压力打击去伸张正义,为真理而呼喊。这些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肯降志辱身的人,堪称中国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