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思者
2008-05-30张汝伦
张汝伦
一个人的离去:悼王元化先生
策划人语
上海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王元化病逝于上海瑞金医院。他和2003年过世的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一样都是死于肺病,和1998年辞世的钱钟书先生一样都是死于88岁高龄。从此,无论思想界的“南王北李”,还是文艺理论界的“北钱南王”,皆成绝响,而上海文化圈自巴金、施蛰存、贾植芳、王元化去世后,几乎塌了一大半。
王元化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他30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50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至1981年平反昭雪后,曾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后转任华东师大教授。著有《向着真实》、《文学沉思录》、《文心雕龙创作论》、《清园夜读》、《读莎士比亚》和《思辨录》等。
王早年对思想界的影响表现在反思“五四”,反省卢梭“公意”论,告别黑格尔,以及对顾准的推崇等方面。相比同辈一些杰出的学人,他的这些贡献在当时的环境下,因其兼具官方身份,因而颇具分量。至于后来他与李慎之等人关系的变化,具体情形局外人难以深知。
他晚年经常提到胡适的话,“不降志、不辱身、不避危险、不曲学阿世”。他认为,这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座右铭。
——刘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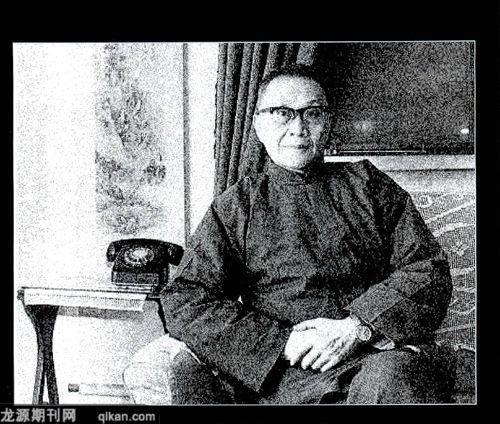
5月9日,王元化先生离开了他一直热爱和思考的这个世界,离我们而去。
我初识先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一复旦友人带我去他淮海路的寓所见他。我向来对结识名人没有很大兴趣,只是碍于友人的好意而勉强成行。结果在整个过程中我实际只是一个陪客,主要是元化先生与该友人在交谈,我和他或者他和我说过什么完全记不得了,很可能只是初见面者会说的一些客套和寒暄吧。元化先生显然把我们的这次初识完全忘了,后来从未提起。
90年代中期以后,我与元化先生的往来渐多。交往愈多,愈是被他的道德文章折服,不由得庆幸自己能在这个平庸的时代,认识这样一位不平凡的思者。他的嶙峋风骨和独立思想,使他不可能被庸众追捧,但他的自由精神与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必将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启蒙之真精神
在我的心目中,元化先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的确,他的家世、经历、天赋、才情、学问、治学方法乃至个性,都有不同寻常处,但对于当代中国思想史来说,这些不同寻常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他的不同寻常在于,他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为数不多的真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
王元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甚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说法,都会被意识形态化。一个人的成败毁誉,往往取决于他的意识形态立场。与众不同者默默向隅,暴得大名者引领潮流,成了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常见现象。人们有意无意依附某种意识形态,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和道德优越,全然忘了真理是需要通过艰苦的探索和批判,尤其是对自己种种成见的怀疑和无情批判得来,以至于批判和真理成了我们时代非常罕见的现象。元化先生却与时流迥异。
元化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思想写作。虽然他是从文艺理论人手,但却并非纯粹为了理论或学术,而是为了“激起读者的思想,引起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头脑中出现许多从未想过的问题,并渴望去解决它们”。这绝非一般文艺理论家的追求,而是一个思想家的追求。元化先生和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对启蒙情有独钟。早在1938年就写过《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80年代末又重新提倡新启蒙。
在现代中国,提倡启蒙者不绝如缕,但大都是以先觉觉后觉的姿态,以为自己真理在握,将自己盲目认同的意识形态作为绝对真理教条地向人宣示。“启蒙”一词来自西方,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和殿军康德对它有一个经典的定义,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王元化是提倡启蒙者中不多的几个真懂启蒙精神者。在《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中,他指出:“新启蒙运动所以提出理性的口号,实是它必须抑制无谓的感情冲动,反对任何笼统的幻想。”半个世纪后,在他主编的《新启蒙》第一辑的编后语中,他又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他未必读过康德论启蒙的文章,但却得启蒙精神的真传。
这与德国古典哲学对他的熏陶是分不开的。他在晚年写的《自述》中说:“我深深服膺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17、18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我很大的影响。”启蒙实际不是向别人灌输自以为是的教条或偏见,而恰恰是无情地反思自己思想的种种偏见与盲点。元化先生就是如此,他不仅毕生工作贯穿了这种批判精神,尤其在晚年自觉地“以它去清理由惰性和习惯所形成的偏见和谬误”。
三次自我反思的思想史意义
王元化一生有过三次自我反思,其实是自我批判的经历(他自己对反思的定义是“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讨”)。第一次是在1940年前后,反思批判自己盲目接受的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第二次反思发生在因胡风案隔离审查期间,这次反思主要是反省和批判自己习惯的知性的片面的思维方式。第三次反思则发生在他的晚年,这次反思批判了他“长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观念,这些既定观念已被我当作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这些“既定观念”其实就是他长期以来秉持的意识形态立场。

这三次自我批判一次比一次艰巨,一次比一次深刻,也一次比一次关系重大。第一次反思只限于批判自己耳食得来的文艺理论,虽然要真正克服并不容易做到,但也不至于伤筋动骨,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也就将其彻底抛弃了。第二次反思就要难得多。人是思维的动物,要批判自己习惯了的思维方式,不啻改变自己走路的样式,很少有人做得到。但这才是启蒙批判精神的精髓所在。经过这次自我批判,元化的思想达到了当时一般人很少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也使他有足够的思维能力进行第三次自我批判。
尽管如此,第三次自我批判仍然是最为艰难的。一个人要改变自己长期以来秉持的立场,出于真心而不是出于趋附和盲从,尤其在晚年,没有丰沛的精神活力和强健的思维力量,是极难做到的。此时的元化,已经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威望,他完全可以像许多人那样,摆出大师或泰斗的架势,刻意营造自己的权威形象,而不是揭露自己长期秉持的错误立场。更有甚者,这一次他所自我批判的立场,与前两次的自我批判对象不同,是海内外相当一部分人中流行的“主流话语”,一旦触及,反弹可想而知。然而,
元化先生却全然不顾这些,“出于一种忧患意识,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对过去的信念加以反省,以寻求真知。”这使他在晚年真正超越了过去的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自我反思的思想史意义,会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
从表面上看,王元化的反思是自我反思,但更深入地看,未尝不可说他的反思也是对其所处时代的反思。王元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激进的”时代,尤其是他的前半生,整个世界的大气候偏左。哪怕是从日本人那里传来的苏俄的理论,也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几近于真理的化身。破除对这些理论的迷信,不仅是元化个人的事,也是时代对独立的思想者提出的任务。元化第二次反思所批判的那种思维方式,一直到现在还支配许多人的心灵,片面的知性思维方式和感性-理性简单二分的时代至今还没有结束。但元化先生却在半个世纪前对这个时代的思想病理进行了剖析,并坚决予以摒弃。
他第三次反思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这足以说明他的这次反思绝非只关个人,而恰恰是击中了时代的命门。五四以来的这个时代的思想状况,可以用以西学为神圣,以洋人为帝天来概括。这种思想状况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激进主义。而意图伦理、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论等,则与这种激进主义相表里。这些恰恰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病症。如果说王元化的前两次反思是由于个人经历的原因的话,那么第三次反思则显然更多是由于时代使然,是时代的事件使他进行了比前两次更为深刻也更为广阔的反思。这次反思不仅是在反思自己过去的观念,更是在反思这个自由思想瘫痪的时代。
王元化一生最可贵的品格,就是走自己的路,任凭别人去说,更不在意令人不齿的明枪暗箭。他的三次自我反思真正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断然拒绝人们将他与别的什么人相提并论的说法,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见解。不管是洋人的思想还是古人的思想,他总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批判思考,决不随声附和。这一点难能可贵。

检点现代中国思想史,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弄潮儿们不仅纷纷自觉朝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靠,而且还将各种思想也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甚至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可以用作意识形态的T具。而某些被人树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标兵,只不过是拾人牙慧的应声虫而已。思想意识形态化后,必然持有势不两立的斗争心态。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激进主义,就是保守主义;不是自由主义,就是新左派;不是全盘西化,就是重建儒教……总之,没有第三种可能。
针对这种含有明显专制暴力因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王元化推崇熊十力提倡的“孤往”或“孤冷”精神,也就是先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他揭示说:“唯新唯洋是从的风气与40年来教条主义的感染不无关系。教条主义与趋新猎奇之风看起来相反,实则相成。两者皆依傍权威,援经典以自重,而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沿习既久,惰性已成,个性日丧,创造力终于斫伤净尽。殆无权威依傍时,则不能创一说立一论,沉迷于中,而不知自省。”这是出不了大师和独立思想家的根本原因。自由思想必出于孤往精神,而不是出于趋附。
思想与学术的交融
元化先生的为学与他的思想一样,从不画地为牢,以专业自雄;而是不拘一格,一任自由思想的引导。虽然元化先生在清华园中长大,晚年也在一所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但他实非学院中人,他的学术工作几乎都是在学院外进行的。也因此,他的学术工作没有学院学术工业常见的毛病——将学术与思想相对立;学科壁垒分明;见树不见林、过于专业化;因袭有余,创新不足;以及术语堆砌却毫无自己的思想,等等。
今天的人们大都会把元化先生定位为一个学者,但我觉得他可能更愿意是一个思者,一个时代的思者。但是,在他那里,思想与学术并不矛盾,相反却体现了它们原本应有的统一。晚年他针对一些人将思想与学术截然分开的做法,明确提出“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看法。他明确指出:“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深化思想。不可想象,没有以学术作为内容的思想,将成为怎样一种思想,而没有思想的学术,这种学术又有什么价值?思想和学术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他自己所有的学术工作,都体现了思想与学术的统一,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一般学术工业产品无法具有的丰富和深刻。
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观点与他从一开始就不完全认同时下流行的、源自近代西方的学科分类有关。人们往往根据他的成名作《文心雕龙创作论》而将王元化归为文艺理论家。可他在该书第二版跋中说得很清楚,他是以文史哲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文心雕龙》的,因为“我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后来分为独立的学科,这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可说是一大进步,但是今天我们这里往往由于分工过细,使各个有关学科彼此隔绝开来,形成完全孤立的状态,从而和国外强调各种边缘科学的跨界研究的趋势恰成对照。我认为,这种在科研方法上的保守状态是使我们的文艺理论在各方面都陷于停滞、难以有所突破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任何文艺思潮都有它的哲学基础。美学作为哲学一个分支,就说明两者关系的密切……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逐渐使我认识到在研究上把文史哲结合起来的必要。”
实际上王元化的学术工作也的确打破了现代学科分科壁垒,横跨文史哲诸多领域。元化先生从未自认为是哲学家,人们也不把他看作是哲学家,但他却对哲学极为重视,在中西哲学上都下过苦功,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对他影响极大。毋庸讳言,由于时代的原因和其他原因,他对黑格尔哲学的阅读和理解都是有局限、因而不免有些片面。但因为他不是把黑格尔哲学作为知识对象来研究,而是作为思想养料来吸收,所以他的阅读即便是片面的,也有片面的深刻。他对黑格尔的一些思想的理解和解释未必正确,但却深得其神髓,这是许多专业哲学研究者都做不到的。他对中国哲学和佛教哲学也下过苦功,论述虽不多,但多有可观。
由于有哲学的底子,王元化的多数著作,都有着哲学或思想的品格,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是要阐发文学的规律性,实际上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完全可以被视为是思想史的研究。在他的《文心雕龙》研究中,他讨论了魏晋儒学与玄学的关系、佛教思想对刘勰的前者影响、意言之辨、心物关系、才性问题等等重要的哲学问题和思想史问题。钱钟书曾说他是用思想史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史,那么王元化则是用思想史和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文艺理论。这使得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在“龙学”研究中独树一帜,不同凡响。
由于非学院中人,所以元化先生的学
术成果,尤其是后期,很少用学院派惯用的方式,即所谓理论专著的形式来表达,而是喜欢用中国传统学人常用的笔记、札记、问答、谈话的方式来表达。钱钟书的著作《谈艺录》和《管锥编》也是笔记、札记体。这种方式在今天的学院派看来,也许上不了台面,但却有其优点,那就是不受学科分类拘束,更无学术八股,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三言两语间,精义立见。元化先生晚年的代表作《思辨录》,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传统表达方式的优点。它使得作者可以打破现代学术分科壁垒,随心所欲遨游于思想天地之间,有感而发,不落空言。读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有选择地阅读,而无任何阅读负担。
任何研究王元化思想的人,都应该首选《思辨录》来阅读,从这部至今还未得到人们足够重视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思想深度、学问规模、人格旨趣、知识教养,乃至性情个性。在此意义上,说《思辨录》是王元化最重要的著作应不为过。该书根据内容分为从甲到壬共九辑,其中戊辑、己辑、庚辑分上中下三部分,所以实际一共十五部分。其中甲辑论述作者的反思和文化思想;乙辑为对“五四”的反思;丙辑论卢梭和韩非;丁辑论述晚清政坛;戊辑都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己辑上中两部论中西哲学,下部是附篇——文史小考;庚辑是美学文艺学;辛辑是作家论;壬辑谈戏剧及文化杂谈。从以上《思辨录》各辑的主题就可看到,此书跨度有多大,内容何等丰富,在中国现代学术著作中,可说是绝无仅有。
但《思辨录》的作者并不想向读者炫耀他有多么渊博,如何学富五车。相反,他倒是一再对读者说他读书不多。这当然是指与前贤相比;但可能更是认同记诵之学,不足以为师的古训。他更渴望让读者知道的不是客观的知识,而是他的思考。即便是有些篇目看上去像是掌故轶闻,或训诂考证,也往往不是纯粹的辑佚或考证,而是要阐明他对某个问题的思考,与那些纯粹堆积材料的笔记体著作不可同日而语。例如,丁辑第七十八篇“沈荩之死”并非纯粹叙述沈荩死事,而是通过叙述沈荩乃死于慈禧“破律乱法”而点出此前“清朝的司法对于皇帝也还是有独立性的”,即便皇帝想杀某个人,往往因为不合律法而不能得逞。这就以事实破除了中国没有法律制度,皇帝想杀谁就能杀谁的说法。又如庚辑第二五五篇“释‘道与‘德”,通过对“道”“德”二字的训释,阐明老子哲学对刘勰《原道篇》的影响。
与当代其他的笔记体著作相比,《思辨录》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它紧扣时代的问题,它讨论的问题几乎全是与这个时代有关的问题。尽管学院派会对此不以为然,甚至以“非学术”相讥,但后代研究者将会把它看作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文献和学术成果之一。
无疑,王元化首先是个时代的思者,他智慧的眼光始终盯着时代的精神状况,不停地思考它,质问它。他无私地向读者贡献他独特的思考与质疑,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只要王元化思考的问题仍然存在,他的思考就不会过时。不同的人们对他的不同看法,恰恰证明了他的思考触及了时代的神经。
王元化曾经是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但在三次反思之后,他成了一个孔子和苏格拉底式的怀疑论者,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是绝对正确的,他特别警惕那些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必不容对手有反驳之余地的思想专制主义者。元化之学术思想,或有可商,他的此种怀疑主义,却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之最终保障。
无疑,王元化首先是个时代的思者,他智慧的眼光始终盯着时代的精神状况,不停地思考它,质问它。他无私地向读者贡献他独特的思考与质疑,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只要王元化思考的问题仍然存在,他的思考就不会过时。不同的人们对他的不同看法,恰恰证明了他的思考触及了时代的神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