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左岸
2008-05-14康慨
康 慨
2006年,我途经巴黎,在喝醉之前,透过雨幕南望对岸,只见灯光昏黄,充满未知。我虽手握地图,仍决定中止凌晨的冒险。与其说我没有时间,不如说错过了时间。青年时代的梦想一去难还。我宁愿停在右岸,整夜享受资本主义的醇酒,默念阿波利奈尔的诗句:“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塞纳河将巴黎一分为二,南部的拉丁区,即“左岸”,因为大学和文化机构林立,聚集大量知识分子,形成了独特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以及高谈阔论、硝烟弥漫的文化氛围。赫伯特·洛特曼记载了左岸人强烈的自我承认:“右岸是没有脑子的中产阶级的领地,智者的生活不可以跨过塞纳河。”
写于1982年的《左岸》一书,截取了法国文化史上政治色彩最为浓烈的阶段之一(能与之比肩者大概要数1968年),即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左翼政党合组的人民阵线上台,经历战时沦陷,直至冷战开始,时长大约二十年。这一时期,苏联的影响力极大地渗透进了法国作家们中间,大批头牌作家,如纪德、阿拉贡、艾吕雅、马尔罗,以及名气更大的萨特,均受到苏联感召,成为红色左岸的明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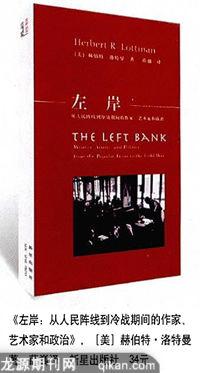
1935年6月,在巴黎的国际作家大会保卫文化会议上,纪德做总结性发言,称:“苏联的安全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我们对苏联的信心是我们爱它的明证。”5年前,63岁的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要用我的生命来确保苏联的成功,我会马上献出生命。”
然而,对苏联的爱并不总是一以贯之。在受邀对苏联进行访问,并得到极高规格的接待之后,纪德出版了“讲真话”的《访苏归来》一书,批评苏联的思想控制,以及个人崇拜的登峰造极和无处不在。“是他变了,还是苏联变了?”洛特曼写道,“无论是哪种情况,对他来说,人性都比苏联更重要。”纪德随即由苏联的座上宾变成了进步事业的叛徒,遭到大规模口诛笔伐。红左岸日渐风雨飘摇,此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终将其红色一层层褪去。
像曾经以巴黎为精神家园的那些美国作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格特鲁德·斯坦因)一样,洛特曼也长居在此,写有多部关于法国的文化史著,最有名的是《加缪传》。同样,和那些美国人一样,他也对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争论天然地置身事外,其热情仅止于旁观。
德雷福斯事件以降的法国知识分子,议政甚至亲身付诸街头行动者大有人在,使“左岸”与政治始终纠缠不清。政治化的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过深地卷入政治,对社会,或是对文化而言,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早在1927年,朱利安·班达——另一位法国人——便曾指出,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政治激情今天达到了普遍性、连贯性、同质性、精确性、连续性和目空一切的程度。”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他写道:“所有的政治激情都备有意识形态的工具,它们以科学的名义宣布自己行为的最高价值和历史必然性。”政治激情高涨至此,也便走向自由的反面,被政治俘虏,而不是驱动政治走向更好。班达慨叹理性、静态和超越世俗的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正像阿波利奈尔站在蜜腊波桥上,怀念一去不返的爱情。
两年前的那个雨夜,我挥一挥眉毛,作别了巴黎的左岸。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