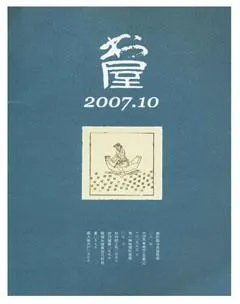《日本真相》(选载之二)
2007-12-29高宗武
书屋 2007年10期
高宗武 著 夏侯叙五 整理 注释
我记得我第一次所办的对日具体交涉,比较重要的是对满洲伪国通邮交涉。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封锁对“满洲国”的通信事务,塘沽协定后,中日双方谅解在停战相当期间内,中日两国应开始商谈关于对“满洲国”的交通通信事件。当时黄郛任华北五省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可以说是完全对付日本人的。日本在那时候虽然刚拿到东北四省,但第二步就要圈定他在华北的势力范围,所以中国政府在华北设立一个大规模的地方机关应付它。那时华北地方事件的外交本来大部分由华北当局就地办理,当然以黄郛为中心,无奈黄氏所经办的通车事件,被国民攻击得体无完肤,因为中国人民十分反对政府当时的抚慰政策,黄郛个人因此也很受攻击。所以这第二件即与“满洲国”通邮事,黄郛不肯再经手办理,请中央派员主持。中央以为过去的关内外通车事件办得不甚圆满,政府为此受到舆论攻击,所以这一次也有意由中央派人负责办理比较妥当一点,这是他们几位要人在庐山会议时决定的。
有一天下午大约四点钟的样子,我有一位朋友郭心崧君〔1〕来看我,他说:“他们在庐山会议决定,通邮的问题是不能再拖下去了,大家的意思,要请你去主持。这本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但国家的事总要有人去干的,大家以为你最相适应,所以今天特来征求你的同意,切莫推辞。”我当时对日本的事情虽然相当注意,但对于实际上的与日本交涉,可谓是一年级的学生,一点经验也没有,关于邮政的事务,更是一点也不懂,同时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我若去干,或者因此送命,也未可知,所以十分犹豫,请他另请高明。郭说:“这是他们在庐山会议秘密决定的,你若不愿意的话,你最好向他们去说。至于邮政事务不懂,并不成问题,邮政局的事务人员你尽可调用好了。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要你去办技术事务的。”我答应考虑几天再回答他。后来我和许多朋友及前辈商量,大家都主张我去干,他们说吃力的事也必须去尝试一下。我接受了朋友们的意见。
因为当时有一部分舆论的反对,所以这次交涉不能不在秘密中进行。我记得我于1934年9月24日由南京秘密赴北平,当时我和邮局内一位邮务长余君〔2〕以及几位随员同去的。政府给我的训令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避免有承认满洲伪国的嫌疑,换言之,在不承认“满洲国”的原则之下,与“满洲国”进行通邮交涉。说起来,这是有点滑稽,一方面说我不承认你,一方面又派人来和你商量通信,只从这两点上看,这篇文章就不是好作的。在法律上不承认他,在实际上又派人和他商量通信的办法,这总是有点不好办。我在接受命令的时候,倒没有什么,以为总可相机应付,后来一路在火车上静思默考,总觉得有点想不通,难以自处,因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然而命令已经领受了,事体非办不可,政府有政府的方针,当局有他的苦心,我呢,也有我的牺牲精神。所以火车一到北平,我就不管理论通不通,只求在事实上做得通和事体的整个解决。
到了北平之后,首先去看望华北五省政委会黄委员长。他本来是和我相熟的,我很直率的告诉他,我此来人地生疏,同时于对日交涉毫无经验,和日本谈判,即使是有经验的人也要上当,请多加帮助和指导。他答道:只要是办得到的事,一定帮助。对我表示十分的好感和殷勤。
这通邮问题本来可以说是很小的一件事,因为邮政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大问题,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来看,又可以说是很要紧的一件事,因为一旦处置不当,小则事体本身不得解决,大则可影响到整个政府,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政府的抚慰政策不谅解,非常反对。我临行时,当时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氏再三再四地吩咐我,有事要直接向他请示,关于邮政技术问题,可向交通部和邮政总局商量。日本方面呢?真正负责的是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仪我(GiGa)大佐,驻北平副武官柴山中佐,另外是“满洲国”的邮政司长日本人藤原三人。“满洲国”本来是中国之一部,因为日本军事上的占领,成立了一个傀儡国——“满洲国”,“满洲国”人就是中国人,这通邮实际上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内部的事,但为要避免承认“满洲国”起见,中国人自己避不见面,而偏要和日本人谈判,用法律和事实一比较,又想不通,然而世界上想不通的事太多,我想不通也没办法。
记得第一次和日方代表见面,是在殷同〔3〕家中。殷同是北宁路局局长,黄郛身边最重要最红的红人。当时中国方面我是主任代表,余翔麟为副代表,殷同、李择一〔4〕为参与人。日本方面藤原为首席代表,仪我、柴山为参与人(但实权在仪我和柴山手中)。由殷同介绍我和日方代表相见后,日方就拿出他们预备好的许多“通航方案”和“通电方案”、“通邮方案”,一起当面交给我。我拿来一看,都是写着“满洲帝国”和中华民国什么什么方案,与殷同事前告诉我的大不相符,于是我就开始说:“本人此次是为办通邮而来的,所以除了本题之外,关于通航问题、通电问题,并非本人职权之内,本人无权讨论,所以关于通邮以外的方案,请带回去。关于通邮问题,我们在讨论之前,要决定两种原则:一、在不承认满洲国的原则之下,商讨邮政上之技术问题,不作任何有关政治之商讨;二、双方倘意见一致,最后结论不签字,不调印,以备忘录方式彼此备案。”这两项原则,是完全为执行避免承认满洲伪国的政府训令而设的,当然是安全之策。但日本方面十分反对,他们说,我们此来并没有要求你们承认“满洲国”的意见,但你们一定要写明白在不承认“满洲国”的原则之下等字样,倒不好办,这是日本所不能忍耐的,日本不愿在这种原则之下和中国办通邮。关于双方不签字,则将来如何对证,彼此也不会有约束力。若是中国坚持非此不可,这通邮问题倒是不必谈判好,因为是无法谈下去的。日本所谓通信是指邮电合并而言,日本的电报局和邮政局是不分的,这是你们知道的,通邮而不通电报,在日本方面是解释不通的,所以电报的问题务必一起讨论。至于通航问题,若贵代表不在职权之内,可以另作计议。
第一天的商讨可以说不但毫无结果,而且马上发生僵局。但是双方的态度尚温和。后来继续商讨了几天,因为双方意见不一致,亦毫无结论。而黄郛先生已十分焦急起来,请我回南京去请示,同时要日方代表也返回关东军所在地请示比较缓和的方案;我则要求日方代表务必先答应我所提的先决条件,我方可回去请示,不然即是回到南京也无用处。后来经过了几次折冲,日方代表竟答应了。
我回到南京向汪行政院长和朱〔5〕交通部长报告,他们均十分满意。这时他们给我的训令是:勿怕决裂。我在南京住了一星期,政府的训令使我态度更加坚定。
回到北平后,始知日方代表早已由奉天到北平。会议重开,不料双方代表均声称:此番回去请训的结果和没有请示以前并无任何不同,不过当时基本原则已经决定,所剩下来的是技术问题,所以比较的尚算好对付一点。
关于技术的急点,最难解决的在邮票本身。中国方面以中国厌恶满洲伪国,不愿意看见邮票上有“满洲国”等字样,要求“满洲国”制造一种特殊邮票,作为与关内通信之用,这一点可谓是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日方认为不能让步,中国方面认为非争不可。此外,中方主张在山海关设立邮电转递局,以商用性质来代替中国邮局直接与“满洲国”邮局来往。但日方坚持直接通邮。双方争论达两个月之久,而仍无结论。
这一次交涉,大概是日本人认为最头痛的交涉。中途,黄郛、殷同二人希望我多让一点步,以期早日结束。当时我不肯让步,我并不是说黄郛不爱国,他是非常爱国的,不过只是我的看法和他有点不同,所以彼此之间时有冲突。代表北平舆论的各大报记者都和我很好,我什么事都告诉他们,他们一点也没有把我的消息透露出去,而且大家都无条件的作我的顾问。当时华北当局对日不敢说“NO”字,我这样的坚决,他们非常痛快。
日本人每次与中国交涉,他们的交涉配角,一定是一个人凶一点,一个人缓和一点,这次也是这样,柴山做好人,仪我做凶人,后来弄得装好人的柴山也变凶了,他们总是变法地向我威胁,说这通邮交涉若不及时解决,关东军将认为由中央派来的代表毫无诚意。事态不论如何演变,日本军人一副可憎面目,天天在我眼中。我则坚持日本若要用兵,那就根本不必与我谈,既与我谈,则不能引谈判以外的话来吓我。
在决裂了的第三天,我准备回南京去,日方派人来说,大家可以再试谈一、二次,以期尽我们做代表的能事。这是他们的要求,我当然接受,因为我并非高调者。后来他们终于让步,黄郛说是他与殷同从中周旋的,所以日方才肯如此迁就。
未料第四天晚上,我们在北京饭店开会,日方代表完全变更其前缓和的口调,作出一副可怕的样子,对我说:我们谈判至今已两个月,所以今天的会议只有Yes或No,用不着再讨论,再讨论一百年也无用。说毕请我答复。我用很温和的口调解释我方的立场后,答说“No”字,彼此遂起立握手而别,表示谈判完全决裂。
我们出来之后,黄郛派人来要我马上到他那儿去,说交涉决裂了,万一中日关系变坏了,谁负责任?!他责备我少年气盛。我告诉他,你不必担心,他们会设法挽回的,而且这个问题马上解决了,中日问题也不会马上就好;这个问题弄坏了,也不会坏到什么地方。
当时黄郛先生急得没有办法,适逢蒋委员长来北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一天早上,他由医院打电话找我去。我赶到医院将交涉经过向他报告了一番,他并没有其他的表示。事后有人告诉我,蒋委员长找你去,是黄郛先生的请求,黄先生的意思,大概是以为我不听他的话,所以请委员长来教训我。后来我在蒋委员长出了医院之后又去见他一次,委员长也并没有什么吩咐〔6〕,所以当时有人说黄氏的内交失败了。
有一天,仪我大佐打电话到我所住的北京饭店来,他说有重要的话要和我单独谈。我当然不能拒绝他来见,所以就说请他马上来。在我挂了电话不到一刻钟他就来了。他说这次不是办外交来的,是他个人作私人拜访来的。他说他十分愿意和我作长久的朋友,倘是我愿意的话。他说我对日本办外交态度很强,十分爱国,这是日本军人最佩服的地方。我表面上也当然说,我愿意和他作长期的朋友,但心中明白他此来必另有用意,因为日本人一举一动皆不落空的。他接着说,我们现在既然是好朋友,所以一切事不能不关心,不然他就不说了。他说关东军对我的坚持不让的态度,一方面固表示敬意,但是另一方面却十分不满;表示敬意是日本军人的精神,表示不满是日本的政策,因此我今后的处境不但很困难,而且很危险。他说关东军的计划,就是他也不能完全知道,例如关东军从前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计划,他虽身任张作霖的顾问,而且当天也是和张作霖同车回奉天的,也完全不知道,幸而他坐的位置和张氏相隔颇远,所以得免于死,否则今天不能和我见面了。所以通邮决裂后关东军的计划,他虽完全不知道,同时也无法知道,但是关东军不会没有第二步计划的,请我特别留心。明天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Yolhijirs umetvn)中将由天津来北平,明天晚上在日本大使馆请我吃饭,也有重要的话和我谈,请我务必出席,态度非常诚恳。说完话他马上就走了。第二天,梅津果然来北平,我应他之请而赴宴。梅津饭后告诉我说,关于通邮的问题,希望大家早点互相让步,不然把才好转过来的中日空气又变坏了,岂不可惜!他再三地说,他一定会帮我的忙,请我不必过分操心,在他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期内,保险华北没有问题。他的态度十分亲切而客气。我知道他们前后的找我,是要我让步,他们大概也研究过我的性格,知道我什么都不怕,也什么都不要,所以用这一次最有力的最后一次友谊的劝诱,以期达成他们的目的。因为在那里,日本不愿意再用兵,同时也不肯让步,他们拿梅津司令来和我说好话,以为我总可以就范的。但结果还是按照我们的几条备忘录式的双方不签字的谅解事项,遂于12月初在北京饭店成立,记得那天我们一直弄到天亮才回来。
第二天上午十时,我们去看黄郛氏,他带着极不愉快的调子说,这些日本人的变化没法办,我们昨天通邮问题刚解决,今天早晨七时仪我、柴山两人又来说,现在通邮问题已解决,非常之好,剩下来的通电通航问题,请从速开始谈判,务期于今年年内解决,以解除世人之怀疑。他们这样的一刻都不放松,如何得了。我告诉他我们在天亮才回来,那是冬天,最少也当在早晨六时半,大概仪我、柴山两人和我们握别之后就没回家,便直接到黄郛那边去提第二次的要求,这是日本军人一贯的作风,他不怕麻烦,也不怕难为情,更不顾人家的私生活如何,他只求达到他的目的,手段是他们所不择的。
这是我第一次和日本军人交涉所得的深刻印象。柴山是日本军人中算是最温和和最进步的人,柴山如此,其他的人更可想而知了。
注释:
〔1〕郭心崧,字仲岳,浙江温州人,为高宗武同乡好友。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教育部司长、交通部参事等职。时任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
〔2〕余君,即余翔麟,为此次谈判中方副代表。
〔3〕殷同,字桐生。北平沦陷后从逆,任伪华北临时政务委员兼建设总署督办。
〔4〕李择一,名宣韩,早年留学日本。时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沪宁沦陷后投敌,参与组织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活动。
〔5〕朱交通部长,即朱家骅。
〔6〕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宗武给同乡挚友郭俊禾一信,透露蒋与高谈话一节,高信中说:“当时交涉方针,皆由汪直接授弟,黄因弟不肯受他指挥,屡表不满,竟背后向日方表示,由他接受日方条件如何,日方代表则谓渠非此案代表,无权接受日方条件。时适蒋到协和医院治牙疾,黄即说动蒋找弟去,由蒋吩咐弟受黄指挥。当时弟深感黄之压力不在日人之下,乃告蒋云,黄即如此勇于负责,当初何以要求中央派人来主办此事,他自己办了算了。今日之事我只能将尊意电汪,汪若同意,我方能办,因我受汪之命而来也。蒋认为十分合理。第二天汪复电坚持原案,不容变更,并云蒋处由他负责去电说明,请勿为念。弟以汪电示蒋,蒋亦不再作主张。……此皆五十二年前之事也。”显然,高宗武在其手稿中“为尊者讳”,而隐去了此段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