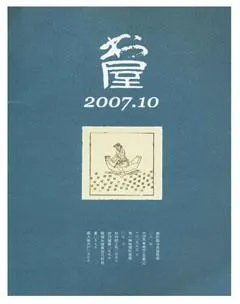高教收费政策不宜大动
2007-12-29裴毅然
书屋 2007年10期
一、选择的艰难
较长时间以来,社会各界对高校扩招和收费政策颇多微词,可谓众说纷纭,反对之声不绝于耳。现在,已到评估这项公共政策的时候了。
首先,我并不同意“教育产业化”(以商业经营为价值指导)的总体定位,不同意将公益性很强的教育办成惟利是求的商业性操作模式。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国情:人多底薄经济太差、教育整体水平太弱,资金缺口巨大。“希望工程”历时二十年,所募助教善款仅二十亿(只够修三公里地铁)。因此,中国教育的发展只能筑基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没有经济的实质支撑,仅靠道德的呼喊,无论如何是空洞乏力的。
要求政府拿出办教育的所有经费,视教育为慈善,这一思路仍走在“万能政府”的老路上,以为政府能够解决一切,能够包办一切。教育确实不能产业化,但也无法慈善化,尤其高等教育,不可能再搞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包办制。实事求是地说,接受高等教育毕竟是个人追求发展的一种需要。在普遍贫弱的现实国情下,要求完全由政府或社会承担高等教育费用,是不现实的。而且,政府或社会从哪来钱?当然,政府应该削减政费军费、削减基建投资、增大教育投入。这些年,政府投入较低确为事实,2005年教育总支出不足四千亿,仅占GDP总额百分之二点一六,低于2004年百分之二点七九与2002年的百分之三点四一。世界各国均值百分之五点二,高收入国家在百分之五点五以上,低收入国家平均也达百分之三点六,中国人均财政教育经费仅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倒数第八位〔1〕。但是,政府再加大投入、再怎么从其他地方挪补也是有限度的,较之教育经费之大缺口,也是一下子填不满的,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即现实国情。
就是中小学初级教育,1990年代的十年间,全国对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和各种“教育集资”,最保守的估计也在一千五百亿元。没了这一笔钱,连中小学教育都撑不下来的。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说:“2006年以前,我们的义务教育没有成为公共财政保障的教育,财政只保障一半,有一半要靠社会筹措。”〔2〕
就是相对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各地政府仍无力承担教育所需全部资金,托举不起这只大盘。相对富裕省、县能够保证辖境内九年义务制教育所需经费,已经阿弥陀佛了。吃饭生存、发展经济、医疗保健、教育投资……谁都重要,谁都要钱,谁都得带着拽着,款额又只有这一点,蛋糕本身就小,不考虑现实平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必须承认,任何选择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掣肘,任何稍有偏重的选择都会遭到其他方面的谴责,都会听到“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各种诉求,而不同时期有所偏重又是无法避免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我国用于教育的公共开支尚不足世界教育开支总量的百分之三。再据1990年代末统计,我国各类在校生为二亿八千三百一十六万,约占世界受教育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2006年3月3日,教育部长周济在人大会议期间记者招待会上说:解决了百分之九十五学龄人口的义务教育。必须承认:我们是在以极其微弱的财力承办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其中艰难可想而知。研究者指出:“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有效地使用公共教育开支,同时必须鼓励增加私人和社会的教育投资。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所有的教育和受教育人口大包大揽。”而且根据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率,小学教育为百分之二十七,初高中为百分之十六,大学为百分之十三,因此“作为人口众多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必须全额资助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大学教育理应增加私人投资。”〔2〕再以小学与高校3f2f40ae99a42d8ad52ee26f52675941a1e9fd57f67246b6e7d344a272f1f8fb生均经费投入来看,1998年小学生人均经费三百七十点七九元,高校生人均经费则为六千七百七十五点一九元,相差十八点三倍。此前差距还要大〔3〕。再说大学生,上海财大生人均经费一万五千元/年,北大生人均经费两万五千元/年,学生所缴纳每年五千元学费,只是负担了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5〕。显然,以国家目前财力,实在无法包办高等教育。按目前执行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在现阶段,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五”,正规院校(尤其重点高校)大致控制在这一比例之内。
还有一则资料。清华、上海交大、浙大,1991年总经费仅为一至一点五亿元,而同期美国康乃尔大学六点八六亿美元,麻省理工十四点零二亿美元,伯克利加州大学七点七亿美元。世界一流大学的经费是我国名牌大学的六十倍之巨。仅仅一所麻省理工所拥有的经费就是我国1991年三十六所委属高校总经费的六倍〔6〕。
据最新资料,目前全国教育部属七十二所院校总负债三百六十亿元,平均每所部属院校负债五亿。之所以欠债如此之高,原因即在于高校招生规模急遽扩大,从十年前招生不足百万发展到目前五百万/年。全国大学也从十年前的一千所左右发展到今天的两千所〔7〕。
众所周知,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没有一点负面效应,尤其在“没钱也要办事”(或钱少也要办事)的中国,任何政策选择都是十分艰难的。关键在于利弊相权之下的理性权重与科学把握,在于各种因素之间尽可能的精准调配。优先发展高教的思路,既因较之中教小教,高教总盘子最小,所需资金绝对数最少,更为关键的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导向。如果教育界龙头老大高校教师的收入持平于中小学教员,那么知识的优越性便无从体现,社会成员自觉追求知识化就会失去现实激励。毕竟,高校教师所需知识积累量要大大超出中小学教师。
二、高教收费的可行性
2006年3月4日,北大张维迎教授在某一内部研讨会上说:“我过去讲过一句话,也是挨骂最多一句——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什么意思?世行研究,欧洲也研究,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都是补贴,但不是补给穷人。我们如果规定学费多少用于穷人助学金,这一问题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不要按计划经济统一的标准,就像病人,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看一个医生,这样是走不通的。”张维迎的意思是用高收费之策进行贫富调节,使学校补贴真正的贫困生,而不是通过降低学费这一普惠制使非贫困生均沾利益,致使学校失去补助贫困生的能力。降低学费,学校失去财政能力,不仅无助于救助贫困生,而且教学质量必然下降——优秀师资外流。
据统计,全国高校生均学费1989年为两百元左右,1995年八百元左右,近年四千至五千元左右,十八年间确实上涨了二十至二十五倍〔8〕。同期职工工资从两百元以下涨至二千至三千元左右,当然职级、行业、地区之间的差距很大,但十八年间全国职工收入增幅至少在十五倍左右,农民平均收入达不到十五倍。从这一角度,学费涨幅高于收入涨幅,存在相对的不合理性。但这一倾斜性收费政策,即通过高中、高校收费,引导国民收入汇聚教育,从整体上支持教育发展,真正体现了教育优先的发展思路。
中国高校为什么不能合理吸纳社会资金?为什么不能执行“谁得益谁支付”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如果以慈善性代替价值规律,便会打破目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价值理念与现实平衡,便会重见那一系列熟悉之至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旧弊旧症。至于城乡贫困家庭子弟无力缴纳学费,则可通过各种补助性质的“绿色通道”予以解决,总不能在收费政策比照“缺口效应”——以最低收入者为基准。因为少数贫困家庭无力纳费,便从整体上否定收费政策或指责收费过高,实际上是破坏整体平衡,否定“教育优先”。所谓“优先”,其实质就在于必须保证经费优先。
以上海高校为例(上海生活费用较高,贫困划定标准高于全国平均线),家庭收入人均每月四百元以下为贫困生,三百元以下为特困生。上海各高校贫困生(包括特困生)约占全体在校生的百分之二十,上海财经大学近年为百分之十三,其中百分之五左右为特困生,这里面必然有一部分“虚贫生”(故意装穷者,学校不可能彻底一一核实)。可见,贫困生总体比例并不高,远未达到需要考虑停收高校学费的地步。如果为了这些贫困生,改变收费这一大政策,那么中国高校财政不是断了一条重要输血管,一条能够得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大学生家庭支持的输血管?有数据表明,近年全国高校经费来自国家财政投入已不足百分之五十〔9〕。某高校计财处长说:“如果严格按《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收取学费,学校就得关门。”〔10〕
必须承认,确有下岗工人或贫困农民因凑不齐子女的高校学费,走了极端跳了楼;也有中西部一些贫困县农民十年不吃不喝供不起一名大学生。但这些个别案例并不能证明高校收费的残酷性,并不能撼动收费政策的整体合理性。就像有人忍受不了竞争压力而自杀,难道就能从整体上推翻竞争体制么?别忘了,仅仅依靠道德是无法推动社会这架大转轮的。
中国之大,各地发展之不平衡,任何一项全局性政策都需要一定的补缺,但局部的补缺并不等于整体的全部推翻。适当运用市场机制,尽量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兴教办学,再以其他补救性政策遏制负效应,应该说是相对合理的政策。目前高校对贫困生采取“绿色通道”——先入学后商量解决费用(减免学费、贷学金、助学金、奖学金等等),即“奖贷助补减”五种救助性措施,没钱也能上大学。据报道,2006年国家助学贷款已资助二百四十点三万贫困生读大学,2005年有三十九万贫困新生通过“绿色通道”未交学费直接入学〔11〕。陕西省累计八万五千名贫困生得到国家助学贷款五亿九千万元;其中四点五万贫困生所得三点一亿贷款,得自2004年6月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以后〔12〕。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贷学金政策执行六年来,除京沪等大城市毕业生还贷率较高(因收入较高),中西部地区还贷率极低,河南全省至2005年只有一名毕业的贫困生还清贷款〔13〕。全国有百分之二十的借贷生逾期未还〔14〕。2006年9月,陕西省教育厅下发通知,要求加强对贷款学生的诚信教育,对违约一年以上不还贷的学生将在媒体及网站公布其姓名与相关信息〔15〕。就是上海,2006年9月,农业银行将九十六名助学贷款不还者告上杨浦区法院,这些已毕业的贫困生如今每月仅需还款一百六十一元,仍然一躲了事。农业银行此类欠款纠纷达三四千件〔16〕。不消说,所有未归还的贷学金还是国家与高校共同买单,高校每年须向教育部协贷中心缴纳本校贫困贷学金总额的百分之四点一为风险金,国家财政部也向该中心缴纳百分之四点一风险金,共同作为银行“坏贷”的赔偿金,等于国家与高校为贫困生的高等教育作出“实际支付”。2001年国家财政高校特困生各类资金总额近七千万(含助学贷款)〔17〕。教育部2006年3月8日发布消息,迄今共发放贷学金一百七十二点七亿元,资助了一万八千二百零六名贫困生〔18〕。由于“坏贷”总额远远高于风险金,银行已有拒绝发放贷学金的动议,并要求对还贷还制定强制性措施。
就是欧美各国,教育投资也是家庭最主要的开支项目。如笔者姨妹夫妇(均为美国博士),家庭年收入十余万美元,也承担不起孩子入学哈佛、普林斯顿等收费很高的名校,只能让孩子进入居住地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因为该州子弟仅收学费五千美元/年。
三、高教扩招的必要性
现在以大学生就业困难反对高校扩招论调不时泛起。实际上,所谓大学生就业难也只是相对于京津沪穗深等高收入城市职岗,若放眼全国,挺进中西部,进入中等城市或再深入县乡镇,就业需求可是“大大的”。再以实际数据来看,2004年底,当年大学生就业率达百分之八十四,全国仅四十五万多毕业生未于毕业后立即找到工作〔19〕。这一“未就业率”显然不足以说明扩招过度。而且,“毕业即失业”乃普遍现实,哪个国家都不可能使本国大学毕业生百分之百充分就业,更不用说“满意就业”了。如果大学毕业生一出现就业难,即以削减招生数相平衡,是一种能够选择的政策么?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的残酷:一定程度存在的失业率,乃是促进人们珍惜工作机会的最大动力。
一头是国家经济发展需要高素质人才与社会进化需要成员素质提高,呼唤高校扩招;一头是国民希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高自身竞争力、提升生活质量。可见,高校扩招乃是上下两头都呼唤都支持的现实需求,于国有益,于民有利。就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也不仅仅是社会成员单向的享权,民主也对社会成员提出相应的文化要求。仅凭就业相对困难即否定扩招,是不是太片面了?至于将高校扩招归之“延缓就业压力”、“扩大内需”、“以教敛财”,亦均似是而非,责之失当。“延缓就业压力”原本无错,难道不需要延缓吗?扩招既延缓压力,又提高青年文化素质,难道不对吗不好吗?“扩大内需”、“以教敛财”(就算是),引导国民向他们愿意且正确的方向投资,错了吗?
据美国学者罗伯特·福格尔(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芝加哥工商管理学院教授)1990年代末调研:中国人均实际收入与美国相差约一百年,但中学教育已达到1970年代水平,而当时美国人的人均收入为中国当时水平的十倍〔20〕。可见,以我们目前相对落后的人均收入支撑当前的中高等教育,确实体现了“教育优先”的发展思路。
不过,高校扩招确实也带来一系列问题,需要慎重对待,如学生人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从十四点四平米降至十一点八平米,生均教学仪器值从六千四百零九元降至六千二百零九元,生均藏书从一百一十七册降至六十一册〔21〕。高校债务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有的大学已经亏损运行,连债务利息都无力偿还〔22〕。研究者已经提醒若继续扩大高校规模,国家经济实力将难以支撑,呼吁我国高教发展重心应从增量转向增质。但这些较之扩招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显为次要方面的负效应,可通过适当调节加以解决。如果因了这些次要方面的负效应,否定扩招的整体积极效应,实属以偏概全,极为失当。再说,任何发展身后都不可能没有一点最初的阴影,只要还在可纠可补的范围内,就不应该因了这块阴影否定已经迈出的脚步。
就中国教育现状来说,虽然问题很多,需要不断修正改进与加大投入,但基本政策还是对路的,或者说相对合于实际国情。至少,高校收费政策目前不宜大动。
注释:
〔1〕〔5〕载《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3月8日第8版“两会特刊”。
〔2〕载《南方周末》2006年10月12日A3版。
〔3〕载《内部参阅》1999年第4期((总第447期)。
〔4〕载《内部参阅》2002年第21期(总616期),2002年6月7日,第66页。
〔6〕林樟杰:《论新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76页。
〔7〕〔8〕载《解放日报》2007年3月11日第3版。
〔9〕载《社会科学报》2006年3月9日第3版。
〔10〕《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12月31日第3版“新闻观察”。
〔11〕载《半月谈》2006年第8期。
〔12〕〔15〕载《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9月4日第2版“国内新闻”。
〔13〕载2005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
〔14〕〔18〕据央视12套法治频道“中国法治报道”栏目报道,2006年3月10日12:00-12:30。
〔16〕载2006年10月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17〕载《内部参阅》2003年第4期(总第648期)。
〔19〕〔21〕载《社会科学报》2005年12月8日第5版。
〔20〕载《内部参阅》1999年第42期(总485期)。
〔22〕载2005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