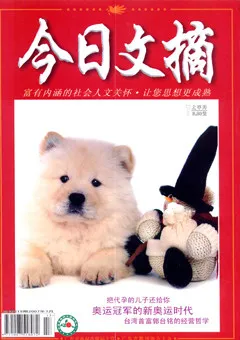大将许光达和他的娃娃亲
2007-12-29杜导正廖盖隆
今日文摘 2007年13期
“救命”的婚姻
许光达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1年,许光达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先生邹希鲁特别喜爱他好学上进,想要他做女婿。1922年,邹希鲁正式托媒人来到许家,为9岁的女儿邹靖华提亲。
邹希鲁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开明之士,本知包办婚姻之苦,却为何急于为小女觅婆家呢?说来有一段隐情。
邹家是一穷困不堪的大家族,四十多口人生活在一起,家里种一些薄田,邹希鲁当教书匠赚的几个钱,除衣食之费,所剩尚不能奉养父母。叔父逼邹希鲁卖掉二女儿桃妹子(邹靖华)和正在吃奶的小女儿杏妹子。邹妻悲痛欲绝,半夜含泪自尽。邹希鲁把小女儿托付给已出嫁的长女,还要把二女儿嫁出去求生。
许光达的父亲十分同情邹家的不幸,为了救人一命,同意了这门亲事。父亲征求许光达意见,许光达说:“邹先生是我的恩师,不能见死不救。长大了,只要她乐意,我愿意同她结婚;如果到时她不愿意,我也一定尊重她的愿意,绝不强求!”
爱的规范
1927年9月,许光达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一带,在三河坝受阻。他当时担任连长,英勇拼杀、冲锋在前,不幸被炮弹击中,负了重伤。
许光达被安置在附近村里一家农户秘密养伤。主人姓孙,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叫翠花,是赤卫队员。
孙家对许光达很疼爱,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翠花更是殷勤备至。她除了煎汤熬药,还常常让许光达讲革命道理、战斗故事,时间久了,就愈加喜欢他。
翠花会说话的眼睛早已把心事告诉了许光达,但桃妹子的影子和她母亲自杀身死的惨事,不断出现在他脑海里。他不能做负心汉,他要对得起桃妹子和她的父母。
当翠花的母亲开口提亲的时候,许光达立刻说:“您老人家不知道,我已经定亲了,是我老师的女儿。”
翠花后来难过地说:“恨我认识你太晚了!希望你走后常常想起我,想起这个小村庄有一个叫翠花的姑娘惦着你的冷暖!”
爱浪中的沉浮
许光达身体康复了,他辗转找到了党组织。经上级批准,许光达先回湖南老家探家。
久别重逢,桃妹子已经长成大姑娘了,眼睛水灵灵的,酒窝深深的,楚楚动人。两人都特别激动,各自掏尽肺腑把情话都说出来。
这时,桃妹子的父亲邹希鲁已去清河县当县长,他曾给许家捎信,提到如果许光达回来,马上为他俩完婚。许光达的父亲也不想让儿子离家远去,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要儿子马上结婚。
但结婚刚十天,由于叛徒告密,长沙警备司令部发出了对许光达的拘捕令。为躲避敌人抓捕,许光达逃离家乡,投奔岳父。但敌人的拘捕令很快传到了清河县,岳父设法让许光达逃走。
许光达逃到北平,不但没找到党组织,反倒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竟在旅店卧床不起。
旅店老板姓隋,他有个女儿在北平女子师范读书,为人热情,思想进步。他们见许光达病重,就请医买药,给他治病。隋小姐敬重许光达,觉得他洒脱倜傥、有学问。
在隋小姐的帮助下,许光达不但养好了病,还找到了地下党员廖运周。
廖运周看到隋小姐常在许光达的身边料理各样事务,就对许光达说:“这姑娘长得好,跟你一样是师范生,对你特别好,说不定爱上你了,要不要我做大媒,两人结秦晋之好啊?”
虽是脱口而出的话语,却还是激起许光达的心潮:隋小姐有较高的文化,妩媚多情,善书爱画……然而,自己是一个已承担了丈夫义务的男人,虽是包办婚姻,但是自己乐意的;虽是出于同情和救急,但是,已经在对方身上扎下了爱根。如果生活只是为了“我”好,那么共产党员的初衷,岂不化成泡影了?
许光达于是把自己已经娶妻的事向廖运周说了,婉谢了他的美意。廖运周为他筹措了一笔钱,他告别了恩人隋家父女。
1929年3月,遵照党的安排,许光达来到无锡做地下工作。
革命征途情丝依依
许光达不知道,自他走后,他的岳父邹希鲁被革职还乡。为了谋生,桃妹子到一袜厂做工。长沙国民党特务机关查到她的落脚点,便和老板沆瀣一气逼桃妹子和丈夫离婚,说只要在报上登一个离婚启事,便不再找她的麻烦。桃妹子说:“我写不来!”老板说:“找人替你写,你抄一下就行。”桃妹子说:“我没钱登报!”老板说:“我替你出!”桃妹子将军道:“你不怕通‘匪属’犯罪吗?”
劝说无效,桃妹子被挂上“共产婆”的牌子,被罚站门。上下班时人来人往,老板指着她的鼻子叫嚣:“通共匪的,就是她这样的下场!”
1932年4月,许光达的父亲接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怪信”。信中这样写道:
德华(注:许光达的原名)兄:
安徽寿县一别,无恙?你说回家成亲,婚后即归,至今两年有余,不见音讯,是爱妻扯你后腿?还是自己激流勇退?望来信告之。
顺致
敬安
廖运周
父亲看信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廖运周”这个名字,他从未听说过。还是桃妹子心细,她从字体上看出像丈夫的笔迹。她认为,八成是丈夫怕人检查,以暗示的方法,让家里给他按信封上的地点回信。
原来,在一次恶战中,许光达的心脏附近中了一颗子弹,他被送到上海的一家医院。
面对这封投石问路的短信,家里人惊喜异常。桃妹子代表全家立刻写了回信:
运周:
来信收悉。感谢你的挂念。其实,德华自1928年秋天离家,一直未归。他如今生在何方,死在何处,望来信告知。
又及:他的妻子桃妹子现在工厂做工,苦得很,一心在等他,全家人一如往常,恕不赘述。
许光达接到这封信,多年悬在心头的忐忑之石落了地,他立刻修书一封,把在医院节省下来的200元银洋寄回家乡。
当丈夫的第二封信寄到桃妹子手中时,她激动得大哭。他的确活着,她得到他身边去照顾他。她又写了信,等待着对方的同意。
几个月过去,没有一点消息。正当桃妹子焦虑、失望的时候,许光达从苏联寄来了信。
许光达怎么到苏联去了?原来,上海的大夫正准备给他作手术的时候,叛徒告密,供出这家医院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组织上得知消息,将许光达迅速转移,然后把他送往苏联。
许光达知道妻子不懂俄文,为了寄信便当,他寄来十多张俄文写就的收信地址条,只要往信封上一贴,再贴足邮票,对方就可以收到。
十多张地址条很快用光了,由于国民党和苏联关系恶化,两国边境封锁,以后的6年当中,双方再难得到只言片纸。
原来他不是“不懂感情的木头”
1938年,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经徐特立介绍,桃妹子带着许光达的小妹许启亮,一同投奔延安。
来到延安的当晚,十分疲劳的桃妹子正欲睡觉,突然闯进一个小战士,大声喊嚷:“这儿住着邹靖华吗?”
“有!谁找我?”
“我们教育长。”
“教育长?姓什么?”
“许光达!”
一位高大魁梧的军人悄悄走进来,借着微弱的麻油灯光,邹靖华一眼看出来人正是自己多年来朝思暮想的丈夫!瞬间,两个人泪眼模糊,恍如梦境一般……
许光达的窑洞里,挤满了许多宾客,不少人是来看教育长的夫人的。因为许光达风华正茂,又是吃过洋面包、会说洋文的高干,在延安抗大正是姑娘们瞩目的对象,其中也不乏勇敢者向他求爱,但都被许光达婉言谢绝了。一些失意人非议:“他是块不懂感情的木头!”
现在,大家才知道,“木头”不是木头,原来他是心有所系,不可动摇。
此后,许光达和他的“桃妹子”邹靖华一直过着幸福美满、恩恩爱爱的婚姻生活,直到许光达离世。
(刘晴荐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