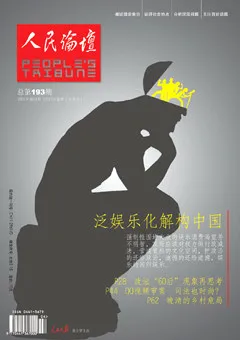泛娱乐化如何挑战公共政策
2007-12-29毛少莹
人民论坛 2007年4期
各种力量的复杂博弈,令泛娱乐化现象成为解读当代中国的绝佳视角,而传媒等公共政策的调整,则进一步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开放程度与民主进程
泛娱乐化现象引起了广泛而复杂的社会效应,不仅引起了文化批评界的广泛关注,更进一步对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构成了挑战。
毫无疑问,五花八门的各式娱乐主要依赖大众传媒来表现和传播。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各种形式的“娱乐”与大众传媒的“合谋”,就不可能有娱乐的泛化,不可能有泛娱乐化现象的生成。
正因为如此,泛娱乐化现象对公共政策的挑战,首先,也主要表现为对传媒政策的多方面挑战。限于篇幅,这里简单分析两个方面。
对传媒政策构成的两大挑战
挑战之一是关于媒体的性质、定位以及市场化问题。
我国现行的传媒体制,由于既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坚持新闻传媒作为党的“喉舌”基本定位,又要适应市场经济,我国的主要传媒(报纸、广播电视)实行的是国家兴办、政府经营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体制。这一体制使得媒体具有双重属性——既有事业单位的事业属性,也有赚钱营利的企业属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办传媒也需要通过广告收入等市场手段,不断提高媒体的产业化程度,并发展其在国际传媒产业领域的竞争力。事实上,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广泛渗透于各个领域的泛娱乐化倾向,就是通过媒体,包括权威传媒在市场利益的驱动和消费主义的引导下,迎合大众,适应市场,或者是过度市场化的一种努力或结果。因此,客观地说,泛娱乐化现象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媒体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在进一步的改革中,我们的传媒,尤其是主流传媒到底应当如何定性、定位,究竟需不需要市场化、需要什么样的市场化?市场化有没有必要的限制等?无疑都是推动传媒体制改革等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挑战之二则是指向传媒的社会责任。
进入一个高度信息化的大众传媒时代,传媒的影响力已经毋庸置疑。现代传媒在改变传统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同时,形成了任何一个别的行业难以比肩的“文化领导权”或曰“文化霸权”。正是传媒带来的庞杂而丰富的信息,极大而且迅速地影响、改变着人们关于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信仰与怀疑、崇高与卑下、生活的价值和意义、道德的准则和界限等基本信念。娱乐、游戏,固然是人性的自然要求,但是,正如调味品不能替代食物,娱乐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深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长期靠娱乐这种文化快餐或调味品长大的青少年,更不免患上精神贫血症。社会各界对泛娱乐化现象负面效应最集中、最深刻的指认和批判,正是其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冲击和解构。为娱乐而娱乐带来的浅薄的狂欢既不能给人予生存意义的解答,更无法缓解现实的痛苦,却很大程度上麻痹着人们的心灵,遮蔽了现实的苦难。而在泛娱乐化的潮流中成为时尚的搞笑、无厘头,占据主流媒体舞台、充斥核心文化空间的大量所谓笑星、丑星,刚好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混淆美丑、颠倒黑白、价值混乱的象征。那么,拥有“文化领导权”的传媒是不是也同时必须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对社会事件忠实客观的报道,对弱势群体生老病死的真诚关怀,对真、善、美等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尊重与维护等等?
公共政策调整后操作困难
我国大约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不断推进新闻传媒体制的改革探索并持续推出新的传媒政策。大体而言,包括了集团化经营、规范和完善新闻单位采编与经营业务“两分开”政策、可经营部分的企业化改制等。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政策制定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重点,其中,对包括泛娱乐化等“低俗之风”现象也提出了明确的抵制要求。
总的来看,鉴于特殊的国情,我国传媒实行的国家兴办,强调“正确舆论导向放在首位”,“巩固和发展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等媒体管制格局和政策取向都并没有随着改革而改变。此外,现行传媒政策对媒体市场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对如何真正解放媒体生产力,解放文化生产力,缺乏基本的管理架构调整和细化配套政策,导致宏大的政策目标在实际的操作落实中存在很多困难。
如何应对各种力量的复杂博弈
放眼世界,泛娱乐化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不仅是现在的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传媒管理经验,正确对待类似泛娱乐化等媒体过度市场化现象,显然是在进一步的传媒政策研究与制定中必须加以考虑的。著名荷兰传播学家库仑伯格与麦奎尔指出:“传播政策源于政府的国家利益诉求和商业/工业企业运作之间的互动,双方都期望通过特权、规定以及约束来实现各自的利益。”针对媒体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发达国家一个普遍的做法是建立公共媒体,即通过建立非营利的、非国有的、全民所有的公共媒体,独立运作,同时,通过公共法等制度,要求公共媒体在节目内容、经营目标等方面实现决策的公共性和管理的透明性。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其实也就是公民的参与性。公共媒体给我们的启示是,传媒政策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应当考虑如何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引入公民的力量,或许只有借助公民社会力量,通过建立公共的、非营利的传媒,如公共电视台等,才能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释放大众被压抑的心理与文化能量,并提供一种既不同于单纯的政治宣传、又超脱于商业利益至上的文化节目,有效地改变泛娱乐化等低俗文化现象的大面积发生。
挑战和关于挑战的应对都正在发生着,其中所体现出的管控与开放、政府主导与市场力量、雅文化与俗文化、个人文化权利与集体权利等的复杂博弈等等,都令泛娱乐化现象成为解读当代中国的绝佳视角,而传媒等公共政策的调整,则进一步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与民主进程。或许可以有一个初步的共识,即,仅有管制显然还不够,或许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积极的开放和更加宽松的环境,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生产更多更好的更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以置换、替代、占领泛娱乐节目已经占据的传媒空间和文化心理需求空间。
泛娱乐现象的生成既有市场的力量,也从某种角度表达了日益成长中的公民社会的民主化需求,简单地否定限制或完全的放任自流都是不可取的。构建民族核心价值观、重塑文化理想、加强审美教育、提高全民素质、不断推进传媒体制的改革,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媒体产业,建立公共媒体等,或许是顺应时代潮流所应采取的媒体政策走向。(作者系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文化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