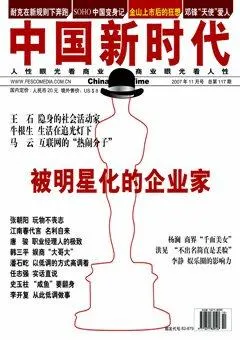邓锋“天使”爱人
2007-12-29冯嘉雪
中国新时代 2007年11期
在自家的车库中酝酿创业;从天使投资人那里获得第一笔风险投资;依靠“破坏性技术”,将行业竞争的门槛一下提高了一个数量级,令众多对手望尘莫及……邓锋拥有一个典型硅谷人的一切特质
硅谷就是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它把一个原本只将目光锁定在中关村的工科生,变成了一个敢于在硅谷冒险求生的创业者。
为了创业,邓锋不惜辞去在英特尔的工作——他放弃的不仅是一个“金饭碗”,还有英特尔一路飙升的股票——当时,邓锋已经在英特尔工作了4年多,而按照英特尔的惯例,工作满5年的员工就能获得大把股票和期权。从邓锋进入英特尔到离开时,其股价已从60多美元飞涨到了390多美元。“我在最后一年离开,等于100多万美元就这么打水漂了。”今天说起这件事,邓锋脸上依然挂着淡淡的笑容。
2001年12月11日,邓锋创办的NetScreen公司在纳斯达克挂牌。它是“9.11”事件后第一家在美国股市上市的高科技类企业。起初,邓锋和他的创业伙伴也曾犹豫,在美国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被严重打击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还应逆市而上?最终,他们的“冒险”之举博得了市场的热烈回应——所有华尔街投资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了NetScreen身上,其良好的业绩得到了投资人的认可,上市当天,NetScreen的市值就高达24亿美元。
但是,邓锋的硅谷故事还没有结束。2004年,他以40亿美元将NetScreen出售给全球第二大网络设备制造商、美国的Juniper公司。
当邓锋在NetScreen的历史使命结束时,他做出了一个全新的选择:回中国创立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北极光”。

曾经受益于天使投资人的邓锋,这次要自己做“天使”了。“我是一个比较敢冒险的人,”身为北极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的邓锋这样评价自己。
从硅谷回到中国,邓锋用了整整16年的时间。回想在硅谷的一路打拼,邓锋感叹自己到目前为止还比较运气,因为在每次冒险之后,发展得都还算顺利。
哪个创业的人不要冒风险呢?利弊权衡,会在关键时刻左右一个人的判断,邓锋也不例外:“当自己要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就需要先丢掉些东西,但不要只看这点,要往前看。不要被历史的包袱拴住,使自己不能前进,该往前走的时候就要往前走。”
被“天使”选中
1987年,邓锋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攻读硕士研究生。不过,他可不是一个只会啃书本的书呆子,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了自己的校园创业。
“那时候,这里既是我的实验室,也是我的办公室。”指着清华大学校内的一栋老房子,邓锋说,当时他领着一帮低年级师弟,在校内租赁的3间房中,承接各种项目。正当他的生意越做越火,打算毕业后在中关村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时,女友却表示,她希望实现自己多年的梦想——出国深造。
面对事业与爱情,邓锋很快做出了选择:放弃闯荡中关村的原定计划。
1990年,顺利来到美国的邓锋开始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电脑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业余时间,他也找一些咨询方面的工作打打零工。直到1993年,邓锋觅到了一份他心仪的工作——英特尔的系统架构师。他干脆向学校请长假,正式加入了这个IT精英的大本营。
不过,邓锋在英特尔并不是埋头钻研技术,做一颗“螺丝钉”。“我开始去的时候觉得是要学技术,去了之后才发现英特尔的技术并没有想象中的如何如何。”邓锋发现,英特尔的管理水平非常高,“有人说英特尔的整个团队就像以色列军队,纪律极其严明。”
初入英特尔,邓锋得到了一个比较资深的职位,负责管理一个10余人的小团队。在英特尔,每个人都是技术精英,但如何能让几百甚至上千人同时完成一个项目,这就要考验管理者的协调能力:能否恰当地调动每位工程师,让整个团队步调一致地行动。
“世界上第一个用在笔记本上的奔腾Ⅰ和奔腾Ⅱ处理器就是我们做的。”在这个过程中,邓锋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如何管理好一个团队。四年,邓锋收获颇丰。四年,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创业的火苗却在邓锋心中,从未熄灭。
当时正是90年代中期,互联网热潮刚刚兴起,身处技术前沿的邓锋意识到,网络安全将是未来影响网络应用的一个大问题。尽管当时世界上已经有30多家公司在做网络防火墙,但这些网络安全产品却普遍面临着“性能瓶颈”──加装了防火墙软件后,网络的带宽就会下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出路何在?“Cisco在路由器方面的成功告诉我们,将防火墙、VPN、网络带宽管理等功能全部集成在一个统一结构的硬件平台中,是网络安全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思科经验的启发下,邓锋想到了通过硬件来解决网络安全问题这个突破口。
最初,就在自家的车库中,邓锋与自己的创业伙伴——清华大学的同学柯严以及在美国结识的谢青,每周六聚在一起商谈未来公司的雏形。后来他们几乎同时辞去了各自的工作,全心投入到了新公司——NetScreen的创立中来。
和众多初创的公司一样,NetScreen首先遇到的就是资金问题。由于当时整个网络安全市场的规模还很小,因此NetScreen最初并没有引起硅谷风险投资家的关注,邓锋和他的创业伙伴就自掏腰包用作公司的启动资金。
“其实那时候我刚买了房子,已经没什么积蓄了。”邓锋向同学借了5万美金投入到NetScreen中,“我们就是为了向投资人证明,做这个事情我们是认真的。”邓锋说,如果将这次创业比作“跳火坑”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们几个创始人要最先跳下去。
幸而,硅谷是创业者的天堂。在这里,形形色色的天使投资人并不难找到,关键就看你是否有本事打动他们了。
在同学和朋友的推荐下,邓锋开始与“天使”们的接触。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与天使投资人见面的情景,“刚开始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要看我们的技术有多好,但是谈着谈着我就发现他们根本不懂技术。开始我还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投我们,根据他们的问题我才感觉到,他们实际上是在判断你这个人怎么样。”
原来,天使投资人赌的就是人:你的团队是什么样的?为了这个公司你个人的牺牲有多大?你是否有执着的精神……邓锋的表现让天使投资人十分满意。
从美国人、新加坡人到中国人、日本人……“后来愿意投我们的天使投资人越来越多,但是我限制他们,每人只能投10万美元或者更少。因为如果一家投得太多,就会对我们形成控制了。”邓锋说,用了两个星期,他们就从天使投资人那里拿到了第一个百万。
尽管当时NetScreen的产品开发还处于试用阶段,但其产品的创新性以及第一批风险投资的“示范效应”,使得一些实力雄厚的投资机构也开始将目光锁定在NetScreen身上。
就在NetScreen成立五个月后,以投资雅虎而闻名的红杉资本等风投机构纷纷开始为其注资。除去最初的天使投资,NetScreen在历经四轮融资后,总共融得了8800万美元。
“天使”的梦想
“到上市那一天,我们才开始扭亏为盈。”邓锋说,这就是美国风险投资的特点:他们并不希望你很早就能赚钱,因为高科技类的新公司需要在早期做很多研发工作。但如果一开始就想着赚钱的话,将很难进行深入地研发。“而当你扭亏为盈后,很快就能赚到很多钱。”
邓锋和NetScreen的表现也的确没有让“天使”们失望。通过硬件来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是邓锋创新的一种模式。“我们采取了一种‘破坏性技术’,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市场秩序,导致别人无法和我们竞争。”
通常情况下,一家做硬件的公司做不了芯片,做软件的公司又不知道如何做硬件,而NetScreen的优势则是“软硬兼备”,“我们把一帮做硬件的人和一帮做软件的人聚到了一起,让他们一起来设计这个硬件。”邓锋说,这就建立了一个barrier of entry(“入侵壁垒”),使得其他公司很难与之竞争。“过去软件公司性能的提高,往往只有20%—30%,而我们则一下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即10倍。”邓锋说。
时至今日,在全世界的网络安全领域,NetScreen依然占据着高端产品市场份额的第一位。
一个优秀的创业者不一定是合格的管理者,邓锋需要在NetScreen的发展中不断提升自己。“我从技术转到了管理,从运营转到了策略。”邓锋说,从产品策略、商业拓展到公司并购,从一个技术专家到一名管理者,邓锋在NetScreen的角色不停地更换。
邓锋和NetScreen共同成长,他和伙伴们的目标是上市。最初,创业者往往会将上市当作成功的标志。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刚做公司的时候我们都这么想,觉得一旦上市我们就解脱了。”邓锋说,“但上市是一件很磨人的事。心里总念叨,马上就该上了……但老是上不去。”在期盼与焦虑中,邓锋度过了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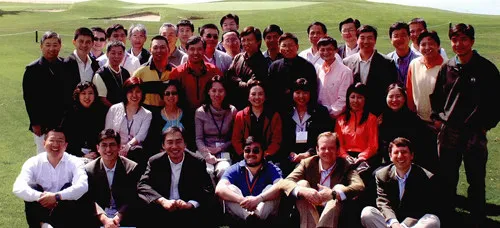
2001年12月11日,NetScreen上市的钟声终于在纳斯达克敲响。作为“9.11”事件后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高科技类企业,NetScreen的成功,不仅是硅谷年轻创业者们的又一次胜利,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给更多的后来者带来了信心。
但上市并没有让邓锋真正轻松,“上市之后高兴了三天,我发现自己根本没解脱,公司的事和原来还是一样的,而且每个季度还得完成报表,还要天天和华尔街的投资人打交道,压力更大了。”
就在NetScreen上市后的第4年,全球第二大网络设备制造商、美国Juniper公司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当时,NetScreen的每股价格大约为26块,而Juniper的出价是每股42块,股东一天就可以赚钱很多钱。尽管NetScreen是我一手创立的,但是我要为公司的全体股东着想。”经过权衡,邓锋很快就做出了出售的决定。
2004年2月,Juniper以40亿美元收购了发展势头正盛的NetScreen。
“在(出售Netscreen)签字的时候,我就知道不会在那个公司长期做下去了。”尽管此后邓锋还在Juniper担任主管公司战略的副总裁一职,但一个关于“天使”的梦想,已在他心中慢慢成长。
“我一生要做两件事,一件是要make fortune(赚钱);第二件要make influence(有影响力),而且一定是对中国经济有影响的,与中国社会相关的事情。”邓锋说,最初他想用一半的时间做天使投资人,其余的时间在中国做一个像兰德公司那样的智库,利用自己在美国的资源优势,帮助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
“其实对很多留学生来说,他们最能做的就是帮中国企业走出去。”邓锋自己的体会就很深刻,很多在国外学习、工作多年的留学生已经在当地生根。而中国大陆的企业要走出去,正需要这些对当地很了解、又懂得中国文化的人。“如果能够把留学生的资源用起来,把他们的智慧与经验挖掘出来,和中国的大陆的企业一起做,帮助他们走向国际化,这将是留学生团队能够做出最大贡献的地方。”
尽管邓锋有种种设想,但他很快就发现,如果在国内没有一个恰当的平台,理想就很难实现。
不一样的“天使”
下定决心回国做风投,邓锋首先就找来了老搭档柯严做合伙人。2005年10月底,北极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办公地点就在清华科技园内。当时,这片位于清华南门的新楼群刚刚落成,北极光则是这个还有尘土味的大楼中第一批进驻的公司。
北极光的一期基金募集额是1.22亿美元。凭借丰富的人脉,融资对于邓锋来说并不是难题,但这一次他不是做普通的高科技企业,而是做“公司背后的公司”。
在北极光成立之前,IDG、软银等国外老牌风投早已进驻中国市场多年,而邓锋这次的创业却是从头开始。“我回到中国的时候,三大变化在我身上同时发生,而这些变化在其他VC身上是看不到的:第一是从企业家变成投资家;第二是从一个很熟悉的市场换到一个陌生的市场;第三,我之前没有加入过风投公司,而是自己开了家风投公司。”
邓锋对北极光的投资人开玩笑说:“你们够勇敢的,居然敢投这样的公司。”对方的回答也很干脆:“我们投的就是你这个人。因为即使出现一次失败的话,你也不会放弃。”
实际上,投资人不仅看好邓锋,也看好整个北极光团队。除了邓锋和柯严,另一位普通合伙人周树华曾在苹果中国、飞利浦等公司工作多年,加入北极光之前,曾任新浪副总裁。另两位创投合伙人陈大同和杨镭,则分别是Spreadtrum通讯的创始人之一以及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掌上灵通”的前CEO。
与一般的VC不同,邓锋说,他们不热衷于问公司创始人“你们的发展计划是什么样的”这类宏观问题,而是“你们的渠道是如何建立的”、“IT系统如何升级”、“如何管理供应链”这类运营方面的问题,“不像是要为企业做投资,更像是为企业做咨询。”
北极光的几位合伙人都有着深厚的技术背景以及丰富的公司运营经验,因此,他们不仅能提供给企业资金,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告诉这些处于初创期的企业,在发展到某个阶段时最容易犯什么错,如何才能避免。
在北极光成立将近两年的时间内,邓锋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创业型企业,但是“看的很多,很少有能投的”。
“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公司创始人的管理经验不足。”邓锋说,除此之外,就是很多人有一个误区,以为技术是第一位的,只要有一个好的创意,就能做出一家伟大的公司,“其实公司能否做好并不是在创意上,而是在团队和执行这两个层面上。我不认为创意那么重要,还有很多比创意更重要的,例如团队的执行力、企业文化等等。”
就像当初天使投资人看中的是邓锋这个人一样,现在邓锋最看重的也是人,“关键要看你这个人对这件事有多认真。尽管市场风险很大,但我不能赌在人上,风险投资希望人的风险能最小化。”
能被邓锋相中的公司创始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学习能力强、有开放的心态、人品好。这之中,被邓锋一再提及的就是人品,因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能否与团队成员合作好,能否有开放的心态等都与人品直接相关。
而所谓的“学习能力强”,并非指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百问不倒。在最初与公司创始人接触时,邓锋经常会抛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但他并不期望对方能不假思索地对答如流,“最好的情况是,我问一个问题,尽管对方没学过或者没遇到过,但是他自己能够推导,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或者根据我的提示,他能一步步通过逻辑推理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也就是说,能力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知识。”在邓锋心目中,“最好的人,是个人的成长总能比企业的成长快一步。例如,今天能管三个人的公司,明天就能管三十人、后天能管三百人……这才是最好的CEO。”
到目前为止,北极光已经投资了15家企业,其中有三家公司已进入了二期融资的阶段,而珠海矩力、展讯通信则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
2007年初,邓锋和沈南鹏、张醒生、朱敏等10人,被评为“中国最活跃的天使投资人”。
“我在成功后,应该把这种经验和大家分享。”邓锋的想法与公司的另几位合伙人不谋而合,“我们做北极光时,并没有想过要赚多少钱,因为对我们来说,赚钱的诱惑远比不上创造影响力的意义大。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帮助中国建造出世界级的企业,能够培育出世界级的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