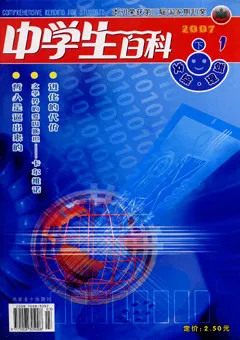科学家们的决斗
2007-12-29沉醉东风
中学生百科·悦青春 2007年1期
著名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感情率真、爱憎强烈,曾数次与人发生决斗。1837年2月,在决斗中,遭法国流亡者致命枪击,终年只有38岁。
决斗,是欧洲近代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解决争执的办法。决斗双方在公证人监视之下,利用剑或手枪来进行公平较量,直到一方被杀为止。在决斗中胜出的一方无需为被杀者的性命负责。因此欧洲大陆上曾经决斗盛行,大仲马名著《三个火枪手》里就曾经数次描述。
对于生在中国的人来说,如果不是对欧洲近代的决斗风俗有所了解,这样的事情是全然无法理解的。文人有学术之争、意气之争,但多数付诸口舌与纸笔。用武器决斗是武人的行为,即使是在崇尚武风的唐代,文人纵有佩剑的风气,也不会轻易用它来决定荣誉与生死。
而与中国人大不相同的是,过去的欧洲人权衡荣誉与死生却有另一套准则。裴多菲诗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正是如实地记录了他们对于荣誉、爱情与生命的看法。爱情可以高于生命、自由比生命更加重要。如果遭遇了决斗的挑衅,逃避就不免会被视作懦弱的行为,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奋勇一战。
如果说诗人的气质使得他们更易于倾向用感性和武力的冲突来决定荣辱成败,那后人至少还可以从他们的行为中解读出一种悲剧的诗意。然而本当最擅长用理性来作决定的科学家也选择同样的方式时,却多少会令人觉得有些不是滋味。
在数学史上,有一则充满悲剧气息的决斗故事广为流传:1832年5月30日,一名不满21岁的数学天才、以开创“群论”知名的青年数学家伽罗瓦,在一场因恋爱纠纷而引起的决斗中身亡。而就在他参加决斗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在通宵达旦地奋笔疾书,为他的论文做注释,力图在那场很可能会带走他生命的决斗到来之前把他的所有数学成果记录下来。在那些被视作遗书的手稿旁边,还写着:“要完成这个证明还需要做些工作,我没有时间。”
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在20岁那年与一名丹麦贵族发生了争执。虽然决斗在当时已被法律禁止,但冲动的青年仍决定用比剑解决争端。黑暗中决斗的结果是,第谷被削掉了大半个鼻子,不得不用合金制作了一个假鼻子,用胶粘在脸上,从此需要随身携带一个装胶的小盒子,不时地给鼻子上胶。
如果第谷在1566年就在决斗中丧生,那么他将无法坚持二十多年的天文观测,更无从引导开普勒从他多年观测积累的精确行星运行数据中推导出行星运行三定律。第谷编制的777个星体位置表至今还在使用,不由令人庆幸他那场出于年轻意气的决斗没有造成更坏的后果。
决斗这一行为在19世纪末期开始渐渐被压制下去。但与其说这是政府的强制力量所致,倒不如看作人们的理性在逐渐地抬头:那么多年轻杰出的生命,就这样消耗在一件件意气之争的决斗上,这样的行为,是否有意义?一个人的人生有什么样价值,是否只能用一种态度来裁决?如果伽罗瓦能够活下来,他是否会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证明他的理论和成果?是否会为整个数学界的工作带来更早的推进?这一切在他去后,也只能沦为无谓的猜测。
所幸的是,伽罗瓦的悲剧为后世的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机会:决斗这样的冲动行为,是否真的值得不惜生命与事业地参与。就在伽罗瓦不幸丧生数十年后,发生在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身上的一则与决斗有关的故事证明,伽罗瓦的牺牲不是全然无谓。
当时的巴斯德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一名不速之客闯进来对他说:某伯爵准备与他决斗。巴斯德的回应则十足体现了科学家的理性与冷静:“无论谁要提出与我决斗,按照惯例,我有权选择决斗的武器。这里有两只烧杯,一只装着卡介苗菌,另一只装着清水。我的对手可以随便选一杯喝掉,剩下的归我来喝。”
那位无礼的伯爵是否真的去喝过烧杯里的水无人知晓,但众所周知的是,巴斯德的一生没有终结于无谓的争斗。他作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以倡导疾病细菌学说、发明预防接种方法闻名于世。他的预防接种办法从开创至今已经拯救了无数的生命,且在可见的未来里,仍会继续为人类的健康造福。
生命诚可贵,它的可贵尤其在于不应当被随意地衡量与舍弃。
编辑/刘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