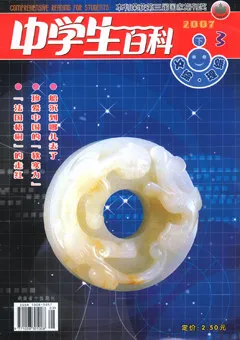不输文采的唐太宗
2007-12-29王峰
中学生百科·悦青春 2007年3期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几句话,至少对汉武帝刘彻和唐太宗李世民来说是冤枉的,因为他们并非只会马上取天下,两人都雅好文艺,汉赋、唐诗,可以说正是在他们的提倡和带动下繁荣起来的。
李世民武功政绩自不必说,在文艺方面也有相当的兴趣和造诣。《全唐诗》小传称他“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这当然有点夸饰,但与事实相比,还不算很离谱。他留下了诗作一卷69首,这些诗即便不是皇帝所做,也算得中规中矩的合格之作。李世民还在做秦王时,就在府中开设了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做了皇帝之后,又设置弘文馆,让学士们轮番值班,办公之余就探讨学问、吟诗作文。现存的那一卷诗,远不是他的全部作品。他在书法上也下过工夫,据说弄到《兰亭集序》真迹之后,爱如拱璧,在戎马倥偬的年代也从不离身。
他写《帝京篇》组诗,自序说“予以万几之暇,游息艺文”,表明自己只是业余写作,自觉地和热衷于文艺活动却把国家搞垮的陈后主、隋炀帝这些人划清界限。他声明自己写诗是为了“明雅志”,而不是像陈叔宝、杨广那样流连于奢侈靡丽、醇酒妇人。他是个好皇帝,所以得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注意不在诗文里落下把柄,但如此一来,写作题材很受限制,除了表达政治抱负、忧国爱民情怀,就只能一本tyfL1x7MtoYrCnPy0iFd7P571+a4aSO00li+TUFoeb8=正经写写风景、景物。
南朝梁陈以来流行一种宫体诗,专门描写宫廷生活和男女私情,虽然格调有点儿不高,但形式华美、音调柔婉,对作者和读者都很有吸引力。好皇帝毕竟也是皇帝,唐太宗生活在宫廷之中,后宫佳丽众多,渐渐地就不满足于只在诗歌里“明雅志”了,对宫体诗也跃跃欲试。有一天,他找来文学侍臣虞世南,假装漫不经心地说:“我写了首艳体诗,玩玩而已,不当真的,你来唱和一下吧。”
这位大臣虞世南,是著名诗人、书法家,早年曾得到宫体诗高手徐陵的称赏,在隋炀帝时也曾奉命写过这一类东西。但这种路数与他沉静好学的性情不合,所以入唐之后,他就收手不做,成为集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法于一身的当代名臣、道德模范。他看完唐太宗的宫体诗,恭恭敬敬地递回去说:“皇上的诗做得很好,不过请恕臣斗胆直言,内容可有点儿不够雅正。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这样的诗一旦传出去,只怕天下人都要争相效仿,后果将不堪设想。臣绝不敢奉诏,也请皇上今后不要再下这种命令。”
李世民兴头上被浇了一瓢凉水,不免扫兴,但也只得笑笑说:“其实我也只是试探试探你罢了!咱们君臣哪能把心思花在写这种东西上头呢?”他赐给虞世南五十匹绢。得了这个教训之后,他就死心塌地继续写言志诗、咏物诗,不再动宫体、艳体的念头。不过他对陈叔宝、杨广的生活方式多少有些艳羡。
后来有一回,李世民写成一首讲述历史兴亡的很正经的诗,自己觉得不错,想找个人讨论一下,才想起来虞世南已经死了,他叹口气对左右说:“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啊!这首诗还能拿给谁去欣赏呢?”于是命令另一个文学侍臣褚遂良把诗稿拿去,在虞世南灵前焚化。
李世民最好的一首诗,大概是有格言诗风味的《赐萧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后世的评论家说,唐太宗的诗主要还是沿袭陈隋遗风,这是不错的。他爱用些细碎而不免雷同的小巧意象,比如《秋日效庾信体》中“珠穿晓露丛”和《月晦》诗里“穿露晓珠呈”之类的句子,就诗艺而言,确实不大高明。《唐诗三百首》这样的通俗选本不选他的诗,明清易代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号船山)编《唐诗评选》,倒是选了唐太宗好几首,还称赞他的《咏桃》诗为“绝代高唱”。但王船山的欣赏口味常常和普通读者不同,这首诗到底为什么是“绝代高唱”,看过他的评论仍然不容易弄懂。
编辑/孙栎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