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乐水梁季阳
2007-12-29曹昕
中华儿女 2007年5期
见到梁季阳,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眼睛,虽然佩戴着一副眼镜,却感觉那双眼睛可以穿透地球。“作为一名研究水的科学工作者,我的工作岗位既不在讲台,也不在实验室,而是经常‘离家出走’,在野外进行科学实地考察。直面大自然是我的一种偏爱,使我能够亲身体会自然环境的灵性和魅力,感受到水是自然的血脉,是生命之源。‘人水和谐’是我致力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野外工作环境艰苦、恶劣,但是从不觉得乏味、厌倦。”当梁季阳青春的脚步踏上理想的征途,面对挑战他从未缺乏勇气。
智者乐水
1965年,梁季阳大学还没有毕业,就与水结缘。
“记得,当时我正在乡下搞‘四清’,每天都在水田里劳动,或者是搞运动,开大会。突然有一天,系里的老师找到我,要我马上回学校,去承担一项任务,很快我就动身离开了乡下。”一切准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同学、老师乃至家里的亲人,都不知道梁季阳离开乡下到了哪里,去做什么。梁季阳也没有想到,从此他便告别了学生时代,开始与水结缘40年的水梦年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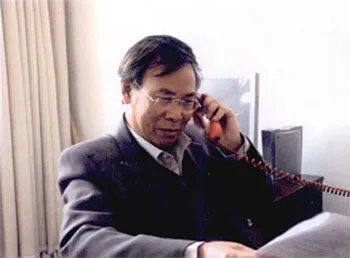
“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24岁的梁季阳怀着这样的青春豪情,一步迈进了祖国建设的大潮中,参与“三线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探索开拓金沙江航道。
经过一路的周折,梁季阳和同伴乘火车从南京出发经成都、西昌,最后到达渡口。他们乘着一叶扁舟,在金沙江的惊涛骇浪中漂流,勘查、记录所有险滩、岩石、暗礁的分布情况。感受着奔涌不息的金沙江把陡峭山峰横切成的险峻大峡谷;湍急的金沙江水流翻卷着的巨大的漩涡;金沙江拍打的磅礴大气。梁季阳和同伴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任务,为国家开拓金沙江航道工程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料。“金沙水拍云崖暖”。滔滔不绝的金沙江水咆哮着向前冲去,不屑向懦夫侧目。梁季阳在金沙江水的冲击中历练、成长。
“1968年黄河河口的水位出现异常的情况,水流人海不畅,位于黄河口的胜利油田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胜利油田向中央提交了紧急情况的报告。”1969年,梁季阳和水科院、黄委会的同志组成了黄河河口水道考察组,赴黄河河口进行实地考察。“黄河河口水深比较浅,原来的机动考察船不适合这片水域。我们只好离开大船,换乘一艘木船驶入黄河河口。那是水天相连的一片汪洋,我们在木船上连续工作了七天七夜。通过对河流走势、滩槽变化状况等因素的综合分析,最终确认河道仍然处于发育期,否定了立即改道的方案,建议保持现有河道行洪。上级部门采纳了我们的意见。第二年黄河河口的水情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黄河上经历的一场狂风暴雨,给梁季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考察第4天,狂风暴雨突然袭来,往常平静的黄河瞬时大浪滔天,水下暗流翻涌。平日里对他们十分客气、和蔼的船老大,严厉地命令他们停止所有工作,回到船舱内,盖上船舱盖板。“里面一片漆黑,我们只有静静地等待,只觉得小渔船在波浪中疯狂地颠簸,隐约听到如雷的涛声,两个船夫紧张的呼喊声。”在漆黑的小船里,身临其境的梁季阳和同事们才真正理解了黄河,当勇气战胜恐惧,当意志战胜懦弱的时候,思想和灵魂突破了黑暗,达到一种新的境界。当梁季阳和同事们看到从船舱盖透过的阳光,船老大的大手伸向他们的时候,一股温暖的力量通透全身,梁季阳对水事业的热爱已融入他的生命和血液。
1974年,梁季阳的足迹又踏上“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来到了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此次实地考察的任务是为青藏铁路的建设作前期准备,在铁路线路设计中,需要对经过的所有大大小小河流曾经发生的洪水进行调查,需要计算未来一定概率的洪峰流量,并以此来设计各个桥梁、涵洞的高度和长度,测量与计算的结果将直接影响整个铁路的工程造价。
在内地,7~8月份正值盛夏,而在青藏高原却漫天飘起了鹅毛大雪。梁季阳和铁道第一设计院的同事们,在氧气不到海平面一半的高原上,白天气喘吁吁地沿着青藏公路,背着测量仪器,一条河,一条沟地勘测,晚上住宿在接待汽车运输兵的兵站,和士兵们同吃同住。“工作时要背着各种仪器,不可能再带氧气瓶,长期处在高原反应状态中,一些同志反应比较严重,晚上睡不着觉,只好下山了。”高原反应、夹生的米饭、半生不熟的馒头、咸菜疙瘩,这是梁季阳近两个月的高原生活状况。“不冻泉得了病,五道梁送了命”“风火山,鬼门关”(不冻泉到五道梁距离仅几十公里,意指高原病的凶险),梁季阳和同事们面对高原工作中可能发生的一切危险,泰然处之。“从纳赤台到唐古拉山,处于高原阴坡,终年少见阳光,再加上高原缺氧,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当翻越唐古拉山进入西藏,到达海拔3000多米的拉萨,见到阳坡绿色的草原,灿烂的阳光,精神为之一爽,我们感到似乎是来到了美好的人间天堂。”追忆当年那段无尽艰难中的一丝美好,梁季阳的眼角带着甜美、乐观的笑容。
回想起过去一幕幕享受艰苦的激情人生,梁季阳深情地说:“现在年纪大了,回过头来看,那时能够被祖国挑选就是荣誉、是信任,是我们那一代人最为之自豪的。艰苦才是享受,才有快乐。自己的所学能够为祖国经济建设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一生能够扎扎实实地为祖国做几件事情,我觉得这样就很幸福了。”梁季阳在最难、最险、最高的地方都留下了自己青春的足迹,让知识在艰苦的环境中闪光,正是梁季阳那一代中华学子价值观念的真实写照。
作为一位科技工作者,梁季阳重视野外的实践工作,也十分重视理论研究,特别是对于研究工作有价值的新方法,新技术。70年代,他很早就意识到计算机在科研工作中的巨大作用,很快学会了当时国产和进口计算机的使用方法,经历了从最初的黑纸带,穿孔卡片,8寸、5寸、3寸的软盘,大盘磁带等计算机用的存储介质,掌握了多种编写程序的高级语言,并将这些知识用于水文现象的模拟。1985年,应美国一所大学的邀请,由对方提供全部费用,梁季阳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开展近2年的合作研究。梁季阳作为主持、主要参加者承担了多项国家攻关、省部委和基金的研究课题,与合作者一起获得了多项科技大会奖、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奖。
对水负责就是对中国的未来负责
梁季阳深知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水资源,而我国又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为了科学地利用水资源,开源节流,防治水污染,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梁季阳几乎走遍了全国的江河、湖泊,近年来,梁季阳对我国西部的水电开发、河流健康与能源战略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思考。
目前,我国中西部以及水能富集的西南地区,各大河流的干流和支流均规划了大量的梯级电站,中小河流的水电开发也纷纷立项上马,小河流的小水电更是遍地开花。2002年底的电力系统改革,从原国家电力公司分出的5家全国性电力集团相继制定了中西部发展战略,开始了更具商业色彩的电力大开发计划。与此同时,大量的地方资本、民间资本则盯上了各大集团“圈”剩的中小河流。在2004年6月举行的昆交会上,浙江、福建、湖南等与云南签约开发地方水电的资金就达62亿元。梁季阳一语道破其中的原由:国家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较丰富的水电资源自然而然成为产业发展的首选方向,吸引国资、民资、外资等各路资本竞相进入电力市场。这股“圈水”的热潮不禁令人联想起不久前的“圈地”热潮。
建国以来,由于不合理的河流开发,也曾出现河流局部河段死亡、河道断流,造成区域性的生态灾难:塔里木河上游兴建水库,拦蓄的河水灌溉草原和农田,形成了新的绿洲,新的城市在荒原上诞生。正当人们欢呼征服大自然的伟大胜利的时候,由于塔里木河中下游断流,大面积的胡杨林死亡,罗布泊干涸,大片土地荒漠化。建国之初,河北平原的地下水埋深仅几米,人们可以用扁担勾着水桶打水,现在山区修建了大量水库,由于缺乏地表水补给,大量开采地下水,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已形成跨冀、京、津、鲁的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有近7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沉痛的教训应该会让我们警醒。无序的水电开发,将是把河流节节寸断,原来奔腾不息的河流,将成为水库隔断的一潭潭死水。河流的自净能力将会丧失,水的污染将会加剧水资源短缺的危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格言是不应该忘掉的啊。”
面对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于能源的迫切需求,梁季阳将国家的各种能源和水电资源进行了同步思考:在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的前提下,经过科学规划,构建以大型水库为框架,中型水库为主体,适度的小型水库为补充,相信可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也可以维持河流的健康生命力,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核电工业,保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梁季阳心目中,自然界的河流都是有生命的,他们奔腾不息、潺潺舒缓,孕育了各类水生生物的世代繁衍。他不愿看到一条条河流因为人类的急功近利而“生病”,更不愿看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无水为继,国计民生由于缺水而陷入困境。如今,梁季阳虽然离开了工作第一线,但是,作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学术指导,他仍然时刻关心着祖国的水利事业,10年来,梁季阳在全国“两会”上多次提交了有关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提案和书面发言。责任和情感不可分离地融入梁季阳对水的终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