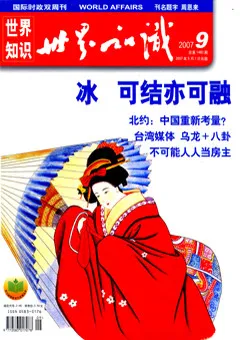伊朗:徘徊在鱼与熊掌间
2007-12-29任宇
世界知识 2007年9期
从德黑兰出发,沿着高速公路向南约300公里,荒漠中有一个名叫纳坦兹的小镇坐落在绿洲上。在海拔2500余米的纳坦兹,春天的脚步姗姗来迟,草场刚刚泛绿,果园里梨花如雪,和远处雪山相映成趣。放眼四望,赭红色的小山坡上,防空高射炮隐约可见。4月9日这天,伊朗总统内贾德在纳坦兹铀浓缩基地以伊朗国旗和原子标志为背景的讲台上,兴高采烈地对外宣布,“从今天起,伊朗已经加入有能力进行工业规模核燃料生产国家的行列”。“伊朗人将捍卫自身权利,直到最后一刻”。显然,联合国17天前(3月24日)通过的旨在遏制伊朗核计划的1747号决议,并没有让内贾德感到局促和为难。相反,内贾德有意让大家分享自己的欢乐。这一天,纳坦兹铀浓缩基地汇集了数百名伊朗政府高官、议员和外国使节,以及近百名国内外记者。在现场,歌手、诗人和交响乐团竞相表演,颂扬之声不绝于耳。面对国际社会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制裁,伊朗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西方观察者眼中的伊朗
从欧洲大城市出发,只要五个多小时的空中飞行,就可以到达德黑兰。经济舱里人满为患,不禁让第一次踏上伊朗之旅的西方观察者感到惊讶。原本以为即将到达的地方,早就被战争阴霾笼罩,谁想机舱里沸沸扬扬的景象却这样提醒了他:不要低估伊朗面纱下面深藏的与西方经济往来的规模和密切程度。
还没等飞机离开欧洲的地面,临座的伊朗小伙子又给观察者上了一课。这是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是伊朗一家外贸公司派驻伦敦的常驻代表,他滔滔不绝讲的当然是自己的国家。他赞美西方国家的发达,痛斥国内毛拉们的腐败,对总统内贾德则是毫不掩饰地懊恼:“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平常根本没有兴趣过问政治。正是由于我们的缺席,内贾德才在大选中意外地获胜。”
年轻人无所顾忌的言论,让内贾德和他领导的伊朗在观察者眼里顿时变了模样。原来在核问题上奉行强硬政策的总统背后,并不是铁板一块。伊朗人通过民主选举把他推上总统宝座,却不意味着他完全代表民意。新闻工作者马苏德也有这样的判断:目前只有15%的伊朗人可以算做内贾德的铁杆后盾。一年前内贾德公开宣称“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的时候,一些伊朗人也有几分羞愧。
马苏德解释道:“把选票投给内贾德的人,是因为相信了他的承诺。当时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拉夫桑贾尼代表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拉夫桑贾尼自己就是个有钱人。于是,内贾德努力去争取穷人。”人们看到,新总统很快重修了公路,有效缓解了首都的交通拥堵;新总统就任后不到一个月就宣布从石油收入里抽取13亿美元建立“基金”,专门帮助年轻人解决就业、成家和住房问题;在他的关照下,德黑兰南部郊区大片荒地被改造成公园……大家说这是一个能干的总统,暂时没有注意到其他。可后来,人们渐渐发现,前任总统哈塔米在大学开创的文化中心,被新总统改造成了礼拜室,快餐店也被勒令歇业。而早在内贾德担任德黑兰市长的时候,就已经要求市政工作人员穿长袖衬衫,男性蓄胡须,政府办公大楼实行男女分乘电梯的政策;就连英国足球明星贝克汉姆的广告头像也被从墙上扯下。在内贾德的管理下,曾经缓慢走向开放的伊朗,又被严厉的伊斯兰教规收紧了缰绳。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真的难以适应。而在一个30岁以下人口比例高达70%的国家,这显然不是什么好征兆。
三十年始终徘徊踌躇
对于习惯西方生活方式的人来说,德黑兰的日子有点忧郁。
这里风景很美,清澈的山泉水顺着明沟一路淌来,浇灌着街道两旁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几乎让人误以为身在巴黎。可是,沿街没有高堂满座的小酒馆儿,也看不见灯红酒绿的舞厅。来来往往的伊朗妇女,全都严格按照伊斯兰教规着装,就连走秀的时装女模特也必须用头巾把头部蒙上,因为“规定就是如此”。在德黑兰机场,穿着一身绿色军装的“风化警察”似乎不放过每一位过往的女性,不时走到某个年轻姑娘面前,一面彬彬有礼地请求她换一身更长的外套,一面递给她一块纸巾:“请您擦去嘴唇上那一点挑逗的红色。”
伊朗曾是中东地区西方化世俗化较为彻底的国家。1979年被推翻的巴列维王朝一度企图利用巨大的石油财富,迅速把伊朗拉上现代化的快车道。在极短的时间里,伊朗大城市一派莺歌燕舞,音乐厅、电影院、咖啡馆、游乐场和豪华酒店应有尽有,简直与西欧都市难分轩轾。德黑兰甚至拥有容纳上千名风月佳人的红灯区,以供有钱阶层买醉寻欢。宗教领袖霍梅尼掌权之后,“伊斯兰革命”以疾风扫落叶之势迅速对种种“西化”现象展开清扫,红灯区固然属于必须清扫的内容,就连大学校园也被视为“培养西化人才和殖民主义奴才的地方”而一度封闭,直到1982年底才宣告复课。

巴列维和霍梅尼分别引领伊朗走向发展的两个极端。多年以来,伊朗社会一直在两种倾向中艰难寻找平衡的支点。一位流亡海外的伊朗高级知识分子尖锐地指出,虽然巴列维国王倒台差不多30年了,伊朗社会始终徘徊踌躇:“伊朗一直犹豫着该向哪个方向妥协:是回归伊斯兰传统,还是纳入现代化发展轨迹;是融进现实世界,还是继续自己的‘伊斯兰革命’;是接受新任领导人(内贾德)的选择,还是索性明确提出,伊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离不开西方的帮助。”
霍梅尼去世后,伊朗领导人选择中间路线,对伊斯兰禁忌的控制有时严格一点,有时放松一点。哈塔米当总统的时候,流行音乐、快餐和可口可乐又回到日常生活中。内贾德继任之后,它们立刻远离而去。伊朗人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在德黑兰,表面上看到的东西和真实的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碰到有组织的游行,大家辱骂美国,高喊与阿拉伯世界结成一体,“打倒以色列”的口号震耳欲聋。但是私下里,许多年轻人却对美国赞不绝口,把阿拉伯人看作侵略者、历史上的宿敌。至于以色列,相当一部分伊朗人愿意把他们视为这个地区为数不多的朋友,理由是:“我们,他们,还有土耳其人,是中东地区的非阿拉伯民族。”
基什岛的“怪现象”
在波斯湾,距离德黑兰1052公里(空中距离)有一个91平方公里的小岛——基什。作为伊朗屈指可数的自由贸易区,基什拥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利。每年大约有100万伊朗公民怀着各种心情和想法前往基什一游。今年春天,年轻的玛亚姆和同伴也决定到这里放松一下。出发前,她的心中充满了期待:“据说,这是一个让时间可以停滞的地方。”
基什曾经浓缩了巴列维国王的强国梦想。国王亲自设计行宫(有厚实的水泥墙和宽大的茶色玻璃,可以挡住炎炎夏日),还兴建了高级俱乐部和可以起降协和超音速客机的停机坪……1979年国王仓皇辞庙,霍梅尼忙着摧毁本土残留的西方化痕迹,一度把距离海岸线只有20公里的基什遗忘。1989年拉夫桑贾尼政府决定将基什岛辟为工业贸易自由区,1993 年议会以法律形式加以确认。
基什设有证券交易所,银行多如牛毛,吸引流亡海外的伊朗人来这里投资。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之后,基什新的阿亚图拉管理手段虽然比前任严苛,但免税区仍然留够充足的自由空间。对生意人来说,这是一块投资的好地方,而在玛亚姆和同伴的眼里,这是一个可以痛快玩一场的游乐园。在最新一版的旅游手册里,标明了海豚馆、珊瑚礁、植物园、旧日行宫遗迹的位置。
“在基什,我们可以穿着无袖T恤衫四处闲逛,而在德黑兰,我们必须把自己包裹起来才能上街。”玛亚姆说:“德黑兰的公共娱乐场所虽然也有台球,但是禁止女性参与,到了这里,规矩就没那么严了。”来到岛上,每一次小小的违禁都让她笑声不断。在伊朗的其他地方,青年男女只要还没有结婚,绝对禁止进行肉体接触。可是到了基什,年轻情侣可以手拉着手逛商场,把脸贴在大橱窗上,放肆地盯着衣着暴露的塑料模特。巨大的广告画上,漂亮的金发模特搔首弄姿地推销最新款的名牌香水。
在基什的海滩上,高高混凝土围墙的背后有一块只对女性开放的日光浴场。“禁止照相”的警示牌随处可见。准备到这片海滩晒太阳的伊朗女性,必须在指定的地点更衣,摄像手机问世后,这项要求更严格了,不过,她们仍然可以穿着比基尼游泳衣上海滩。一位女性救生员穿着性感的无吊带泳装,脖子上挂着哨子,站在木头搭成的了望哨上,不知疲倦地观察海滩的动静。
要不是眼见为实,外国人绝不肯相信伊朗还有这样的地方。当伊朗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因为核问题变得紧张而微妙的时候,基什岛愈加显得不可思议。来这里投资、工作的伊朗人、外国人好像并不担心可能发生的危机。俄罗斯和科威特的有钱人来基什是为了投资;菲律宾人和印度人选择到基什小住数月,是为了换取到其他海湾国家打工的签证。从卡塔尔的迪拜国际机场搭乘基什航班,不但可以登陆基什,甚至还能前往阿富汗的喀布尔。基什岛的存在,恰好反映伊朗人内心的冲突:他们渴望国家获得发展,却深怕自己沦为强国手中的战略工具。无论神权政治还是核计划,都是免遭沦为强国工具的保证——然而要发展,又不能缺少基什岛。
冰雪消融,从内部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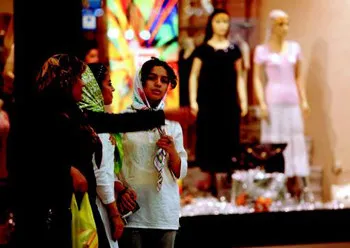 `
`近十年来,三股政治势力你来我往,率领伊朗社会在“鱼”与“熊掌”之间忽左忽右地徘徊。总统内贾德是保守派的代表,他的背后有最高领导人、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支持,有精锐的革命卫队做保障。前总统哈塔米所代表的是改革派。他们希望伊朗变得更世俗化,尽量拉近神职人员与政治的距离,在外交上,则希望缓和与西方的紧张气氛。站在两派中间的,是以“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拉夫桑贾尼为代表的温和保守派(或称中间派),他们也希望和西方修复关系,希望经济上更趋开放,不过,他们对国家世俗化倾向的提议,并不热衷。
去年12月,伊朗第四届专家会议选举和第三届地方议会选举同时举行,温和保守派阵营控制了伊朗主要城市议会的大多数席位,而在上届选举中失利的改革派也超过内贾德率领的保守派,位居第二;保守派仅获得不到20%的议席。在更为重要的专家会议选举中,拉夫桑贾尼一派获得了较大优势。由于专家会议可以在领导人不称职时将其废黜,所以内贾德一派在这块阵地上的失利,更加引人关注。
据说在德黑兰,不满的声浪时隐时现。大家失望地看到,通货膨胀有增无减,失业率居高不下,内贾德当初许下的美好承诺大多化成一张空头支票。今年1月份,有150名议员联名写信,批评总统的经济政策,就连忠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保守派报纸《伊斯兰共和国报》也大量刊登批评的文章。如果说,内贾德总统在宗教领域重新收紧的缰绳已经足以让年轻人感到不快,那么他在经济政策上的乏力,更像是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最近一段时间,一个重要的信号通过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亲信,传到西方观察家的耳朵里,据说最高领袖对总统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其实,哈梅内伊对内贾德颇感失望的说法,已不是新闻。